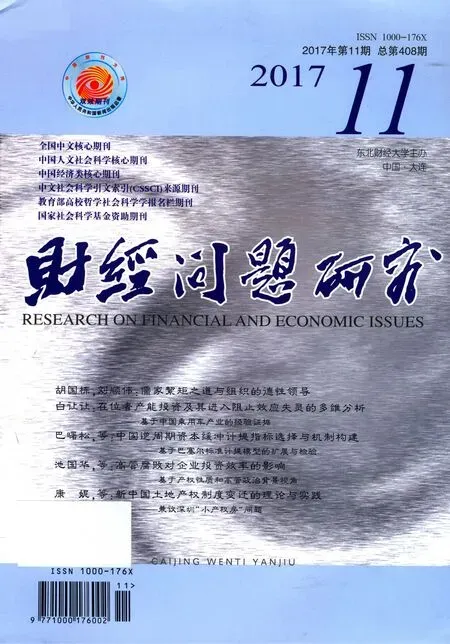董事會兼任經理層、審計需求與審計意見
——從第一類代理成本角度
郭 林
(東北財經大學 會計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5)
·財務與會計·
董事會兼任經理層、審計需求與審計意見
——從第一類代理成本角度
郭 林
(東北財經大學 會計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5)
隨著董事會兼任經理層的比例在我國上市公司董事會層面逐年攀升,經理層與股東之間的代理問題逐漸凸顯,基于此,本文實證檢驗了董事會兼任經理比例與審計師選擇、審計意見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首先,兼任比例與代理成本、高質量審計需求成倒U型關系,進一步研究發現,上市公司能夠識別審計師的質量,對本土大所的品牌認同度不高;其次,我國整個審計市場的質量偏低,還不能發揮應有的監督作用,尤其是本土大所可能存在與經理層合謀行為,出具有利于經理層的審計意見欺騙外部投資者。
董事會兼任經理層;審計需求;審計意見;外部投資者;代理成本
一、引 言
董事會兼任經理層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一般認為,董事會在公司治理中具有戰略咨詢與監督控制的職能。由于董事的時間和精力有限,并且兩項職能的發揮對經理層共享內部信息的激勵不同,因此,董事需要在兩項職能中做出權衡,而權衡的直接方式就是董事會與經理層的兼任。兼任使得董事會與經理層的聯系更加緊密,因而可以緩解董事會與經理層間的信息不對稱,但同時也削弱了董事會相對于經理層的獨立性,故董事會的戰略咨詢職能得到了強化,但監督控制職能卻被削弱。
為保證董事會職能的發揮,我國一系列法律法規對董事會與經理層的兼任進行了直接或者間接的規定,包括設立獨立董事制度、不鼓勵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等。從這些規定來看,現有法律法規允許但是并不鼓勵董事會與經理層兼任,特別是董事長兼任總經理,對兼任經理層的董事比例要求最多不超過2/3,并從獨立董事比例角度強調董事會的獨立性。但實踐中董事會與經理層兼任現象越來越普遍,并呈逐年攀升趨勢,公司治理中股東與經理層之間的第一類代理問題凸顯,這就使得合理有效的經理層制衡機制顯得尤為重要。本文將重新考察我國資本市場的有效性以及在這種環境下國際“四大”、綜合排名十大、本土十大和其他小所與審計質量的關系,主要通過構建董事會兼任經理層變量的二次項,研究不同董事會結構(董事會兼任經理層比例)的公司與外部審計師選擇、審計意見之間可能存在的復雜關聯。具體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探討:(1)從審計需求角度,受第一類代理成本影響的上市公司會選擇怎樣的外部審計師?在資本市場有效性上,上市公司能否識別不同審計師的審計質量?或者上市公司是否相信“審計師規模越大審計質量越高”?(2)從審計供給角度,外部審計師在出具審計意見時考慮了上市公司存在的第一類代理問題嗎?被市場認為具有較高聲譽的N大會計師事務所是否與經理層合謀,向外部投資者傳遞“真實可靠信息”的信號卻并未提供高質量的審計服務?
二、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一)董事會兼任經理層的比例與代理成本
代理問題是企業有效契約觀的基本問題之一。現代企業中通常存在著兩類代理問題:第一類是股東與管理當局之間的代理問題,第二類是控股股東和外部中小投資者之間的代理問題。董事會兼任經理層的代理問題主要是指第一類。一般而言,關于董事會兼任經理層對代理成本的影響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由于委托代理問題的存在,兼任比例的增加使得經理層的權力得到大幅度提升,董事會的監督職能減弱,此時可能出現內部人控制現象,以CEO為首的經理層掌握著董事會議程、提交給董事會的信息和決定董事會討論議題等重大問題,在自身利益與股東利益不一致時,往往會選擇維護自身利益而損害股東利益,代理成本增加。另一種是從現代管理理論角度,人既有可能成為自利的代理人,也有可能成為無私的優秀管理者,作為理性的經濟人,不僅有追求物質滿足的動機,也有追求榮譽和成就的動機,無論是經理層向上進入董事會還是董事會成員向下擔任經理層,均是對高管個人能力的肯定,是一種權力表彰,此時,經理層決策的出發點更會從股東利益出發,以公司價值最大化和股價不斷攀升為目標。除此之外,兼任使得董事會與經理層的聯系更加緊密,可以緩解董事會與經理層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同時,由于經理層對公司經營狀況比較了解,有利于提高董事會決策的有用性和公司運營的效率,促進董事會戰略支持功能的發揮,代理成本得到大幅度降低。
因此,隨著兼任比例的逐步上升,經理層的掠奪效應明顯,表現出兼任比例與代理成本正相關,但隨著兼任比例進一步上升,并不會導致經理層掠奪程度的進一步上升,而是使經理層的行為從企業整體的利益出發,從而又將表現出兼任比例與代理成本負相關的。因此,本文提出假設1:
假設1:董事會兼任經理層的比例與代理成本呈倒U型關系。
(二)董事會兼任經理層的比例與審計師選擇
根據代理理論,公司內部存在嚴重的代理沖突將導致其對外部監督或約束機制的內在需求,尤其是信譽較好的外部審計師,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市場價值。自從 Jensen和Meckling[1]以來,已有一系列西方學者從管理層持股、成長性與外部審計的角度,實證考察了公司是否會通過聘請高質量審計師,以降低管理層與外部投資者之間的代理成本,從而提高公司價值,并得到了經驗證據的支持。根據代理理論,成長性越高、管理層持股比例越低,代理成本越高,因而越會選擇更大的審計師事務所。Simunic[2]、Firth和Smith[3]發現,管理者持股比例越低,IPO時越容易選擇“八大”作為主審事務所。Eichenseher等[4]發現,那些主審事務所從非“八大”變更為“八大”公司的總資產增長率明顯高于從“八大”變更為非“八大”或者保持原來事務所不變的公司。我國學者也發現,現階段代理沖突嚴重的公司有動力聘請高質量的外部審計師。曾穎和葉康濤[5]用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衡量代理成本,發現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我國上市公司選擇“四大”呈倒U型關系。李明輝[6]從公司規模、成長性、財務杠桿、管理層持股比例、董事會獨立性等幾個方面,實證檢驗了代理成本與審計師選擇的關系,發現公司規模與選擇大事務審計所有顯著的正向關系,管理層持股與選擇大事務所審計呈倒U型關系。王燁[7]研究發現,控制性股東的控制權結構所產生的代理沖突越嚴重,上市公司越有可能聘請審計質量較高的“四大”審計。
本文也將綜合排名十大和本土十大作為高質量審計師的替代變量。從兼任比例與審計師選擇的關系可以檢驗:在我國資本市場上,上市公司是否相信“事務所規模越大審計質量越高”,即代理成本較高時公司是否更傾向于選擇規模較大的高質量審計師?因此,本文提出假設2、假設2a和假設2b。
假設2:董事會兼任經理層的比例與選擇高質量審計師呈倒U型關系。
假設2a:董事會兼任經理層的比例與“四大”、綜合排名十大、本土十大呈倒U型關系。
假設2b:董事會兼任經理層的比例與其他小所呈U型關系。
(三)董事會兼任經理層的比例與審計意見類型
理論上,隨著代理成本的增加,審計師面臨的控制風險增大,此時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概率更高。然而,審計意見是外部利益相關者用來評價經理層受托責任履行狀況的一種重要的外部監督方式,因而對于經理層具有重要意義。經理層會盡可能避免獲得非標準審計意見,他們可能利用自身的權力影響審計費用或其他方式對審計師施壓,使其不出具過于嚴厲的審計意見,即審計合謀。周中勝和陳漢文[8]以大股東資金占用定義第二類代理成本,發現審計師在出具審計報告時會考慮大股東資金占用,大股東資金占用越嚴重越可能獲得非標準審計意見。李海燕和厲夫寧[9]認為,高質量審計能給債權人更好的保護,審計意見具有預警作用,但國際“四大”與本土“五大”并不能給債權人更強的保護。由此,本文擬從審計供給角度,檢驗外部審計師在出具審計意見時能否考慮上市公司存在的第一類代理成本,在代理成本較高時能否保持獨立性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進一步從不同規模事務所出具的審計意見類型檢驗:在我國的資本市場,審計師規模與高質量審計的關系是否符合現實?因此,本文提出假設3、假設3a和假設3b:
假設3:董事會兼任經理層的比例與審計意見呈U型關系。
假設3a:在“四大”、綜合排名十大和本土十大審計的樣本中,董事會兼任經理層的比例與審計意見呈U型關系。
假設3b:在其他小所審計的樣本中,董事會兼任經理層的比例與審計意見呈倒U型關系。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擇2005—2014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為原始樣本,并在此基礎上:(1)剔除年報中沒有披露審計意見、無法獲得高管任職信息、營業收入、營業費用和銷售費用的公司。(2)剔除金融行業公司樣本。(3)剔除ST及*ST的公司。(4)剔除樣本期間缺失數據較多且無法補充的公司。經過以上的篩選過程,我們最終選取了12 582家符合條件的上市公司。
本文所使用的董事會結構數據、審計意見和財務指標數據等均來自于CSMAR數據庫,其中,董事會兼任經理層比例的數據全部為手工收集計算獲取。為了防止極端值對本文結論的影響,我們對所有連續變量小于1%和大于99%分位數據進行了Winsorize處理。采用 STATA12.0進行數據分析。
(二)模型設計與變量說明
為了檢驗假設1,本文使用如下模型:
Dlcb=a+b1Jianrenbili+b2Jianrenbili2+b3Power+b4Cfodirector+b5Ind+b6Size+b7Lev++b8Ma+b9Growth+b10Dizhi+b11State+b12Block+b13Loss+b14Rec+b15Inv+b16Year+b17Indu+μ
(1)
為了檢驗假設2,本文使用如下模型:
Auditor=a+b1Jianrenbili+b2Jianrenbili2+b3Power+b4Cfodirector+b5Ind+b6Size+b7Lev++b8Ma+b9Growth+b10Dizhi+b11State+b12Block+b13Loss+b14Rec+b15Inv+b16Year+b17Indu+μ
(2)
為了檢驗假設3,本文使用如下模型:
Opinion=a+b1Ljianrenbili+b2Hjianrenbili+b3Power+b4Cfodirector+b5Ind+b6Size+b7Lev++b8Ma+b9State+b10Loss+b11Rec+b12Inv+ b13Year+b14Indu+μ
(3)
1.被解釋變量
Dlcb為代理成本變量,是上市公司當年實際發生的營業費用與銷售費用之和占營業收入的比重,衡量上市公司管理層與股東存在的代理成本(即第一類代理成本)。
Auditor為審計師選擇,包括Auditor1(“四大”),Auditor2(綜合排名十大),Auditor3(本土十大)和Auditor4(其他),衡量上市公司當年聘請的審計師,為虛擬變量,賦值1或0。其中,“四大”是指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綜合排名十大是指“四大”和當年本土綜合排名前六大事務所;本土十大是指除“四大”外,本土當年綜合排名前十大事務所;其他是指除“四大”和本土十大之外的本土其他事務所。
Opinion為審計意見變量,是指上市公司當年財務報告獲得的審計意見。當審計意見為標準審計意見時為 1,否則為 0。
2.解釋變量
Jianrenbili為董事會兼任經理層的比例,是上市公司當年董事會成員中兼任經理層的人數占董事會人數的比例,并加入Jianrenbili2,分別用來衡量管理層的壕溝防御效應和利益協同效應。在檢驗假設3時,為了更加準確地檢驗審計師在出具審計意見時是否考慮了上市公司存在的第一類代理成本,本文借鑒 Morck等[10]的設計,以 38.5%(根據檢驗1結果算出的代理成本最高時的兼任比例)為分界點,設置了Ljianrenbili和Hjianrenbili 兩個變量。當兼任比例低于38.5%時,Ljianrenbili等于其持股比例;當兼任比例高于38.5%時,Hjianrenbili等于其持股比例與38.5%的差額,低于則等于0。
3.控制變量
從公司治理方面:(1)Power代表CEO控制權,用CEO同時兼任董事長即兩職合一衡量,兩職合一使得CEO控制權提升,可能會影響到董事會議程、提交給董事會的信息和決定董事會討論的議題等重大問題。(2)Cfodirector表示CFO兼任董事會成員。由于CFO對本公司的內部經營狀況、財務狀況和市場競爭環境等多方面情況有更為詳盡的了解,因而CFO擔任內部董事可以在經營決策、聘請外部審計師等方面具備話語權,減少信息不對稱,有利于制約經理層兼任董事會成員帶來的不良影響。(3)Ind表示獨立董事比例。Beasley和Petroni[11]發現,保險公司聘請著名事務所的可能性隨著外部董事比例的提高而增大,因而我們有理由認為,獨立董事的比例越高,代理成本越高,更傾向于聘請高質量的審計師進行審計。(4)Ma表示全部高管(包括董事、監事和高管)持股比例。管理層持股可能會影響其在決策中的風險承受能力,如果管理層持股較高,公司就越不愿意花費較高的審計費用來監督管理狀況,而非執行董事持股比例越高,公司對高獨立性審計服務的需求越強烈。(5)Block表示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動力選擇高質量審計師,降低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和代理成本。從公司特征方面:(6)Size表示公司規模大小,使用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作為替代變量。(7)Growth表示成長性。高成長性公司管理者進行機會主義行為的概率更高,越不愿意聘請高質量審計師。(8)Loss表示近兩年是否發生虧損,衡量公司的財務風險。在我國,由于連續兩年虧損的上市公司將受到特別處理的處罰,連續三年虧損將面臨退市的威脅,因而虧損公司有強烈的粉飾財務報告的動機,越不傾向于選擇高質量審計師。(9)State表示實際控制人的性質。已有的研究表明,與非國有控股公司相比,國有控股公司傾向于選擇高質量審計師,支付較高的審計費用。(10)Dizhi表示上市公司所在地。已有研究表明,經濟發達地區的上市公司愿意聘請“四大”。(11)Rec表示應收賬款占總資產的比重,Inv表示存貨占總資產的比重,兩者是審計師重點審計項目,用來衡量公司的財務風險,因此,當兩者較大時,上市公司越不愿意聘請高質量審計師。除此之外,加入Indu和Year虛擬變量控制行業、年度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
(三)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檢驗
1. 描述性統計
由描述性統計可知,Opinion均值為0.954,說明我國審計市場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比例偏低;Auditor1均值為0.061,Auditor2均值0.414,Auditor3均值0.439,Auditor4均值0.500,說明我國審計市場集中度不高,本土其他小所占據高達50%的市場;Jianrenbili均值為0.262,反映了董事會兼任經理層的比例占26.2%,與規定的不得高于2/3相距甚遠,除此之外,在較低的兼任區間,均值為0.246,在較高的兼任區間,均值為0.401。進一步,本文對全部A股上市公司董事會兼任經理層比例的分布情況進行了統計,以35%為標準,在較低的兼任區間,28.63%主要集中在5%—15%之間,在較高的兼任區間,17.35%主要集中在35%—45%,而從整體來看,55.06%集中在5%—25%之間。
在控制變量方面,Power的均值為0.213,反映了樣本中1/5多的上市公司CEO兼任董事長,說明兩職分離的上市公司占多數;Cfodirector的均值為0.218,反映了21.8%的公司CFO擔任內部董事,與總經理兼任董事長的比例差不多,說明我國上市公司CFO進入董事會的比例較低,CFO還未充分發揮其監督和戰略支持的作用;Ind的均值為 0.365,略高于所規定的獨董比例要達到董事1/3的要求,且標準差只有 0.051,說明我國A股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比例較低且沒有較大的差異;Ma均值為0.080,反映了我國上市公司管理層持股比例普遍為8.0%,對管理層的股權激勵不足;State均值為0.473,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比例稍低于非國有,說明我國上市公司的“國有”屬性已經不明顯。除此之外,其他控制變量從均值和分位數角度講總體分布正常,無異常值出現。
2. 相關性檢驗
本文對三個假設涉及的變量均進行了皮爾遜(Pearson)相關系數檢驗,由于變量較多,為了節省行文空間,沒有報告出具體結果。總體來看,除了Jianrenbili與Jianrenbili2之間相關系數為0.974,Ljianrenbili與Hjianrenbili的相關系數為0.522外,其他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并不高,大部分在0.300以下,均在0.500以下。
四、實證檢驗與分析
(一)董事會兼任經理層與代理成本、審計需求的關系
從表1可以看出,兼任比例與代理成本呈倒U型關系,說明隨著兼任比例逐步上升,經理層的掠奪效應發揮作用,表現出代理成本與兼任比例正相關,但在兼任比例進一步上升后,兼任比例的增加并不會導致經理層掠奪程度的加強,卻會使經理層利益與企業整體利益趨于一致,從而又表現出代理成本與兼任比例負相關的關系,支持假設1,對該模型進行一階求導,得出兼任比例在38.5%時代理成本達到最大。
兼任比例與“四大”、綜合排名十大、其他小所呈倒U型關系,但綜合排名十大不顯著;與本土十大呈顯著U型關系。令人驚訝的是,兼任比例與本土十大呈U型關系,而與其他小所呈倒U型關系,這與常理與假設不符,筆者認為可能是由于審計市場格局和事務所客戶群不同造成的。進一步發現,大規模公司與“四大”、綜合排名十大相匹配,小規模公司與本土十大、其他小所相匹配,符合2012年諾貝爾得主埃爾文和勞埃提出的匹配穩定理論,也與王杏芬(2015)的結論一致,也就是說,從審計市場格局來看,“四大”、綜合排名十大與本土十大、其他小所的客戶群確實不同。

表1 假設1和假設2的多元回歸結果(N=12 582)
注:***、**和*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顯著性水平;括號內為t值,下同。
本文進一步將樣本按資產分為大規模和小規模兩個子樣本檢驗,從表2和表3可以看出:(1)在大規模公司中,兼任比例與四大、綜合排名十大呈顯著倒U型關系,與本土十大、其他小所的關系不顯著,即代理成本越高越傾向于選擇“四大”和綜合排名十大,說明大規模公司對“四大”、綜合十大具有品牌認同度,但由于綜合排名十大的顯著性低于四大,因此,與國內大所相比,大規模公司更加認同“四大”。(2)在小規模公司中,兼任比例與本土十大呈顯著U型關系,與其他小所呈顯著倒U型關系,與預期不一致。一種可能是小規模公司認為本土十大并沒有提供高質量的審計服務,代理成本越高越不傾向于選擇本土十大,寧愿選擇國內小所;另一種可能是小規模公司內部人控制嚴重,董事會形同虛設,經理層掌握聘任審計師的權力,為了便于權力尋租,避免聘請本土十大,而選擇小所。但是我們注意到,無論在全樣本還是子樣本中,CEO與董事長兩職合一與“四大”、其他小所呈負相關關系,而與綜合排名十大、本土十大呈正相關關系,由此,CEO權力較大時更傾向于選擇本土大所,這是因為選擇本土大所一舉兩得:一方面,與“四大”相比,本土大所獨立性差,審計師擔心失去市場份額等而在審計聘任契約關系中明顯處于弱勢地位,經理層更容易與審計師形成審計合謀侵害投資者的利益;另一方面,與其他小所相比,本土大所審計質量的市場認同度更高,擁有良好的信號顯示效應。此外,管理層持股與“四大”、其他小所呈負相關關系,而與綜合排名十大、本土十大呈正相關關系,也呼應了這個說法。由此我們有理由懷疑本土大所沒有提供高質量的審計服務,而是與經理層勾結,進行審計合謀。

表2 大規模公司:董事會兼任經理層比例與審計需求的關系(N=5 718)

表3 小規模公司:董事會兼任經理層比例與審計需求的關系(N=6 864)
(二)不同審計師的治理效果差異:董事會兼任經理層與審計意見類型的關系
為更加確切地檢驗審計師是否在出具審計意見時考慮了上市公司存在的第一類代理問題,這一部分本文采了 Morck等[10]的分段回歸法,區分兼任比例的兩面性,即對不同區間內兼任比例的效應采用不同的變量來反映。具體表現為:在較低的兼任比例上,經理層的壕溝防御效應占主導地位;而在較高的兼任比例上,經理層的利益協同效應占主導地位。由于在前面的檢驗中得出董事會兼任經理層比例在38.5%時代理成本達到最高,因此,本文以38.5%作為分界點。
從表4可以看出,在全樣本回歸中,代表董事會兼任經理層的兩個變量符號與預期相反,其中,Ljianrenbili在10%水平下顯著,而Hjianrenbili的反向相關并不顯著。說明在兼任比例低于38.5%時,隨著兼任比例的增加而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可能性越小,也就是經理層的掠奪效應越強,越容易獲得標準審計意見;而在兼任比例高于38.5%時,兼任比例與審計意見不存在顯著關系。因此,從整體來看,由于受被審計單位存在的第一類代理成本影響,我國審計師難以出具客觀的審計意見,沒有很好地起到監督約束經理層尋租行為的作用。在“四大”子樣本中,兼任比例變量有著同全樣本類似的影響,但是不具有顯著性,這說明“四大”在出具審計意見時受被審計單位經理層影響較小,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獨立性。在綜合排名十大和本土十大的子樣本中,兼任比例變量與審計意見均呈顯著倒U型關系,且綜合排名十大比本土十大的顯著性更強。由此可以認為本土大所,特別是本土前六大,更容易與被審計單位經理層合謀,代理成本越大越傾向于出具標準審計意見。進一步呼應和解釋了前面的回歸結果:(1)兼任比例變量與本土十大呈顯著U型關系,即代理成本越大,公司越不愿意聘請本土十大。(2)CEO與董事長兩職合一與綜合排名十大、本土十大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兩職兼任的公司更愿意選擇綜合排名十大和本土十大。在其他事務所的子樣本中,Hjianrenbili與Opinion正相關,與預期一致,Ljianrenbili與預期的符號相反,均不顯著,一定程度上說明其他小所在出具審計意見時考慮了上市公司存在的代理問題,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沒有選擇與經理層進行審計合謀。

表4 董事會兼任經理層比例與審計意見類型的關系
在控制變量方面,筆者發現,無論在全樣本還是子樣本中,Power、Ind和State對Opinion均沒有影響;Size與Opinion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即公司規模越大,獲得標準審計意見的概率越高;Lev和Loss與Opinion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說明審計師對負債比例高、存在財務困境的公司更傾向于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另外,除了“四大”的子樣本外,Inv與Opinion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但方向與預期不一致,而在“四大”子樣本中,兩者呈負相關關系,但不顯著。可能的原因是,在目前的法律環境下,審計師的風險意識不強,除“四大”外,其他審計師在審計中較少考慮到相關的風險因素。
因此,從總體來看,較本土大所而言,“四大”和其他小所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經理層權力對其出具的審計意見類型影響較小,“四大”和其他小所分別在不同的客戶群中對經理層的尋租行為起到一定的監督制約作用。而本土大所是經理層掩蓋其掠奪行為和權力尋租的首要選擇,本土大所無法提供高質量的審計服務。
五、穩健性檢驗
對于假設2,采用Morck等[10]的分段回歸法,即用Ljianrenbili和Hjianrenbili代替Jianrenbili和Jianrenbili2代入模型(2)檢驗。結果發現,Ljianrenbili與Auditor1不再顯著,造成這種現象的可能原因是,在較低的兼任區間,兼任比例主要集中在5%—15%,這一區間由于代理成本較低,壕溝效應不明顯,因而對高質量審計的需求有限,但不影響整體趨勢。
采用Jianrenbili和Jianrenbili2代替Ljianrenbili和Hjianrenbili代入方程檢驗,同時,從假設3的回歸結果來看,Power、Ind和State無論在全樣本還是子樣本中均不具有顯著性,即對審計意見沒有顯著影響,因而將其剔除。結果發現:在其他本土小所的子樣本中,Ljianrenbili與Opinion關系符號發生了變化,即兼任比例與審計意見呈U型關系,進一步說明了其他本土小所在出具審計意見時考慮了上市公司存在的第一類代理成本。其他主要變量沒有發生變化,說明結論具有穩健性。
為了克服審計師自選擇問題,我們采用Heckman兩階段模型來考察不同審計師審計的公司兼任比例與審計意見的關系。第一階段,根據以往研究,選取Size、Lev、Loss、Growth及Ma與Auditor1、Auditor2、Auditor3和Auditor4進行Probit回歸,并分別計算出Lambda值。第二階段,將Lambda值代入模型(3)進行多元回歸,主要變量沒有發生變化,同時Lambda系數不顯著,說明結論具有穩健性。
六、結論與啟示
首先,從審計需求角度,董事會兼任經理層的比例與代理成本、高質量外部審計呈倒U型關系,說明董事會與經理層兼任導致的代理成本是影響企業外部審計需求的重要因素。具體來說:兼任比例與四大、綜合排名十大和其他小所呈倒U型關系,但綜合排名十大不顯著,與本土十大呈顯著U型關系。進一步發現,不同事務所的客戶群不同,即大規模公司與“四大”、綜合排名十大相匹配,小規模公司與本土十大、其他小所相匹配。其中,在大規模公司中,兼任比例與四大、綜合排名十大呈顯著倒U型關系;在小規模公司中,兼任比例與本土十大呈顯著U型關系,與其他小所呈顯著倒U型關系。可以看出,我國上市公司對本土大所不具有品牌認同度。另外,CEO和董事長兩職合一、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四大、其他小所呈負相關關系,與綜合排名十大、本土十大呈正相關關系,說明本土大所是經理層掩蓋其掠奪行為和權力尋租的首要選擇。
其次,從審計供給角度,我國整個審計市場質量不高,審計師獨立性不強,還不能很好起到監督的作用。具體來說:較本土大所而言,“四大”和其他小所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分別在不同的客戶群中對經理層權力發揮了一定的監督制約作用。而本土大所,特別是本土六大更容易與被審計單位經理層合謀,無法出具客觀的審計意見。
最后,從整體來看,在我國資本市場上,上市公司愿意引入高質量的審計作為一種有效的治理機制,且上市公司能夠識別審計師的質量,即上市公司并不認同“事務所規模越大審計質量越高”。但整個審計市場的質量不高,尤其是本土大所可能與經理層存在合謀行為,出具有利于經理層的審計意見欺騙外部投資者。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完善市場法律環境,加大懲罰力度,促進審計事務所增強獨立性,嚴格監管經理層與外部審計師之間的合謀行為,引導審計市場健康有序的發展。
[1] Jensen,M.,Meckling,W.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4):305-360.
[2] Simunic, D.A. The Pricing of Audit Services: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80,18(1):161-190.
[3] Firth,M., Smith,A. Selection of Auditor Firms by Companies in the New Issue Market[J]. Applied Economics, 1992,24(2):247-255.
[4] Eichenseher,J.W.,Hagigi,M.,Shields,D.Market Reaction to Auditor Changes by OTC Companies[J].Auditing,1989,9(1):29-40.
[5] 曾穎,葉康濤.股權結構、代理成本與外部審計需求[J].會計研究,2005,(10):63-70.
[6] 李明輝.代理成本與審計師選擇——基于中國IPO公司的研究[J].財經研究,2006,(4):91-102.
[7] 王燁.股權控制鏈、代理沖突與審計師選擇[J].會計研究,2009,(6):65-72.
[8] 周中勝,陳漢文.大股東資金占用與外部審計監督[J].審計研究,2006,(3):73-81.
[9] 李海燕,厲夫寧.獨立審計對債權人的保護作用——來自債務代理成本的證據[J].審計研究,2008,(3):81-93.
[10] Morck,R., Shlifer ,A., Vishny, R. Management Ownership and Market Valuat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8,20(1-2):293-315.
[11] Beasley, M. S.Petroni,K.R. Board Independence and Audit Firm Type[J].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2001,20(1):97-114.
(責任編輯:楊全山)
2017-09-18
郭 林(1987-),男,北京人,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上市公司財務研究。E-mail:123710489@qq.com
F037.1
A
1000-176X(2017)11-006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