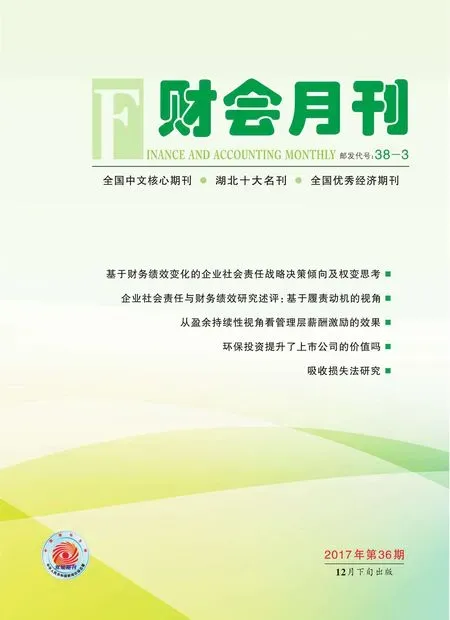關于綜合收益的風險相關性研究
——基于我國A股上市公司
趙 艷(博士),劉玉冰
關于綜合收益的風險相關性研究
——基于我國A股上市公司
趙 艷(博士),劉玉冰
以2009~2014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數據為研究樣本,利用實證分析方法研究綜合收益波動性和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對企業估值風險的影響。研究表明:綜合收益波動性以及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與企業股票回報波動性和β值顯著正相關,說明綜合收益與其他綜合收益具有風險相關性,且綜合收益波動性和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會降低非正常收益的估值作用;進一步研究發現,在較好的地區制度環境下,其他綜合收益的風險相關性更強。
綜合收益;其他綜合收益;風險相關性;回報波動性;市場模型β值
一、引言
綜合收益的概念最初由美國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于1980年在第3號財務會計概念框架“財務報表要素”中提出,其取代傳統收益表反映企業財務業績已然成為各國會計準則機構業績報告改革的趨勢。綜合收益報告突破了實現原則的限制,在一張財務報表中既包括企業已實現的利得和損失,又包含未實現的利得和損失。綜合收益報告被認為能使報告的收益更全面和真實,有助于使用者做出合理的經濟決策。相對于西方國家,我國證券市場起步較晚,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相對滯后,同時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應用的限制等因素阻礙了綜合收益報告的應用與發展,直到2009年我國財政部才在《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3號》中要求上市公司在利潤表中補充披露其他綜合收益和綜合收益的信息。改革業績報告的目標是要求報告反映更全面、更有用的財務業績信息,以滿足使用者投資、信貸及其他經濟決策的需要。因此,關注綜合收益信息的決策有用性是檢驗業績報告改革是否成功的切入點,能為準則制定者提供經驗證據,并有助于信息使用者更好地解讀綜合收益信息。
現有文獻主要通過綜合收益價值相關性以及其他綜合收益的增量價值相關性來解釋綜合收益及其他綜合收益信息對投資者的決策有用性,但鮮有實證研究對綜合收益和其他綜合收益信息的風險相關性進行考察。會計概念第8號公告(SAC No.8,2010)指出,決策有用的信息能幫助投資者評估企業未來凈現金流量的數額、產生時間和不確定性,這里明確地界定了決策有用信息的評判標準,即有助于投資者對企業回報和風險評估的信息才是決策有用的信息。Easton、Zmijewski(1989)的研究證實了盈余和回報的關系會受到兩個重要因素的影響,即盈余持續性和風險。
因此,綜合收益決策有用性的研究不僅僅是價值相關性研究,還應包括風險相關性研究。一方面,價值相關并不一定意味著風險相關,價值相關性大多使用財務報表項目和股票價格或股票回報之間關系的強弱來衡量,風險相關性則多采用財務報表項目時間序列的波動性和股權回報的時間序列波動性之間的關系來衡量。這意味著,企業基本面信息的變化引起了股價的變化(價值相關),但股價變化可能并不會導致股權回報的波動(風險相關)。簡而言之,價值相關性主要解釋了會計信息對投資者回報的影響,而風險相關性主要解釋了會計信息對企業估值風險的影響。另一方面,我國漸進式的經濟發展路徑造就了地區發展的顯著差異,各省市之間在政府行政管理、企業經營的法律環境和金融服務等經營環境方面差異較大。制度環境對組織結構及效率的影響是公司治理最重要的研究領域之一,Ball等(2000)認為不同制度環境下對會計盈余需求的不同是影響會計盈余特性的重要因素。那么,其他綜合收益信息的風險相關性是否會因為地區制度環境的差異而表現出差異?因此,本文從綜合收益和其他綜合收益的波動性與市場風險以及公司特定風險的關系入手,進一步考察不同的制度環境是否會影響其他綜合收益的風險相關性,并在制度環境差異的背景下,從風險相關性的角度探討綜合收益信息對投資者決策的有用性。
二、文獻回顧
相對于檢驗股票價格(股票回報)與綜合收益(其他綜合收益)關系的豐富文獻,檢驗投資者估值風險和綜合收益關系的文獻則相對較少。自綜合收益概念出現之后,包含了未實現利得和損益的綜合收益是否會增加盈余的波動性一直是被討論的熱點問題。Barth等(1995)通過使用1971~1990年銀行數據研究發現,使用公允價值會計計量方法之后:一是包含了投資證券未實現利得和損失的盈余比一般公認會計原則(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簡稱“GAAP”)的盈余的波動性更大,且這種計量方法下的“公允價值盈余”的增量波動性不能被投資者定價;二是資本監管違法行為在公允價值會計下比在GAAP下更易發生,公允價值會計下的資本監管違法行為可以預測實際的資本監管違法行為,但是投資者無法對這種風險進行評估。本文認為在公允價值會計下,所有資產負債表賬戶用公允價值計量的收益波動性是經濟風險的更好的代替變量。
西方的主要會計準則機構在要求披露綜合收益之初,允許企業從在業績報表中補充披露與在股東權益變動表中披露這兩種方式中做出選擇,引起了學者們對不同披露方式是否會影響綜合收益的波動性以及投資者估值的一系列研究。盡管一些經理們擔心在業績報表中披露綜合收益會加大綜合收益的波動性,但Lee等(2006)沒有發現證據證明在業績報表中披露綜合收益會減少綜合收益相對于凈利潤的波動性,這與經理們可能想在股東權益變動表中“隱藏”綜合收益波動性的觀點是相反的。Maines、McDaniel(2000)分析了綜合收益的披露方式如何影響非專業投資者對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得和損失的波動性評估,以及這些波動性評估又如何影響投資者對股票風險的評估,研究發現,無論綜合收益如何披露,保險公司的非專業投資者都能夠識別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得和損失的波動性。但是當綜合收益在業績報表中披露時,投資者對股票風險的評估表現出對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得和損失更高的識別能力。這一發現說明綜合收益可以幫助投資者評估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得和損失相關的風險,并且當綜合收益在業績報表中披露時更有助于投資者評估企業的風險。此外,這項研究還證明了經理們對投資者將高波動性的企業評估為高風險企業的關注。
Bloomfield等(2006)使用MBA學生作為實驗對象,檢驗了在市場環境的試驗中,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得和損失與回報之間的反饋關系是否會引起股價的波動并導致投資風險,發現當企業投資較高以及未實現利得和損失在綜合收益表(業績表)中報告時,價格波動是最高的。Koonce(2006)在對Bloomfield等(2006)的研究的討論中認為,這項研究中的投資者可能沒有能力來調整他們基于相關投資結構的估值決策,也就是說非專業的投資者,可能不能在他們的價值評估之前針對未實現的利得和損失對投資者回報和風險的影響來調整每股盈余。
為數不多的文獻在比較凈利潤波動性和綜合收益波動性的基礎上,進一步檢驗了綜合收益波動性與回報波動性(或β值)的相關關系。如Hodder等(2006)對1996~2004年美國商業銀行樣本使用了三種不同的收益計量方法(凈利潤、綜合收益和充分公允價值收益(full-fair-value income),檢驗了回報波動性和收益波動性,以及股本成本和收益波動性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綜合收益比凈利潤的波動性更強,并且凈利潤波動性和綜合收益波動性都與回報波動性以及長期利率β值正相關;然而,綜合收益波動性與股票市場β值顯著負相關,凈利潤波動性與股票市場β值不相關;增量綜合收益波動性(綜合收益波動性和凈利潤波動性之差)與回報波動性不相關,與股票市場β值顯著負相關,與長期利率β值不相關。
Hodder等(2006)還發現了綜合收益增量波動性(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的代理變量)不能幫助投資者對非正常收益折現,與潛在的股本成本也不相關。由于金融企業和非金融企業的商業模式是完全不同的,Khan和Bradbury檢驗了非金融企業兩個樣本的收益風險相關性。Khan、Bradbury(2012)檢驗了新西蘭企業的樣本,研究發現大約三分之二的樣本企業綜合收益比凈利潤的波動性更強,然而,當綜合收益扣除了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允許但美國會計準則(U.S.GAAP)不允許的不動產、廠房和設備的重新估價進行調整之后,這個比例僅有57%。他們沒有找到證據證明綜合收益的增量波動性或者扣除資產重估的綜合收益增量波動性與回報波動性或市場模型β值是相關的,也沒有找到證據證明投資者使用了這些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所傳遞的信息來折現非正常收益。Khan、Bradbury(2014)利用美國的非金融企業的樣本實施了與他們2012年論文中相似的檢驗,發現了增量的綜合收益波動性與回報波動性或CAPM模型β值不相關,以及沒有被用來折現非正常盈余。他們還提供了描述性證據表明綜合收益和所有的其他綜合收益組成項目比凈利潤的波動性更大。
綜上可以發現,目前對綜合收益波動性大于凈利潤波動性的觀點已基本達成一致,但沒有得到綜合收益波動性和風險之間的穩定(或沒有)關系。目前各國會計準則機構已紛紛取消在股東權益表中報告其他綜合收益和綜合收益的披露方式,經理們擔心包含在業績報告中的其他綜合收益會使投資者迷惑,導致會計業績更加波動,從而產生更加波動的回報,因此可通過檢驗綜合收益組成項目的波動性與投資者的股票回報波動性(以及β值)之間的相關性來深入了解綜合收益波動性對估值風險的影響。而國內外研究綜合收益和其他綜合收益風險相關性的文獻較少,更鮮有文獻結合制度背景對該問題進行探討,因此本文研究是對綜合收益信息投資決策有用性方面的有益補充。
三、綜合收益風險相關性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風險、綜合收益波動性和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根據決策理論,理性投資者在進行決策時會選擇產生最大期望效用的行為,這里同時假定投資者是風險規避的,這意味著投資者在對企業進行估值時,同時需要有關風險和未來收益期望值的信息。資本市場研究已調查了會計數字對評估證券和投資組合風險的有用性,如Beaver等(1970)的經驗證據表明收益的變異程度、資產增長率、財務杠桿等7個會計變量對預測系統風險非常有用。此后的研究不斷擴大被檢驗的會計變量的范圍。Hamada(1972)和Lev(1974)的研究分別構建了系統風險與財務杠桿、營業杠桿之間的理論模型。Ismail、Kim(1998)的研究為會計信息對風險溢價的解釋能力提供了經驗證據。以往研究表明會計盈余信息可以用來評估風險。
關于SFAS 130(報告綜合收益)草案的一個主要焦點是投資者如果依據其他綜合收益的增量波動性是否可得到關于企業風險的推斷。如Graham、Harvey和Rajgopal's(2005)在他們的調查報告中指出,一些CEO認為當盈余更加波動時,市場對潛在的現金流更加不確定,即使兩家企業擁有相同的潛在現金流波動,CEO們仍然認為盈余波動性大的企業其風險更高。管理者們似乎也都一致認為擁有更大波動性的其他綜合收益項目的企業會被評價為“高風險者”(FASB,1997)。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30號——財務報表列報》(CAS 30),綜合收益包括凈利潤和其他綜合收益。其他綜合收益是指企業根據其他會計準則規定未在當期損益中確認的各項利得和損失,這些項目主要源于兩個方面,一個是公允價值的變化,另一個是管理層估計、精算假設以及準則機械運用的結果。在我國現行的會計準則規范和資本市場環境下,公允價值變化原因引起的其他綜合收益是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因此公允價值變化導致的波動性也是導致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最主要的原因。綜合收益波動性和其他綜合收益的波動性會影響未來現金流的不確定性,從而會與企業估值風險存在一定的關聯關系,企業未來現金流的不確定性也會影響投資回報的波動性,因此會對投資者決策產生影響。
現有的幾篇文獻對財務報表項目的波動性一直采用項目企業層面、時間序列的標準差來衡量。Hodder等(2006)和 Khan、Bradbury(2012、2014)的研究都發現了綜合收益波動性與回報波動性之間的正向相關關系,表明了綜合收益是風險相關的。這三篇文獻采用綜合收益波動性減去凈利潤的波動性衡量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結果顯示這種衡量方法下的其他綜合收益增量波動性與風險是不相關的。
本文從兩個方面延伸了他們的研究:①對于風險的衡量采用了兩種方法,第一種方法仍然采用之前研究對風險的衡量,使用回報波動性。因為回報波動性信息是關于投資者對未來現金流不確定的信息,概念框架中明確指出企業回報以及回報的變化和組成的信息對投資者是重要的,“尤其是在評價未來現金流的不確定性的時候”(FASB,2010)。第二種方法本文采用CAPM模型回歸得到的β值來衡量公司特定的風險,因為β值是投資理論中重要的證券風險計量指標,它衡量的是單一證券價格和市場組合的市價之間的同步變化關系。股票的β值在財務會計信息對投資者有用性的研究中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披露公司風險的“起始點”。Beaver等(1970)第一次研究了β值和基于財務報表的風險指標(股利支付率、杠桿系數和收益波動)之間的關系,發現會計風險指標能更及時地反映β值的變動。因此,本文同時檢驗了綜合收益波動性(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與股票回報波動性以及β值之間的關系,以此來驗證綜合收益和其他綜合收益是否具有風險相關性。②本文直接計算了其他綜合收益的波動性,而不是使用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的代理變量。如果綜合收益的波動性和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與回報波動性或β值是正向相關的,則說明綜合收益(其他綜合收益)反映了風險相關的信息。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綜合收益波動性、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與股票回報波動性是正向相關的。
H2:綜合收益波動性、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與CAPM模型β值是正向相關的。
根據Ohlson模型,權益市場價值是權益賬面價值、非正常收益和其他信息的線性函數。非正常收益等于實際收益減去預期收益。公式如下:
ARit=Rit-E(Rit)
預期收益(正常收益)根據市場模型確定:

如果收益波動捕捉了資本市場價格的風險因素,那么收益的波動性越高,風險就越大,要求的期望收益就越高,從而降低了非正常收益的估值作用。另外,盈余波動性越大,盈余質量就越低,本身就會降低盈余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因此可推斷,由于綜合收益和其他綜合收益的波動性,導致了風險的增加,從而降低非正常收益的估值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3:綜合收益波動性以及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會降低非正常收益的估值作用。
2.制度環境對其他綜合收益風險相關性調節效應的理論分析。不同的制度環境因素決定了企業面臨的市場和政府的影響是不同的,面對不同的外部制度環境,企業管理者提供的會計信息質量就會有所差異,相應的會影響到不同制度環境下企業會計信息的有用性。一個國家的法律或司法制度會影響會計數據的屬性,會計信息系統在制度環境對投資者保護的分析框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資本市場信息的不對稱,投資者保護主要有兩個基本問題:信息問題和代理問題。會計信息作為公司信息的主要來源,在投資者保護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會計信息的定價功能有助于緩解信息不對稱,幫助投資者做出正確決策,其次會計信息的治理功能可以降低代理成本,約束管理者的機會主義行為,保障投資者獲取收益。本文從投資者保護的角度,采用了兩種路徑依賴分析不同地區的制度環境對其他綜合收益風險相關性的影響。
第一種路徑依賴的理論分析依據是制度環境的“后果觀”假說,該假說強調了制度環境在財務會計信息系統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制度環境較好的地區意味著法律對投資者和債權人的保護程度較高,根據以往的研究,制度環境較好地區的股權結構較為分散,資本成本較低,公司的價值較高,而這也會導致投資者與管理者之間更為嚴重的代理沖突,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則能夠幫助緩解由于信息不對稱引發的代理問題(Ball等,2000),在這種情況下,管理者基于契約的約束以及自身代理成本的考慮,自愿披露高質量會計信息的動機就比較強。同時,由于法律環境較好的地區對于投資者和債權人的保護程度較高,不僅使會計準則規范的執行更加有效,強制性地保證了較好的會計信息質量,還增大了管理者面臨的法律訴訟風險,使管理者愿意主動披露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因此,在制度環境較好的“后果觀”假說下,管理者無論出于自愿還是強制性動機都愿意提供高質量的會計信息。
第二種路徑依賴的理論分析依據是會計信息對制度環境的“替代機制”假說,會計信息的“替代機制”假說強調的是在投資者法律保護較差的地區,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可以作為一種弱化較差的投資者保護的制度環境帶來的負面效應的替代機制。La Porta R.等(1998)在分析不同地區法律保護差異時,提出投資者保護較弱的國家是否具有其他替代機制來解決這一問題。他們注意到國家的財務會計系統可能是這樣的一種替代機制,其可以為投資者提供公司經營運作的信息,為簽訂契約提供可證實的信息,并推測高質量的會計系統能夠減輕金融市場發展中弱投資者保護帶來的負面效應,即高質量的會計系統能夠替代弱投資者法律保護并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陳勝藍、魏明海(2006)在使用我國上市公司數據對會計穩健性的跨地區制度環境的比較研究中發現,財務會計系統能夠補償較弱的投資者保護帶來的負面效應。因此,在制度環境的“替代機制”下,較差制度環境需要提供高質量的會計信息來弱化較差制度環境對投資者和債權人決策有用性的負面影響。綜上,地區制度環境和會計信息之間關系的兩種相互競爭的理論分析的基本邏輯是“制度環境—會計信息質量—會計信息的有用性”。
我國的制度改革是漸進式的,根據王小魯等(2013)對2006~2012年我國分省企業經營環境的調查分析,東部地區在政府行政管理、企業經營的法律環境和金融服務等經營環境各方面的指數都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區的各方面指數一直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各省市之間的經營環境差異較大,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蘇和山東一直是排名靠前的省份,而且位次相對較為穩定,排名靠后的省份如新疆、寧夏、青海等也基本上是中西部地區。相對于經營環境較好的地區,在企業經營環境相對較差的地區,政府的干預程度更大,地方保護主義更嚴重,金融市場的競爭不充分,甚至不發達,缺乏相應的金融人才、金融工具和融資技術創新;同時,有關企業估值的信息更不易于獲取,信息的不確定更大且可靠性更差,企業與會計信息的主要使用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更嚴重,投資者對于通過市場機制獲取企業相關信息并做出有效評價存在一定的障礙。
基于我國企業制度環境存在的地區差異以及地區制度環境和會計信息之間關系的兩種相互競爭的理論分析,本文以其他綜合收益信息為研究對象提出兩個相互競爭的假設:
H4a: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制度環境對其他綜合收益風險相關性的調節作用符合制度環境的“后果觀”假說。
H4b: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制度環境對其他綜合收益風險相關性的調節作用符合制度環境的“替代機制”假說。
四、研究設計
1.研究樣本與數據來源。本文選擇的樣本集中于存在其他綜合收益的上市公司。鑒于我國財政部在2009年6月發布的《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3號》首次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其他綜合收益項目,本文選擇2009~2014年在我國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作為初始樣本,剔除ST類公司、所有者權益為負值的公司、審計意見為非標的公司以及數據缺失的公司,共得到11248個觀測值。其中,約44%的樣本公司在樣本期間報告了其他綜合收益,得到4930個研究觀測值。由于計算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需要連續滾動三年的數據,因此風險相關性研究的樣本在價值相關性研究樣本選擇的基礎上,將樣本年度界定為2011~2014年,刪除市場風險缺失值后,共得到2114個觀測值。制度環境與其他綜合收益風險相關性模型的樣本期間選擇為2009~2012年(截止到2012年的原因是王小魯、余靜文和樊綱2013年發布的《中國分省企業經營環境指數2013年報告》的公司經營環境指數截止到2012年),共得到2103個公司的年度觀測值。
本文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和RESSET數據庫。為消除異常值的影響,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了Winsorize(1%)極端值處理。
2.回歸模型和變量定義。根據研究假設,借鑒Hodder等(2006)和 Khan、Bradbury(2014)的風險相關模型,本文使用如下模型來檢驗綜合收益波動性和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相對于凈利潤波動性)與市場風險的增量關系:

模型中MRProxyj是j企業市場風險的替代變量,本文采用兩種方法來衡量市場風險:股票回報波動性和β值。股票回報波動性是總體風險的替代變量,采用2011~2014年期間連續滾動三年股票回報的標準差來衡量。β值是系統風險的替代變量,本文使用2011~2014年前60個月的股票回報與流通市值加權的市場回報對CAPM模型進行回歸來估計β值,并使用2011~2014年期間的周股票回報率和流通市值加權周市場回報率對CAPM模型進行回歸估計β值,且進行穩健性測試。σCI、σNI和σOCI衡量的是CI、NI和OCI波動性,通常采用收益的標準差來衡量(如Dechow等,2010),本文使用2011~2014年連續滾動三年的經平均總資產標準化的CI、NI和OCI的標準差作為CI、NI和OCI的波動性的替代變量。
為了控制其他會計變量對市場風險的影響,本文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控制了會計指標基礎的風險變量(ARIndexj),并采取兩種方法來衡量。①第一種方法,選取債務權益比(DE)作為資本結構導致的違約風險的替代變量,選取經營活動現金流與流動負債比值(CF)作為流動風險的替代變量。已有文獻已經驗證了風險與財務杠桿的相關性,二者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Beaver等,1970;Bradley等,1984)。②第二種方法,采用Z分數模型計算出的Z值衡量企業的財務風險,Z分數模型選定了5個指標,從企業的獲利能力、財務結構、償債能力等方面綜合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Z值越小,企業遭受財務失敗的風險可能性越小。Altman(1968)檢驗出Z分數模型對臨近財務失敗的企業預測的準確度為96%。
為了檢驗股價中是否反映了收益的波動,即收益波動是否是導致股價降低的一個因素,本文借鑒了Hodder等(2006)的研究,構建如下檢驗模型:

其中:P表示j企業的每股股價;BVE表示j企業的每股權益賬面價值;AE表示j企業每股非正常收益,非正常收益采用Hodder等(2006)的計算方法,即當期每股盈余減去期初無風險回報率與期初每股權益賬面價值的乘積。具體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定義
為檢驗制度環境對其他綜合收益風險相關性的調節作用,在模型(1b)的基礎上添加了制度環境變量與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的交互項,構建模型(3a)和模型(3b)進行分析:

依據王小魯、余靜文和樊綱2013年發布的《中國分省企業經營環境指數2013年報告》,選取“政府減少不必要干預”分項指標、“企業經營的法制環境”方面指數、“金融服務”方面指數以及“經營環境”總指數作為制度環境的替代變量。由于該報告僅披露了2006、2008、2010和2012年的相關數據,本文借鑒李虹、田馬飛(2015)的方法,采用最近兩年的平均增長率計算2009~2012年的企業經營環境指數。具體變量解釋如表2所示。

表2 制度環境變量定義
五、實證結果與分析
1.描述性統計。下圖描述了2009~2014年綜合收益、凈利潤和其他綜合收益的時間序列值,可以直觀地看出綜合收益的波動性要大于凈利潤的波動性,且其他綜合收益在2009~2010年大幅度下降,可能原因是公允價值被認為是2008年金融危機加劇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企業在公允價值計量屬性下確認的未實現利得和損失。

CI波動性和NI波動性年度變化(n=2114)
表3 Panel A列示了風險相關模型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綜合收益波動性(σCI)的均值是0.12,凈利潤波動性(σNI)均值是 0.09,從橫截面來看,綜合收益波動性的均值大于凈利潤的波動性。從評價綜合收益相對于凈利潤波動性的指標(σCI/σNI)來看,σCI/σNI的均值為1.62,說明綜合收益波動性比凈利潤波動性高62%。其中,綜合收益波動性大于凈利潤波動性的樣本值為1270(σCI/σNI>1) ,占 比60.08%;綜合收益波動性小于凈利潤波動性的樣本值為844(σCI/σNI<1),占比 39.92% ,且不存在綜合收益波動性等于凈利潤波動性的企業。股票回報波動性(σRet)的均值(0.13)大于中位數(0.03),樣本呈右偏。市場β值的均值等于中位數,呈正態分布。Panel B列示了制度環境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可以看到,四個制度變量的均值與其中位數非常接近,說明樣本基本呈現正態分布。


表4 模型(1)的回歸結果
2.回歸分析。表4報告了其他綜合收益風險相關性的回歸結果。第(1)~(4)欄列示了綜合收益波動性、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對股票回報波動性影響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σCI、σNI和σOCI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綜合收益波動性和在凈利潤波動性基礎上的其他綜合收益增量波動性與股票回報波動性正向相關,即綜合收益波動和其他綜合收益波動均反映了和市場風險相關的風險因素,但綜合收益波動性和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的系數均小于0.05,對市場風險相關的風險因素反映較弱,H1得到了驗證。第(5)~(8)欄列示了綜合收益波動性、其他綜合收益波動行對股票β值影響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σCI、σNI和σOCI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綜合收益波動性和在凈利潤波動性基礎上的其他綜合收益增量波動性與股票β值正向相關,即綜合收益波動和其他綜合收益波動均反映了和公司特定風險相關的風險因素,但綜合收益波動性和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的系數均小于或等于0.005,對公司特定風險影響也較小,H2得到了驗證。衡量會計指標基礎的風險變量DE、CF以及財務風險指標Zcore的系數均為正,與預期結論一致,表明會計指標基礎的風險測量均能反映與企業估值風險相關的風險因素。
表5的檢驗結果顯示AE的系數均顯著為正,驗證了會計盈利的價值相關性。交互項σCI×AE、σNI×AE和σOCI×AE的系數均顯著為負,說明綜合收益波動性以及在凈利潤波動性基礎上的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會降低非正常收益的估值作用,H3得到了驗證。交互項DE×AE、CF×AE和Zscore×AE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對于具有較高會計風險的企業,市場分配的非正常收益資本化的金額較低。

表5 模型(2)的回歸結果
由表6第(1)、(3)、(5)和(7)欄可知,無論會計指標基礎的風險變量在以債務權益比和經營活動現金流與流動負債比來衡量,還是以Z值衡量的情況下,OCI×G_index、OCI×L_index和OCI×F_index的系數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由第(2)、(4)、(6)和(8)欄可知,OCI×C_index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結果表明,企業受政府干預越少、企業所處地區法律環境越好、金融市場越發達,以及企業所處地區的社會經營環境總指數越高時,其他綜合收益在凈利潤基礎上的增量風險相關性就越高。本文提出的H4a得到了驗證。
3.穩健性檢驗。為了驗證綜合收益風險相關性研究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采用了如下方法進行穩健性測試:①首先對股票回報波動性、綜合收益波動性、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凈利潤波動性和股票β值進行變量替換,借鑒Hodder等(2006)的做法,以連續滾動5年期間來計算σRet、σCI、σNI和σOCI,樣本期間縮短為2013~2014年。股票β值采用2011~2014年期間的周股票回報率和流通市值加權周市場回報率對CAPM模型進行回歸來重新估計β值。檢驗結果見表7,結論與前文一致。②對于綜合收益波動性和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對股價影響的穩健性測試,將股價(P)進行變量替換,為了減少股價漂移現象對回歸結果的影響,本文采用5月最后一個交易日前復權的股票收盤價作為因變量,檢驗結果見表8,研究結論保持不變。
同時,為了增強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本文進一步以王小魯、余靜文和樊綱(2016)年在《財經》雜志(2016年第47期)發表的《中國市場化八年進程報告》中2009~2014年的市場化指數,作為制度環境的替代變量,并將樣本期間擴展至2009~2014年(由于篇幅所限,檢驗結果省略)。結果發現當市場化指數作為制度環境替代變量時,市場化指數越高,其他綜合收益的風險相關性越大,同樣驗證了制度環境的“后果觀”假說。
六、研究結論與啟示
1.研究結論。本文實證檢驗了在我國會計制度和資本市場環境下綜合收益和其他綜合收益的風險相關性。研究發現:綜合收益波動和其他綜合收益波動均反映了企業估值風險中的風險因素,并且綜合收益波動性和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會降低非正常收益的估值作用。地區制度環境的差異對其他綜合收益風險相關性的研究結果表明,較好的地區制度環境(政府干預程度較低、地區法律環境較好、金融市場較發達,以及企業所處地區整體經營環境較好),顯著增加了其他綜合收益的增量風險相關性。說明在我國特定的地區環境差異下,制度環境在財務會計信息系統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即在較好的制度環境下,管理者無論出于自愿還是強制性動機都愿意提供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其他綜合收益信息的決策有用性和契約有用性也就比較高。

表6 制度環境對其他綜合收益風險相關性的影響

表7 綜合收益和其他綜合收益風險相關性回歸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制度環境的“替代機制”假說沒有得到驗證,但是應該明確的是制度環境與會計系統之間的關系是動態變化的,并非“一成不變”的,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后果觀”假說和“替代機制”假說也有可能同時成立,制度環境與會計信息系統在我國資本市場的投資者和債權人保護中可以是一種相機選擇機制,兩者之間的關系由我國資本市場參與者的理性決策力量最終決定。
2.啟示。本文研究結論的意義在于,投資者使用綜合收益信息和其他綜合收益信息時,要同時考慮其價值相關性和風險相關性,這樣才能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現有文獻大多從價值相關性的角度檢驗了綜合收益對利益相關者尤其是投資者的有用性,但僅分析信息對投資者收益的影響是片面的,風險與收益是投資者決策需要同時考慮的兩個因素。綜合收益風險相關性研究,對綜合收益決策有用性的文獻做了有益的補充,并為我國利潤表的改革提供了經驗證據。我國財政部在2014年對CAS 30的修訂中增加了有關其他綜合收益和綜合收益的披露規定,這表明,我國在會計準則方面已開始和國際接軌,為進一步過渡到綜合收益報告打下了基礎。然而,現行的其他綜合收益披露情況(利潤表中只按照總額反映,其組成項目在附注中披露)導致了該信息的模糊性,另外由于其他綜合收益多涉及金融工具及衍生金融工具,原始信息的復雜性導致了信息提供者和使用者對其理解存在偏差,阻礙了綜合收益信息對各利益相關者的決策有用性。因此,進一步完善會計準則規范和理論基礎,將有利于信息提供者有據可依并易于解讀,從而提高其他綜合收益的信息含量。

表8 綜合收益波動性/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性、非正常收益與股價之間關系的回歸結果
Easton P., ZmijewskiM..Cross-sectional variation in the stock market response to accounting earnings announcement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89(11).
Ball R.,Kothari S.P.,Robin,A..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factors on properties of accounting earning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0(1).
Maines L.,McDaniel L..Effects of comprehensiveincome characteristicson nonprofessionalinvestors'judgments:The role of financial-statement presentation format[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0(75).
Hodder L., Hopkins P., Wahlen J..Riskrelevance of fair-value income measures for commercial banks[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6(81).
Ismail B.E.,Kim M.K..On the association of cash flow variable with market risk:Further evidence[J].The Accounting Review,1989(1).
Graham J.,Harvey C.R.,Rajgopal S..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corporate financial reporting[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5(40).
Dechow P.,W.Ge ,C.Schrand.Understanding earningsquality: A review ofthe proxies, their determinants and their consequencie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0(2).
M.Bradley,G.A.Jarrell,E.H.Kim.On the existence of an optimal capital structure: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Finance,1984(3).
Altman E.I..Financialratios, discriminant analysis and the prediction of corporate bankruptcy[J].Journal of Finance,1968(4).
王鑫.綜合收益的價值相關性研究——基于新準則實施的經驗證據[J].會計研究,2013(10).
威廉.R.斯科特著.陳漢文等譯.財務會計理論(第6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F832.5
A
1004-0994(2017)36-0028-10
山東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項目編號:ZR2015GL004)
山東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山東淄博255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