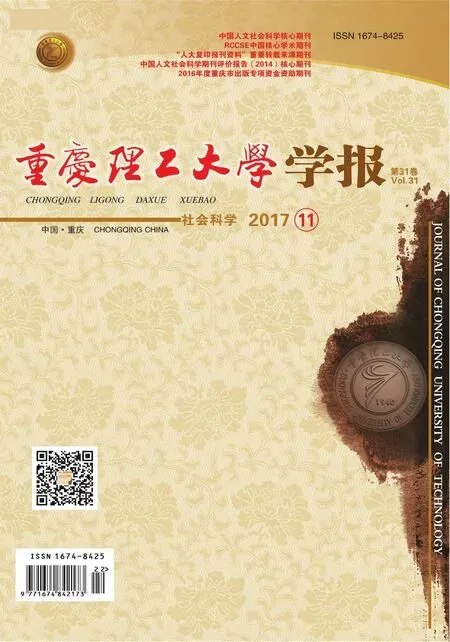“三變”視域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研究
——內在機理、運行機制和實證分析
陳華彬
(中共安徽省宣城市委黨校 綜合教研室, 安徽 宣城 242000)
“三變”視域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研究
——內在機理、運行機制和實證分析
陳華彬
(中共安徽省宣城市委黨校 綜合教研室, 安徽 宣城 242000)
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的“三變”改革,深化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集體產權歸屬不清、權責不明、保護不嚴、流轉不暢,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集體經濟發展活力不足,現代農業發展滯后,必然要求推進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政策引領、制度保障和實踐探索構建了集體產權改革的良好制度環境。旌德縣的改革實踐明確了集體產權主體、創新了集體經濟經營模式、推動了集體經濟穩健發展、拓展了四條壯大集體經濟的途徑。其主要做法是清產核資、成員界定、折股量化、成立主體,取得了一定改革成效,但也存在一些急需解決的問題。提出以下建議:完善股權設置和流轉體系;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理順黨支部、村委會和集體經濟組織的關系;健全農村經營管理體系。
“三變”改革;集體產權;內在機理;運行機制;實證分析
深化農村改革要著力推進農村集體資產確權到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發展多種形式的股份合作,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更多的權能,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以“三變”(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為重要內容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悄然興起,從根本上解決了資源分散、資金分散、農民分散這些阻礙農村發展的頑癥;以股份合作為紐帶,穩步推動了農村集體經濟向規模化、組織化、市場化方向發展,有力地促進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家庭農場、合作社、企業)與農戶聯產聯業、聯股聯心,有效地激活了農村發展內生動力[1]。基層組織在群眾中的影響力和凝聚力顯著增強。
一、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科斯指出,只要產權界定清晰,不需要國家進行過分干預,市場就會自動、合理地解決外部性經濟問題[2]。張五常認為,政府要集中精力抓緊建立由資產界定權利的產權制度,實實在在地去考慮自由轉讓資產及自由選擇合約形式的制度體系和法律規范,確立產權明晰的市場經濟體制[3]。當前,我國迫切需要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集體經濟運行新機制,構建“歸屬清晰、權能完整、流轉順暢、保護嚴格”的集體產權制度。
(一)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1.集體產權歸屬不清、權責不明、保護不嚴、流轉不暢。農村集體資產是農業、農村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動力來源,是計劃經濟時代殘存的最后一塊“大鍋飯”領地。集體資產產權關系界定不清,集體資產的決策權、監督權和收益權不能很好地實現,從而造成對集體資產“人人有份,人人不問”的情況出現。留存于集體賬戶上的資金,一次性分掉,則斷了“子孫糧”;若不分,誰來管?怎么管?針對農村集體資產歸屬不清、權能不明、管理不當而導致的資源閑置、資產貶值、滋生腐敗、引發民怨等問題,政府應該盡早將集體資產確權到戶,明確農戶對集體資產的股份權能,防止其流失、被侵占和貶值,從而實現集體資產由“人人所有、人人沒有”到“按股共有”的轉變[4]。建立農戶與集體之間“管理民主、共擔風險、共享收益”的利益聯結紐帶,實現村集體、農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聯產聯業、聯股聯心”,提高各利益主體的責任感、主動性和積極性。
2.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現階段農民收入的構成包括經營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四個部分。農民想靠糧食生產增加經營性收入已經很困難,因為小麥、水稻、玉米等農產品受價格“天花板”和生產成本“地板”的雙板擠壓。轉移性收入的主要來源是農業補貼,由于WTO黃箱政策限制,對糧食的補貼也已達到上限,所以農民轉移性收入增長趨于極限。這幾年,工資性收入增長緩慢,受經濟下行壓力的影響,農民工出現結構性失業,單純靠體力勞動很難增加工資性收入。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6)》的數據,2015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 11 421.7元,其中人均財產性收入為251.5元,僅占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2%。國際經驗表明,居民財產性收入一般占可支配收入的30%,美國則高達40%。因此,拓寬財產性收入是未來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渠道。那么,怎樣去拓寬農民財產性收入的空間?首先,要給農民財產,農民就有了財產性收入;其次是給農民創造財產,把國家、集體所有的財產的用益物權給農民;最后是實現“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資源是國家的,資產是集體的,集體擁有的水面、房屋、設備等資產和農民個人都沒關系,但是,通過“三變”改革,國家的資源變成資產,集體的資產變成資本,集體投放的資金改變存在形式,就可以讓農民擁有資產資金,農民的財產性收入空間就拉開了。
3.集體經濟發展活力不足。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農村公有制的主要形式,也是農民共同致富的根基,更是農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物質保障。雖然一些集體經濟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大多數集體經濟還存在收入來源單一、發展不平衡、缺乏制度保障等問題,主要原因是發展集體經濟缺少“能人”、可利用資源、項目啟動資金。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既可以發揮集體經濟優越性,又可以壯大集體經濟。集體經濟的健康發展能有效地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的經濟負擔,促進農村各項事業的持續發展[5];同時,有助于美麗鄉村建設的債務化解和管養維護,有助于精準扶貧工作的“人脫貧、村出列”,進而提升基層組織在群眾中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帶動力,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和政權建設。
4.現代農業發展滯后。現代農業發展不足、不快、不優是制約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和農民收入持續增加的重要因素。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能有效激活人力資本、存量資產資金和自然資源,培育壯大一批要素完備、管理規范、經濟實力強和經營效益好的農業經營主體。以產權為紐帶,將農業產業鏈中從事生產、加工、服務的各經營主體通過要素、產業、利益緊密連接,積極探索以品牌建設為導向,符合本地實際的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現代農業產業聯合體[6]。比如,將集體林場發包給相關公司發展茶葉、香榧、油茶等特色種植業,將承包到戶的土地通過租賃形式集中到村集體,反租倒包給合作社和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化農業。
(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可行性分析
1.政策引領。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農村集體資產結構和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結構也隨之發生了變化,農村集體資源、資產、資金的管理及其收益分配等矛盾日益突出。黨的十八大提出,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依法維護農民集體收益分配權,壯大集體經濟實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經營主體。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發展壯大集體經濟,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權利,積極發展農民股份合作,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以及抵押、擔保、繼承等權利。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創新適應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集體資產所有權的保護。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要完善農村集體產權權能。黨中央出臺的一系列政策為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營造了適宜的政策氛圍。
2.制度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必須以保護產權為基本導向。《關于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提出:“對經營性資產,重點是明晰產權歸屬,將資產折股量化到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發展多種形式的股份合作。”《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指出:“完善農村集體產權確權和保護制度,分類建立健全集體資產清產核資、登記、保管、使用、處置制度和財務管理監督制度。”《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對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作了總體部署,明確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頂層設計的目標方向、重點任務、推進原則、實施要求、保護農民財產權利和民主權利、改革的重要目標、保障措施等問題[7]。黨中央、國務院的一系列指導意見,為農村集體產權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
3.實踐探索。在實踐層面上,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萌芽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80年代中期得到發展,90年代之后得到廣泛發展。比如,從1992年的廣東的“南海模式”,到2002年開始的江蘇蘇州農村股份合作制改革,2003年北京昌平開展的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以及浙江寧波農村股份合作模式等都是典型代表。王賓、劉祥琪認為,針對不同類型地區的特征,不宜采取一刀切的方式進行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量化配股應當以集體成員身份為基礎,制定股份繼承和轉讓的實施細則,加強對集體資產確權到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的監督指導和政策扶持[8]。據農業部統計,目前,全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擁有土地等資源性資產66.9億畝、各類賬面資產2.86萬億元,全國平均每個村約為500萬元、東部地區的村高達千萬元。截至2015年底,全國已經有5.8萬個村、4.7萬個村民小組開展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當年就分紅411億元,累計發放股金紅利近2 600億元[9]。
得益于黨中央、國務院的政策引領、制度保障和實踐探索,各地圍繞集體產權改革進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實踐,對集體資產確權到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工作的指導、規范工作流程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環境。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內在機理如圖1所示。

圖1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內在機理
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實證分析
本文以安徽旌德縣作為個案進行分析[10]。旌德縣位于皖南國際文化旅游示范區核心區,總面積904.8平方公里,總人口15萬,轄9鎮1鄉,68個村(居),1 165個組,村組資產合計2.32億元。其中,集體經濟空白村(居)28個,占41.2%,收入0~2萬元的25個,兩項合計年收入2萬元以下的53個,占77.9%。2015年5月,正式啟動3個村試點。2016年初,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推進工作全面啟動,到2016年7月,全縣68個村(居)都完成股份合作制改革,一批先行先試的村開始試水“三變”改革。目前全縣集體經濟空白村從28個減少到9個,村集體總收入增長124.5%,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7.7%。
(一)明確集體產權主體
集體經濟改革,明確產權主體是核心。旌德縣在開展清產核資、成員界定和折股量化的基礎上,通過以合作社作為股東成立公司,賦予集體經濟組織合法的市場主體地位。這一做法完全符合《公司法》和《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要求,確保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一是開展清產核資。逐項盤清集體資產,全縣68個村(居)的經營性資產和可供發包的資源性資產賬面價值為1.9億元。二是界定成員資格。堅持一村一策的原則,以戶籍人口還是以常住人口為界定標準、外嫁女算不算、采用人口股還是農齡股,這些群眾高度關注、現實且尖銳的問題都經過村民同意且符合法律法規的規定。三是折股量化。依照村民意愿,靈活地折股量化,51個村(居)采取人口股,共確定 96 567股、平均每股1 473.5元;17個村(居)采取農齡股,共確定486 377股、平均每股87元。四是成立法人主體。在于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民法總則》設立“特別法人”之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城鎮農村的合作經濟組織不是法人,無法作為出資人對外投資。《公司法》規定,有限公司的股東數在2~50人,而村民人數遠超規定上限。因此依照《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以自然村或村民組為單位,村民以量化到戶的集體資產股權出資,成立合作社,再由各合作社作為股東共同發起成立集體經濟公司。通過“3次村民大會、5次簽名確認、8次張榜公示”的工作流程,全縣68個村(居)全部注冊成立了集體經濟公司,為全縣35 502戶農民發放了股權證,實現了“農民變股東”。
(二)創新集體經濟經營模式
(三)推動集體經濟穩健發展
通過建立激勵機制和監督機制,拓展集體經濟增收渠道,加強對集體經濟公司監督,增強集體經濟內生動力。一是建立激勵機制。村干部不得在母公司中領取工資,但可以從母公司轉交給村委會的公共支出中,領取最高2倍于基本報酬(2016年村兩委正職為19 800元)的績效工資(2016年績效收入約6萬元)。此外,還鼓勵村干部通過領辦合作社、控股子公司等方式,帶動集體增收且獲取“上了臺面能說清、放進口袋能安心”的合法收入。二是完善監督機制。制定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監督管理辦法,規范村級集體資產管理公司的行為,構建“內部監督+村級監督+鄉鎮監督+縣級監督”四個層次的監督體系。① 內部監督:母公司設立董事會和監事會,重大投資決策要經董事會決定,監事會監督母公司,董事會監督子公司。② 村級監督:母公司在村黨支部領導下開展工作,村務監督委員會既監督母公司財務,也監督村委會對收益的使用。③ 鄉鎮監督:母公司賬務由鄉鎮“三資”代理中心統一代理,發包租賃需報鄉鎮備案,簡單自營和投資入股需鄉鎮批準后方可實施。④ 縣級監督:縣農委、財政局對各村開展集體資產運營進行業務指導和財務監督,縣審計部門或受委托的第三方審計機構定期或不定期對母公司和子公司賬務進行審計監督。
(四)拓展四條壯大集體經濟的途徑
第一條是“盤活資產、發包租賃”型。比如,版書鎮江坑村將閑置的油坊、大會堂、糧食加工廠等房屋進行修繕更新,并將此三處房屋租賃給旌德縣華明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用作廠房和辦公場所,每年獲得租賃費3萬余元。第二條是“主動作為、簡單自營”型。比如,三溪鎮雙河村利用扶貧專項資金,建設一座220千瓦的分布式光伏地面發電站,該項目由旌德縣雙河綠色農業發展有限公司進行建設、維護及管理,每年增加集體經營性收入約20萬元。第三條是“找準項目、入股經營”型。比如,興隆鎮三峰村申報30萬元扶持基金,成立母公司——玉銀鳳峰農業有限公司。母公司入股返鄉創業大學生劉小俊創辦的旌德縣桃花源生態農業發展有限公司,該公司的注冊資本從原來的100萬元增加到130萬元,劉小俊占77%的公司股份并負責經營,分紅比例按照出資比例計算,母公司保底收益3萬元。第四條是“整體打包、委托運營”型。比如,三溪鎮路西村將路西旅游集散中心、濱河公園景觀帶、千年古河埂、沿河觀光步道等公共資源和美麗鄉村建設成果,委托給南京康富源公司經營鄉村旅游,創成3A級景區。路西村通過“公司+協會/合作社+農戶”方式,將外出打工者的閑置民居改造、升級為企業化、信息化、標準化的民宿,融入旅游產業鏈條,使“老鼠住的房子”變成“老板住的別墅”。現已經改建成民宿標準間37間,床位70張,發展農家樂餐飲服務10余家,集體經濟每年增收20余萬元的同時,也帶動了農民致富。
旌德縣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旌德縣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典型村(居)情況統計[11]
三、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實踐經驗總結與問題分析
(一)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主要做法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要求對集體所有的各類資產進行全面清產核資,健全臺賬管理制度。在此基礎上,將經營性資產以股份(確權確股)或者份額(確權確股、不確股值)的形式量化到集體成員,有序推進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進而推進“三變”改革。主要做法如下:
1.清產核資。首先是成立清產核資小組。成員由村(居)干部、村務監督委員會成員、村民代表組成,清產核資要在縣鄉農業、林業、財政管理部門指導下開展,對集體所有資產進行全面清查、界定權屬、分門別類登記。其次是明確清產核資的范圍。包括集體所有的耕地、林地、草地、山嶺、水面、灘涂和荒地等資源性資產;用于經營的房屋、建筑物、機械設備等經營性資產;用于文化、教育、衛生等公益事業的非經營性資產。最后是確認清產核資結果。經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代表)表決確認、公示后,報縣鄉農業、林業、財政管理部門備案。
2.成員界定。確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涉及到每個成員的切身利益,沒有身份就沒有相應的權利;不同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其權利內容也不完全相同[12]。由于各地情況復雜,差異很大,目前很難制定一個統一的成員身份確認辦法。在堅持尊重歷史、照顧現實、程序規范、群眾認可的基礎上,由各地統籌考慮戶籍關系、土地承包經營權情況、對集體發展做出的貢獻等因素,民主確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具體界定辦法和程序由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代表)民主決定并張榜公示,防止侵犯少數人及婦女的權益。
3.折股量化。將經營性資產以股份或者份額形式量化到本集體成員,作為其參加集體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據。在實踐中,股權管理主要有動態管理和靜態管理兩種形式。動態管理可以在一定時期內隨著人口的增減而調整股權或者份額;靜態管理實行“生不增、死不減”,股權終生保持穩定。從2015年中央安排的29個縣(市、區)開展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來看,有24個縣選擇靜態管理形式。最終選擇動態還是靜態管理形式,要由農戶民主決定。
4.成立主體。農戶在自主、自愿、互惠、互利的基礎上,成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召開經濟組織成立大會,審議通過組織章程,并向市場監管部門申請法人登記,從制度上保障農戶對集體資產的合法權益,集體成員與經濟組織之間是一種平等的契約關系。
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是“三變”改革的基礎,“三變”改革是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的進一步發展。“資源變資產”是將集體土地、林地、水域等資源要素和房屋設備等,通過一定形式入股經營主體并取得股份權利。“資金變股金”是將投入到扶持農業農村發展生產的、符合使用要求的財政資金(直補農民、社會保障、優待撫恤、救災救濟和應急類資金除外)進行整合、量化到村集體和農戶,通過一定形式入股到經營主體,并可以按股比進行收益分紅。“農民變股東”就是組織引導農民在自愿的前提下,把“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住房財產權、集體收益分配權)以及農機具、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折價入股經營主體并可以按股比進行收益分紅。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運行機制如圖2所示。

圖2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運行機制
黨中央、國務院鼓勵地方從實際出發探索發展集體經濟的有效途徑,開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增強集體經濟發展活力和實力。比如,2015年,安徽村級集體經濟“空殼村”占到全省總村數的三分之一,村級集體經濟實力仍然較弱、規模較小,全省村集體資產總額為366.5億元,集體經營性收入僅為91.8億元。2016年初,安徽選擇了11個縣中的13個村開展“三變”試點工作,到當年年底,13個試點村中已經有6個村給入股的720戶農民進行了分紅,分紅金額61.3萬元,平均每戶851元;有5個村給入股的村集體分紅,分紅金額72.2萬元,平均每個村14.4萬元[13]。
(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取得成效
1.激發各方創業熱情。集體資產確權到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后,明晰了集體產權關系,村民的主人翁地位進一步得到確立。政府、村集體、村民、本地能人、外來投資者利益聯動,各方積極性、主動性、責任感得以提升。政府設立的扶持集體經濟發展基金為大學生、返鄉創業的農民工提供了資金支持。而村民、本地能人、外來投資者則成為推動農村創業最直接、最活躍的因素,各路人才紛紛流向農村尋找商機。
2.提高村民民主意識和市場經濟意識。村民的民主意識和市場經濟意識在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實踐中得到提升,在改革的各個環節都必須經過民主討論決定,增強了村民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意識;而將村民變成股東,參與集體經濟組織的經營管理,也提升了村民的市場主體意識[14]。
3.加快城鎮化進程。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全面完成,集體經濟合作組織成員的利益得到保證,能夠將富余的勞動力、資金、技術用于開拓新的經濟領域,為戶籍制度改革的順利推進打下了堅實基礎,解決了農民遷移的后顧之憂,推動農民向二三產業和城鎮轉移,加快了新型城鎮化、農民市民化的步伐。
4.維護基層政權穩定。改革后,村里有了穩定的收益,不僅使各項工作經費、村干部報酬有了保障,而且道路、水電、衛生等公共事業經費也有了保障。村干部不再為錢發愁,也不再為集體資產經營煩惱,村級組織各司其職,工作的積極性得以提高,為基層政權穩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存在的問題
1.股權設置和流轉體系不完善。在股權量化和配置方面,有的村在改革中簡單地未將外嫁女、入贅男都界定為成員,沒有充分保障外嫁女、入贅男的權益。為了保證村公共事業支出的需要,有少部分村設立了占集體資產20%左右的集體股,這表明該部分資產仍處于模糊狀態。在股權流轉方面,在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的占有權和收益權時,已經進行了順利而充分的探索,但有償退出、繼承權利該如何界定及賦予成為目前面臨的主要難題。特別是對新增人員、股權外部繼承人員及贈予人員的系統性規定還有待探索。
2.“農民變股東”過程中缺少承接主體。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發現,能夠承接集體資產、經濟效益穩定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不多。而且大多數村級集體經濟基礎差、底子薄,發展還有一個必須符合市場規律的過程。集體經濟公司分紅機制還不健全,當前能夠獲取集體經濟組織分紅的村還不多,農民的獲得感有待進一步提高。
3.黨支部、村委會與集體經濟組織的關系有待理順。改革后,村里掛黨支部、村委會、村務監督委員會和集體經濟有限公司四塊牌子。集體經濟公司同其他“三塊牌子”的關系沒有法律規定。集體經濟組織一般沒有經過村民股東(代表)大會決議,就直接將保底收益、股金分紅交給村委會,這種做法無法律依據。
4.農村經營管理體系不健全,不能很好地履行所承擔的工作職責。各級農村經營管理部門承擔著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農村專業合作社組織建設、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農業承包合同管理、農村集體資產與財務管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仲裁及農村審計監督管理等多項職能。特別是在縣鄉農村經營管理部門具體指導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實施中,農村經營管理隊伍是此次改革的主力軍,但是大部分鄉鎮農村經營管理體系線斷網破,突出表現為機構性質與承擔職責不匹配、隊伍素質與履職要求有差距、工作手段與承擔任務不相適應。
四、完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對策與建議
1.完善股權設置和流轉體系。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確認既要得到多數人認可,又要防止既得利益群體借村規民約、少數服從多數原則非法剝奪或損害少數人的成員資格和合法權益。提倡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家庭今后的新增人口,通過分享家庭內擁有的集體資產權益的辦法,獲得集體資產份額和集體成員身份。當前股權設置有兩種模式,一是只設置個人股,不設置集體股,比如廣州天河模式、蘇州平江模式和嘉興模式;二是同時設置個人股和集體股,比如北京昌平模式、東莞模式和無錫黃巷模式。盡管這兩種基本模式的區別在于集體股的設置與否,但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剛性需求和財政體系沒有完全覆蓋鄉村的情況下,集體股始終以隱性(公積金、公益金方式)或顯性的方式存在[15]。是否設置集體股,應充分尊重村民的意愿,由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民主討論決定。總結各地做法和經驗,建議村級集體經營性資產全部量化給村民,股權設置應以個人股為主,不設集體股,避免進行二次改革,集體生產和公益事業所需開支可以在提取的公積金和公益金中列支。積極探索集體資產股份的有償退出權和繼承權。對于有償退出權,明確集體資產股份退出的范圍、條件和程序,建立集體資產股份有償退出機制。對于繼承權,重點探索建立具備法定繼承人資格但不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人員繼承集體資產股份的機制。
2.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承接主體,在堅持農民土地集體所有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和農民權益不受損害的基礎上,引導農民將已經確權登記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到經營主體,實現農民變股東。現階段,由于經營主體的財政、信貸保險、項目用地、扶持等政策落實不到位,能夠得到農民信任且經營管理水平高的經營主體不多,農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很難找到承接主體,獲得分紅的難度大。因此,可以根據各地的區位優勢、資源稟賦和產業特點,積極培育壯大一批內在要素齊備、管理水平高、經濟實力強、經營效益好的經營主體。要整合相關涉農項目資金,重點投向經營主體;通過利息補貼、設立風險補償基金、加強政策性擔保和信用評級授信等方式,解決經營主體融資難題;安排相關專業技術人員與經營主體結對幫扶,牽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到經營主體建立實訓、研發基地,提升其科技創新能力。
3.理順村黨支部、村委會和集體經濟組織的關系。《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明確了村黨支部是村各種組織和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自治法》明確了村委會、村務監督委員會的職責定位,二者在村黨支部的領導和支持下行使職權;但是沒有確定村黨支部、村委會、村民監督委員會和集體經濟組織的關系[16]。建議修改完善有關法律法規和黨內規章,明確集體經濟組織職能定位及其與村黨支部、村委會、村務監督委員會的關系,明確集體經濟組織將收益分紅交給村民委員會必須經村民股東大會表決同意,村務監督委員會對村民委員會公開的收支明細要履行監督職能。
4.健全農村經營管理體系。《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加強基層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建設的意見》要求:“農村經營管理系統不再列入基層農業技術推廣體系,農村土地承包管理、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農村集體資產財務管理等行政管理職能列入政府職責,確保履行好職能。”但不少地方在實際操作中,撤銷了鄉鎮農經站,導致基層農村經營管理機構不全、人員缺乏、人員流動性強,難以承擔改革的重任。應當按照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健全縣鄉農村經營管理體系”的要求,核定縣級農經編制,鄉鎮設置農村合作經濟經營管理站,采取安排專兼職人員、招收大學生村官、政府購買服務等途徑,切實加強基層農村經營管理隊伍建設,建立健全職能明確、權責一致的基層農村經營管理體系。
[1] 中央黨校農村改革調查課題組.中國農村改革發展的新探索[J].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6(11):87-91.
[2] COASE R H.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a,1937(4):386-405.
[3] 張五常.經濟解釋(卷四)[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43-158.
[4] 羅小華.推進農村集體經濟股份制改革的思考[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2(10):127-129.
[5] 習近平.擺脫貧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141-144.
[6] 陳定洋.供給側改革視域下現代農業產業化聯合體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6(13):78-83.
[7]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N].人民日報,2016-12-30(01).
[8] 王賓,劉祥琪.農村集體產權制度股份化改革的政策效果:北京證據[J].改革,2014(6):138-147.
[9]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政策解讀[EB/OL].(2017-01-03)[2017-04-06].http://www.scio.gov.cn/34473/34515/Document/1538436/1538436.htm.
[10] 中共宣城市委改革辦.宣城市全面深化改革考核材料匯編(五)[G].2016.
[11] 中共旌德縣委農工辦.旌德縣農村集體資產確權到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工作手冊[R].2016.
[12] 賀福中.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實踐與思考——以山西省沁源縣沁河鎮城北村為例[J].經濟問題,2017(1):115-119.
[13] 張延明.推進農村“三變”改革試點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N].安徽日報,2017-02-27(07).
[14] 劉純明,柴鵬,劉遠冬.西部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發展路徑選擇[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5(12):105-111.
[15] 朱瑩瑩.農村集體經濟產權改革中集體股的退出壁壘[J].改革與戰略,2016(4):73-78.
[16] 周密.狠抓集體經濟 走出發展新路[J].農村工作通訊,2016(15):39-41.
StudyontheReformofRuralCollectivePropertyRightSystemfromthePerspectiveof“ThreeChanges”:InternalMechanism,OperatingMechanism,EmpiricalAnalysis
CHEN Huabin
(Comprehensive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Xuancheng Municipal Committee, Xuancheng 242000, China)
“Three changes” refers to the reform of changing resources into assets, funds into shares, farmers into shareholders, and it deepens the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The problems of unclear ownership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ambiguity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lax protection, poor circulation, lead to the slow growth of farmers’ income,the lack of vita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economy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These problems require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Policy guidanc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have set up a goo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the reform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The reform practice of Jingde county clearly defined the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 subject, innovated collective economy management pattern, promoted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expanded four ways of expanding the collective economy. The main practice is to check assets,determine membership, stock quantization, establish business entities. Although it has achieved certain reform results, there are still some urgent problems to be solved.We should improve the system of equity ownership and circulation, foster new types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straighten out the relations among party branches, village committees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improve the rural management system.
“three changes” reform;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 internal mechanism; operating mechanism; empirical analysis
10.3969/j.issn.1674-8425(s).2017.11.008
2017-05-11
安徽省社會科學創新發展研究項目“長江經濟帶創新能力與政策比較研究”(B2015001)
陳華彬(1974—),男,安徽固鎮人,中共安徽省宣城市委黨校綜合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碩士,研究方向:農業與農村發展。
陳華彬.“三變”視域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研究——內在機理、運行機制和實證分析[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7(11):50-58.
formatCHEN Huabin.Study on the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Changes”:Internal Mechanism, Operating Mechanism, Empirical Analysis[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7(11):50-58.
F321
A
1674-8425(2017)11-0050-09
(責任編輯楊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