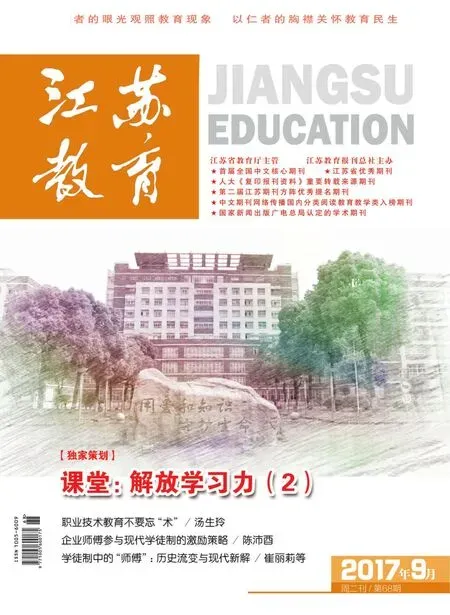學徒制中的“師傅”:歷史流變與現代新解
崔麗莉 王 龍 陳明昆
學徒制中的“師傅”:歷史流變與現代新解
崔麗莉1王 龍2陳明昆3
隨著學徒制的現代復興以及在我國的試點推進,加強學徒過程中的“師傅”隊伍建設愈來愈重要。就技術歷史傳承的角度而言,師傅與徒弟之間為“源”與“流”的關系。以適合現代學徒制發展需要的“師傅”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學徒制形態變遷之下“師傅”身份變化進行梳理,對其類型層次與角色定位進行分析。
學徒制;現代學徒制;師傅
一、學徒制形態的歷史變遷及師傅身份變化
無論何種形態的學徒制,師傅都在技藝的傳承中起重要作用。研究學徒制形態變化下師傅身份的變遷,主要從基于家庭的血親、家族紐帶、契約關系、校企合作的發展形態進行分析。
(一)基于家庭血緣的“直線式”師徒
學徒制作為職業教育的一種形式,在歐洲歷史源遠流長,在職業學校未出現的時期,傳統家庭作坊的運作,主要是通過父子相傳的職業世襲形式。最初的學徒制雛形是父親將自己的手藝傳給兒子,在以學校為載體的職業教育正規化之前,父親的生產技能傳授主要是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兒子則通過模擬的方式,實現“做中學”。此“父教子學”的方式是作為知識、技能、文化傳承的重要方式。
這個時期形態的學徒制,逐步形成了職業世襲制度,僅限于家庭范疇內的技藝傳承。這種父子相傳的職業教育形式,為職業教育技藝的傳承、保存、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在技術的學習中,學徒需要熟悉所從事職業的操作流程,才能生產出更好的、更高質量的產品。在這個過程中,通過師傅的“手把手”教學,學徒能夠進行“做中學”,在道德的約束下,師傅盡心盡力對徒弟進行教育,使得技術不斷向專業化方向發展。[1]
(二)基于家族紐帶的“輻散式”師徒
隨著手工業發展和生產力不斷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化,學徒制形態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在整個社會對手工業產品的需求變大,在經濟利益驅使下,學徒制中師傅的技藝傳承對象開始逐漸擴大,之前的囿于家庭血緣范疇的技藝傳授,出現了擴大化的趨勢。學徒制的技藝傳承不僅僅局限于家庭范圍,而是擴展至家族。此時,以家族紐帶為依托,學徒制中師徒關系出現了擴大化的現象,這是傳統學徒制與手工業發展密切關聯的必然結果。
這個時候,學徒制的私人性質濃厚。基于家族紐帶的“輻散式”師徒中,師傅與學徒之間尚未以規范的合同形式進行約束。師傅對學徒的教育仍然是“言傳身教”的方式。基于家族紐帶的“輻散式”師徒關系融洽,學徒向師傅支付衣、食、住等方面的費用,師傅對學徒的教育在手工作坊進行,師傅可以培養多名徒弟。值得注意的是,師傅不單是讓徒弟重復操作訓練,也十分重視實踐經驗的間接知識和行業行為規范的傳授,以便在技藝和思想上為學徒未來的就業做準備。[2]
(三)基于契約關系的“社會化”師徒
在大約13世紀至14世紀,伴隨經濟的發展,學徒制以道德和私人合同為紐帶,逐漸演變為以契約關系為依托進行約束,學徒制師徒之間呈現“社會化”的狀態關系,產生這一變化的原因主要是行會對學徒制的管理,學徒制師徒之間由私人性質向公共性質過渡。師徒之間是基于契約的社會化關系,意味著師徒關系逐步演變為雇傭關系。
行會加強對學徒制的控制的表現之一為,出現了規范的以契約規定師傅和徒弟行為的現象。師徒雙方須共同遵守契約,在學徒的教育年限、師傅帶徒數量、師徒的權利與義務、師傅的教學內容等方面進行了規定。澳大利亞1901年頒布了《1901新南威爾士學徒法案》,這是相對于1894年頒布的《1894新南威爾士學徒法案》來說更加正規與完善的一項法案。在《1901新南威爾士學徒法案》中除了規定“學徒年齡須在14歲與21歲之間,學徒年限不能多于7年”這一內容之外,同時規定“師傅與徒弟的行為受到契約的約束與管理”。
基于契約關系的“社會化”師徒奠定了現代學徒制契約機制的基礎,在此約束下,傳統學徒制的發展逐漸規范化。
(四)基于校企合作的“現代化”師徒
現代學徒制下的師徒是以學校與企業為紐帶,實行工學交替育人目的。雖然,現代學徒制植根于傳統學徒制,但是,從現代性上加以區分,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表1從教育的范疇對兩者進行區分,以便更好地理解和研究現代學徒制的“師傅”這一群體。

表1 現代學徒制與傳統學徒制師徒區別分析
在現代學徒制這一育人機制中,師徒的主體角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傳統學徒制中單一的師傅角色轉變為師傅與教師雙重角色,單一的學徒身份也轉化為學徒與學生雙重身份。一方面,隨著經濟政治的發展,學校教育與企業教育深度結合,師徒關系已經成為平等、自由、民主的關系,而非之前雇傭環境下不平等的人身依附關系。另一方面,師傅在現代學徒制運行中的教育功用被賦予了嶄新意蘊。適應現代學徒制發展的師傅成為工匠職業文化的傳承者,師傅通過“言傳身教”的教育形式,以匠心品質育人,傳承技術技藝。
二、現代學徒制環境下的師傅類型層次
目前,現代學徒制試點中,職業院校的教師不應該只包括理論教學的教師,也要積極促進技藝精湛的企業師傅充當技能型教師,職業學校要定期聘請一些具有相關行業實踐經驗的能工巧匠進行講座、授課。但是在我國學徒制的實施過程中,師傅的技藝水平也不盡相同。201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對技術技能人才的職業等級進行了修訂與補充,相比2001年版的《國家職業標準制定技術規程》有了更進一步的解釋說明。該文件是基于技藝發展水平與熟練程度,對技術型人才的層級進行劃分。
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的馬陸亭曾指出,現代學徒制的推進,離不開師傅隊伍,對于師傅的類別層次的劃分應與產業特征、專業設置密切相關。[3]依據現代學徒制師傅的技藝能力水平,筆者嘗試將現代學徒制師傅分為3種類型,以便對學生因材施教,實行針對性育人。
第一,傳承傳統工藝的大師類型。這種類型的大師在行業內享有一定聲譽。通過組建校企合作工作坊、大師工作室等形式,職業院校可以嘗試引進具有傳統工藝的師傅。例如為傳承木雕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浙江廣廈建設職業技術學院在木雕設計與制作專業中實行現代學徒制,把曾被國家文化部確認的木雕文化遺產項目傳承人陸光正等師傅聘請入校,通過現代學徒制的運行,培養木雕專業的技藝人才。
第二,培養技術能手的能工巧匠。現代學徒制師傅的引進,需結合區域特征與專業設置。在我國職業院校引進師傅時,需要在區域發展、崗位實踐特征鮮明并適合校企一體化聯合培養的專業進行。通過校企深度合作,將能工巧匠引入這些專業,教授學生應用技能,促進學生的技能實現從學校教育到崗位工作“無縫連接”。
第三,培育批量技能人才的師傅。這一類“師傅”可在通用專業中引進,相對來說,這類師傅的帶徒數量較多。[4]比如浙江工商職業技術學院推行的“首席工人、技術能手帶徒工程”,每位師傅最多收6位徒弟,由師傅為徒弟量身定制培養方案并負責實施。截至2014年底,該校累計聘請市級及以上首席工人、技術能手等450多位,招收在校徒弟1520余名。[5]
三、現代學徒制師傅角色定位分析
現代學徒制中,師傅發揮著重要的育人價值與功效。對于現代學徒制的師傅進行角色定位,可以進一步認識師傅的這種育人價值。筆者試圖從“職業”“技術”“教育”三個角度進行研究,依次將師傅定位為工匠職業文化的傳揚者、高深精湛技藝的傳授者與溫情師徒關系的垂范者。(如圖1所示)

圖1 “職業”“技術”“教育”視角中的師傅定位分析圖
(一)工匠職業文化的傳揚者
源于社會對工匠精神的迫切需求,很多職業院校試點現代學徒制,試圖通過師傅型教師身上體現的追求卓越、注重品質的精神來影響和促進學生的發展。由于職業教育的特殊性,工匠精神這種隱性知識的培育與傳承必須植根于實際工作情境之中,依賴于師傅的“口傳心授”,而工學結合、校企合作的現代學徒制恰恰為工匠精神的傳承提供了體制基礎。
現代學徒技藝成長的特征和環境以及師徒的人倫關系、親情關系、友好關系的培養正是技術傳承、發揚所不可或缺的,也是成長為一名工匠所必需的。企業師傅通過“傳、幫、帶”的方法,不僅向學徒傳授技藝,更重要的是通過此“言傳身教”的方法,讓名師巧匠與學生建立師徒關系,在真實的工作情境與任務規則下言傳身教,通過情感交流與行為感染,培養學生耐心、專注、堅持等品質精神,從而使學生形成敬業、樂業、精業的神圣感與使命感。
(二)高深精湛技藝的傳授者
在現代學徒制背景下,師傅依然在某一行業具有精湛的技藝。教育部推出首批“現代學徒制”試點單位,其目的在于借鑒“學徒制”這一古老的人才培養制度的精髓,將其與當代工藝技術革命有機結合,通過技藝精湛的師傅的教育,為我國職業教育培育應用型人才。師傅作為高深精湛技藝的傳授者,在工作實踐中,經歷長期的、反復的、大量的操作,形成了在某一方面的專門的技藝。
師傅對學生傳授精湛的技藝,離不開校企一體化的工作場所。學生通過學校與工作場所交互學習的方式,進行工學交替,依據崗位作業流程,在師傅的幫助與指導下,有針對性地加強崗位技能訓練。通過教室與崗位的學習—實踐—再學習—再實踐的教學方式,促進學生實現技能的專門化與精深化。
(三)溫情師徒關系的垂范者
學校教育形式可通過系統化教學授課批量化、規范性培養學生,然而傳統學徒則注重師徒之間的道德與義務,注重溫情的師生關系,成功的現代學徒制應該兼取兩者之長。師傅,是溫情師徒關系的主導者。在傳授學徒技能之時,也要注重對學生人格精神的培養。在融洽的師徒關系中,師傅認真傳授技能,學生在真實情境中學習技術技能,共同生產出高質量的產品,滿足社會需求。[6]例如浙江省蘭溪市職業中專,74名烹飪專業的高一學生成為11名蘭溪烹飪界大師的學徒。浙江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朱師傅指出:“烹飪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工藝。借助現代學徒制這樣的教學方式,不僅能激發學徒對學習的渴求、對技藝傳承的使命感,同時還能樹立師傅的權威,增強師傅的責任感。”[7]同樣,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中策職業學校建立大師工作室,學生與師傅建立亦師亦友的自由平等的師徒關系,這有助于促進現代學徒制培育技能型人才目標的實現。
[1]李夢卿,劉晶晶.我國職業教育150年的局變與勢況[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16(34):71-76.
[2]郭志勇.古代學徒制對中職學校辦學思路的啟示與思考[J].中等職業教育,2004(24):3.
[3]邵建東,朱振國.現代學徒制:促進校企合作的真正紐帶[N].光明日報,2015-04-21.
[4]崔麗莉,陳明昆.現代學徒制若興,必尊師而重傅[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07-21.
[5]史望穎,張冶紅.浙江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實行“雙導師”制培養技術技能人才——能工巧匠當教授,學生入企掙學分[N].中國教育報,2015-11-05.
[6]崔麗莉,陳明昆.試點現代學徒制,“師傅”從何處尋?[N].中國教育報,2016-03-01.
[7]胡夢甜.現代學徒制,尋回往日的師徒溫情[N].浙江教育報,2016-03-11.
G710
A
1005-6009(2017)68-0024-04
1.崔麗莉,北京市密云區不老屯中學(北京,101500)教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課程改革與師資隊伍建設;2.王龍,北京市密云區不老屯中學(北京,101500)教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課程改革與校本課程建設研究;3.陳明昆,浙江師范大學(浙江金華,321004)非洲研究院教授,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比較教育研究與職業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