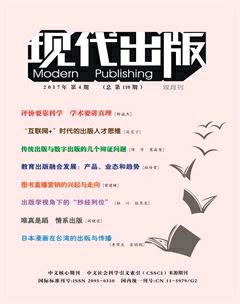“互聯網+”時代的出版人才思維
聶震寧
“互聯網+”時代已經到來,出版業正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既有內容創新的挑戰,也有傳播載體創新的挑戰,還有運營管理創新的挑戰,最根本的還是人才的挑戰。當一個個新型出版人以工作室、文化公司、網絡文學網站、視頻網站乃至“一端兩微”(即移動客戶端、微信、微博)等形式進入出版行業的大格局之中,人們在驚艷的同時,往往會對那位或那幾位掌門人、操盤手的來龍去脈產生興趣,有所思索。這是作為內容產業的出版業的主要價值和經營規律決定的。雖然很多行業都在說“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可也有不少行業主要是資源的競爭、投融資的競爭、技術設備的競爭,而內容產業的競爭脫離了人、脫離了人才,其他許多有利條件都有可能歸零。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出版業較之于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強烈地感受到人才的重要性。
一、人才主義是出版業最根本的主義
人才主義,是我國現代進步出版事業杰出代表鄒韜奮先生在七十多年前提出來的。韜奮先生之所以在“人才”之后綴以“主義”,為的是要強調人才乃是出版事業成敗的關鍵所在。七十多年來,韜奮先生的人才主義_直在我國出版業中廣為傳播。
前不久,為紀念韜奮先生誕辰120周年,本人撰寫了《韜奮精神六講》一書,從六個方面來談韜奮精神。第一,為大眾。韜奮先生一開始進入新聞出版業,主編《生活周刊》,就確定了竭誠為讀者服務的宗旨,他從始至終“永遠立于大眾立場”(韜奮語)。第二,愛祖國。韜奮先生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因而成為首個國家公祭日發布的300名愛國英烈之一。第三,敢斗爭。對于邪惡勢力和反動勢力,韜奮先生總是勇敢地進行斗爭,而且戰而不屈。第四,善經營。在書刊出版發行等諸多方面,韜奮都是經營高手,他主持的生活書店,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時間內發展成了一家有56個分支店的出版發行機構,他主編的《生活周刊》和《大眾生活周刊》都是當時全國期刊中發行量最高的刊物。第五,懂管理。韜奮先生對生活書店有一系列的科學管理辦法和成功實踐。他非常重視人才問題,專門撰文提出人才主義,堅持以人為本、以人才為先,把生活書店的員工團隊打造得非常團結,以至于在他去世多少年后,這個團隊許多人還是以生活書店為家,成為后來的三聯書店的主力,甚至成為新中國出版事業的領軍人才和業務骨干。第六,真敬業。韜奮先生忘我地投身于出版事業,有許多感人故事,其敬業精神令人嘆服。這六個方面中,韜奮先生投入很強烈的感情和很大精力的就是對人才的管理。他不僅提出了“人才主義”,而且身體力行。當時生活書店對店務工作實行委員會管理辦法,成立了三個委員會,即編審委員會、經營管理委員會和人才工作委員會,他親自擔任人才工作委員會主任,主持人才工作。作為全店的總經理,主抓人才工作,其重視程度可想而知。
韜奮先生特別重視人才引進工作。所有新員工進店,他都要組織面試,嚴把進人關。在生活書店,韜奮先生精心打造了一支團結奮斗的專業團隊和學習型組織,要求團隊保有濃厚的友愛精神和學習風氣,從1938年起,生活書店開始組織店內讀書會,讓所有員工獲得更多的學習機會。對于與生活書店相關的許多特殊人才,韜奮先生則以“精神和品格”(夏衍語)加以感召,以至于有一批杰出人才先后加盟生活書店,如徐伯昕、張仲實、金仲華、錢俊瑞、錢亦石、林默涵;還有一批知名人士雖然身在生活書店之外,卻長期與書店緊密合作,如茅盾、胡愈之、鄭振鐸、傅東華、黃源、沙千里、徐懋庸、張庚等。我們知道,這些加盟者和合作者在當時都是文化界和出版界的一流人物,后來也都分別成為新中國文化、出版事業的各級領導人。可想而知,韜奮先生領導下的生活書店之所以能夠成為一流的出版機構,是與書店擁有這樣一批一流的團隊和一流的人才分布不開的。韜奮先生的“人才主義”無疑應當成為出版業最根本的主義,是永遠不會過時的主義。
二、“互聯網+”時代出版業的“改變”與“不改變”
回顧是為了發展。我們使用一些篇幅來回顧重溫韜奮先生的“人才主義”,是為了出版業當前的發展。可以說,身處“互聯網+”時代,雖然技術創新正在不斷改變著出版形態和出版業發展的趨勢,可是,出版業的人才主義不僅沒有過時,恰恰相反,隨著出版業傳統媒介和新興媒介的融合發展,人才主義正顯得越來越不可或缺。
要討論人才問題,先要談談人才思維。要談人才思維,首先要考量互聯網到底對出版行業有多么大的改變和多么大的不改變。
在“互聯網+”時代,出版行業主要有四個方面的改變:
第一,從服務讀者向用戶至上轉型。互聯網思維最核心的理念是用戶至上,過去我們說“讀者第一”已經很了不起了,“用戶至上”就是以用戶需求為主導,整個出版經營的起點和邏輯都要發生改變。
第二,由信息發布向信息交互轉型。過去出版企業發布信息速度很快,渠道很多,甚至電視臺都可以幫忙發布信息,但都是單向度的發布,現在互聯網卻幫助我們實現信息交互。信息交互就是出版企業不僅發布信息,而且還知道信息發布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給了什么樣的反饋,給出版企業帶來了什么樣的信息增值。
第三,由提供知識向分享知識轉型。過去出版企業出書,成千上萬人讀書,這個過程就是出版企業在提供知識、傳播知識。現在出版企業卻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知識,通過互聯網,可以形成一種知識眾籌。出版人也需要通過互聯網獲取更多的知識,然后形成出版的新的內容,而不再是關門編書,不再是完全的獨立創作。
第四,由出版平臺向開放平臺轉型。過去出版企業把書擺上出版平臺,現在是開放平臺,書擺在這里,讀者可以隨時點擊,可以隨時討論。過去是專業作家創作閱讀內容,現在每個用戶都可以生成內容,甚至進行自助出版。
這四個方面毫無疑問是互聯網對出版業造成的巨大改變。那么,出版業又有哪些“不改變”呢?在國家對我國出版業總的性質要求和管理規則沒有發生改變的前提下,出版行業主要有兩個方面沒有發生改變:
首先是出版企業的品牌作用沒有改變。現在是“互聯網+”時代,是海量信息的時代,可是,傳統出版企業的品牌影響力依然可以讓讀者感覺得到,品牌出版社依然是出版質量、信譽、品位的重要保證,品牌價值依然在發揮重要作用。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的海量信息的汪洋大海里,一些具有顯明的辨識度、可靠的信譽度和強大的感召力的出版品牌,將顯得愈發可貴。這不僅是出版者的財富,其實也是閱讀者的福音,因為品牌的存在,將幫助廣大閱讀者節省大量的檢索時間,去除許多無效瀏覽,避免接觸太多的語言垃圾。市場競爭中的品牌策略之樹依然常青。endprint
其次是傳統出版的運營機制和專門化原則沒有根本改變。傳統出版機構無論如何應對出版載體和傳播渠道的變化,也還依然有策劃、選題、編輯加工、營銷推廣等專業環節,至少可以說有很大的“不改變”。馬克斯·韋伯在19世紀末提出科學的分類和專業化,盡管到了20世紀末賽義德提出了用業余性反對專業化,但是我們作為一種專業,出版行業依然堅持著自己的專門化,由專業人員生成內容的方式不會改變,專業化還是基本規律。賽義德的業余性,強調的主要是文化的泛漫性和自由精神,然而,作為出版主體,即便是出版傳播泛漫性文化和自由精神的出版物,也還需要按照出版規律去實現。
關于按照出版規律去適應“互聯網+”時代,本人就還有過一些體會。中國出版集團成立之初,新浪、搜狐正在崛起,由于當時出版集團還是事業單位,沒有轉企改制,沒有籌資權利,更沒有投資能力,失去了數字化、網絡化發展的起步機會。不過,我們并沒有放棄進行數字化發展的努力,更不想坐以待斃,決定集中力量建設專業出版資源數據庫,因為這樣的項目在當時能夠獲得國家財政專項資金的支持。這才有了后來的商務印書館的“語言工具書數據庫”“東方雜志數據庫”,中華書局的“中華古籍數據庫”,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百科術語數據庫”和中譯公司“多語種翻譯數據庫”等產品。中版集團通過數據庫建設,搶占了數字化出版的根據地。這就是堅持按照專業出版的要求,遵循從出版資源著手的出版規律取得的成果。即便在已經是數字化遍天下IP和AR、VR崛起的當下,專業出版社恐怕也還得按照專業化這條路子往前走,才可能在未來的競爭中保住生存的一席之地。
既然出版業有著這么大的“改變”和這么重要的“不改變”,相應地,出版業的人才思維也就應當要有很大的改變和不改變。
三、究竟是“互聯網+”還是“+互聯網”
出版業已經發生改變了的東西需要以“互聯網+出版”來做,反過來,不改變的因素則需要用“出版+互聯網”來做。出版業內討論過究竟是“互聯網+”還是“+互聯網”。有人認為,必須是“互聯網+”,而“+互聯網”是不對的,這不是互聯網思維。我覺得事情不能那么絕對。“互聯網+”是用戶至上,但是專門人員生成知識,專門人員傳播專門知識,就不能用戶至上。尼爾·波茨曼的《娛樂至死》深刻指出,現在進入了娛樂時代,一切話語可以通過娛樂的方式傳播,包括政治、體育、教育、文化、商業的內容,都被娛樂化了,這樣一來,我們將成為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波茨曼意在提醒人們要警惕娛樂化的危害。可是,互聯網的存在卻在為娛樂化大開方便之門,推波助瀾。那么,嚴肅的出版人就要有必要的堅守。特別是專業出版,要堅持內容“+互聯網”,而不是“互聯網+”內容。“互聯網+”內容就把出版簡單化了。我們一定要保持人類認知和思維的深刻性、嚴肅性。誠然,“互聯網+”出版也是可以的,尤其是大眾出版、知識類出版,“互聯網+”娛樂出版更應當如此去做。可專業出版,“+互聯網”也是必須的,這是為了保持出版的嚴肅性、深刻性,以及出版為國家、民族、人類做出更多思想文化貢獻的主體性。
其實,事情沒有必要弄到非此即彼的地步。“互聯網+”與“+互聯網”,沒有必要弄到二者必據其一。事物可以一分為二,也可以一分為三,一分為三的思路更為寬闊。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就不是強調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三生萬物”的觀點可以使得我們的思維更為開闊、自由。譬如,螳螂撲蟬,就還有一個黃雀在后;互聯網出版與傳統出版之爭,還有一個市場規律在制約。當前,不要以為今后只是“互聯網+”出版,也不是是否固守出版“+互聯網”,其實還有市場出版,甚至可能還會有新的載體形態出現。科學技術發展太快,事物的變化是難以預料的。
既然出版業的“互聯網+”和“+互聯網”沒有必要弄到二者必據其一,那么,“互聯網+”時代出版業的人才思維也就沒有必要弄到以“互聯網”為界,不要過于強調人才特別是新進人才是否歸屬于互聯網。我們希望看到的人才是,如果是互聯網專業出身,可是對出版業并不陌生;如果是傳統出版專業出身,卻對互聯網出版有一定的了解。整個社會正在高度重視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的融合發展,出版業的人才隊伍更應當加快融合,即便是一個出版人,無論是傳統的還是新興的,自身的知識結構和業務能力也應當在這兩方面、甚至更多方面有所融合。
四、“互聯網+”時代出版人才需求呈多維多樣特點
“互聯網+”時代的出版人才需求呈現多維多樣的特點。古人說,兵家貴剛,道家貴中,儒家貴柔。出版業的人才需求也將會出現多樣化特點,也需要有兵家、道家、儒家,儒道兵各有其用。“互聯網+”時代的出版業人才需求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要高度重視生成內容的專業人才。這個要求是為了使傳統出版企業立于不敗之地而提出的。出版業絕不可能向互聯網行業主體舉白旗歸順,這就要高度重視生成內容的專業人才。沒有生成內容的專業人才,傳統出版業就只能在“互聯網+”時代敗北。如果傳統出版業承認必須按照互聯網企業的思路去做,那就變成互聯網企業的編輯部,往后生存的自主性將會越來越差。2016年,亞馬遜在美國西雅圖開辦了一家1400平方英尺的實體書店,說明互聯網并非一統天下,實體書店還是有存在價值的。人們在網購的同時還需要體驗式購書,在讀手機、讀電子閱讀器的同時還需要讀紙書。事物總在變與不變之間。傳統出版業不要急著覺得今是而昨非。作為內容提供商,強化自己生成內容的能力才是重要保證。
第二,要高度重視知識經濟管理人才。1990年代-中期,知識經濟概念從國外引進,轟動一時,現在談得比較少。其實知識經濟應當多談。知識經濟就是對知識的經營管理,知識成為經濟的一種形態,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件大事。在出版行業,編輯人才事實上是知識經濟的第—人才,因為編輯管理作者。版權經營管理人才,也是對出版業知識經濟的管理。此外,出版業內部生產協調管理始終是重要的,而目前這方面的力量還比較薄弱,這些方面的管理人才不能弱化。endprint
第三,要高度重視“互聯網+”時代信息營銷復合人才。現在出版社里做信息和市場營銷的人才需要盡可能復合起來,要不然一邊內容宣傳做得熱火朝天,一邊銷售卻跟不上,復合型人才可以減少各種資源的浪費。
第四,要高度重視客戶服務管理人才。現在強調用戶至上,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對于傳統出版業來說,如何管理客戶,如何利用互聯網技術管理好客戶,管理好自己的忠實讀者,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應當有這方面的管理人才。有的發行量很大的期刊,至今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讀者訂戶數據庫,實在令人扼腕,嘆為可惜。其實,即便是發行量不大的甚至很小的雜志,也應當建立自己的讀者訂戶數據庫,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的雜志社還想生存下去,就要重視自己的數據庫建設。
第五,要高度重視既懂互聯網,又懂傳統出版的復合型領軍人才。作家賈平凹說他寫書都是手寫,他在書寫中能找到自己的趣味。作家可以特立獨行,可以遺世獨立,這是沒有問題的。可是一般來說,出版人這樣就不行,一個社長到了今天還不會使用互聯網,恐怕就得準備退休了。出版領軍人要有更加開放的心態和旺盛的學習熱情,要有與時俱進的精神和能力,要有復合型的知識結構和操作能力。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們是在一個越來越開放的“互聯網+”時代從事出版事業,領軍人才必須更加開放和進取。
五、“互聯網+”時代更要廣開人才之路
互聯網已經使世界變平了,也使出版業人才進出的門檻變平了。有位出版社領導來征詢我的意見,說是有一家民營控股的上市公司給他上億股權和百萬年薪,去還是不去呢?我說如果你是為了發財才來做出版,那你肯定要去,而且趕快去;如果你是想在品牌出版社里有一番作為,那就不要去,因為這里是你實現出版理想的地方。都說人才難得,到底人才難得在哪里?難就難在他的心在這里,他的志趣在這里,他的情感在這里。出版業要廣開人才之路,使得人才進出更加方便。廣開人才之路,要讓愿意走的人高高興興地離去,讓愿意在出版業發展的人才進得來、留得住。
第一,出版業的人才要樹立正確的價值觀。現在關于人才的思維有一個理論,叫三圈理論:一個是價值圈,一個是能力圈,一個是支持圈。這三圈的重合點,就是人才的最佳點。重合度越大越好。現在特別需要提升人才的價值維度,使人才價值更多地覆蓋到能力和支持上。在“互聯網+”時代,傳統出版業有可能繼續做紙介質出版,也可能要開發數字出版,這個時候,首先要讓人才認識到在這里具有很大的價值。有一種并不準確的看法,認為編輯出版專業是實用性學科,以為只要掌握好編輯技能、經營管理知識就可以了,其實,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只能是一般的工匠,而成不了出版人才。出版人才必須有人文素養和科學素養,對出版的價值哲學要有正確的認知,要樹立正確的出版價值觀。無論是什么時代,出版人才首先要把編輯出版學當成人文學科、科學學科來學習,只有掌握了更多人文知識和科學知識,牢固樹立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才可能成為優秀的出版人才。
第二,傳統出版業要注意維護和發揚既有的人才優勢。傳統出版行業的人才優勢還在。要很好地愛護、維護作者人脈,出版企業業務骨干的維護工作也不可掉以輕心。一個資深編輯后面往往跟著一大群優秀的作者,往往是出版社走了一個老編輯,立刻遺失掉許多好作者。傳統出版企業要注意用情感留人,用事業留人,用必要的待遇留人,當然,還需要用制度乃至法制留住人才:
第三,傳統出版業要堅決引進人才。這是每個行業、企業都在做的事情,傳統出版業也在做,但是做得往往不是很堅決。傳統出版社還面臨這樣的問題:出版社從互聯網企業、IT企業引進了一些人才,可是大家感覺到這些人才并不像他們在原來的企業那樣干得那么風生水起。這是值得各方面思考的。這當中有可能有體制機制的問題,也還有企業文化的問題。為此,傳統出版社在堅決引進人才的同時,還需要堅決推進老舊出版企業的改革創新,不然弄了半天依然是做不成事,最后還是留不住人。當然,也還需要讓新進的人才形成更好的價值認同、品牌認同、情感體驗、事業體驗,實現人才與企業的雙向融合。
第四,出版業要加大人才培養力度。高等院校在出版人才培養上肩負著很重要的責任,現在培養出來的學生都應當是復合型人才。行業在職人員的繼續教育模式也需要不斷改進,行業在職人員的培訓應該更多地安排一線的出版人來做培訓講師,讓受訓的員工真正學有所得。2013年,淘寶大學開辦,接著萬達大學、京東大學也相繼開辦,三大新興企業都在大力開展人才培養,而且人才培養的講師基本是一線員工。這些居于“互聯網+”時代潮頭的優勢企業都一刻不放松人才的培養,我們這些體制機制偏于老舊的傳統出版企業又有什么理由輕視人才的培養呢?
六、出版企業對人才的評價思維要與時俱進
在“互聯網+”時代,出版企業對人才的評價思維要與時俱進。出版企業對人才的評價,直接關系到人才能不能留下來。當然,不斷提職提薪是最好不過的事情,可是國有企業不可能—直都用這樣的獎勵措施。總之,要有些既不違反干部管理規定又能帶來激勵效果的創新設計。此外,還有一些人才評價思維需要調整。
第一,要把對企業的忠誠變成對職業的忠誠。一個人服務的企業可能會有變化,但是從職業的忠誠度來說,職業態度不能扭曲,不能不守職業道德。鄒韜奮是一個最講職業道德的人。黃炎培曾經回顧說,鄒韜奮自進入《生活周刊》,就沒有再給別的出版社寫過文章。他的職業忠誠度和企業忠誠度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們當然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對一家企業忠誠到底,社會生活這個方程式往往是多解的,但可以要求從業者要恪守職業道德,對職業的忠誠度是必須的。
第二,企業最大的財富在于能夠使用更多人才。出版企業能夠擁有多少好的作者和多少好的書稿,就需要擁有多少好的編輯和營銷人才、移動互聯網經營人才和技術人才。人才以用為本,不要強調人才企業所有制,關鍵是發揮好人才企業使用制。一個優秀編輯雖然離開了這家出版社,但其實還可以繼續留在這家出版社的某一個或幾個項目上發揮作用,按勞取酬。要建立人才資本優先的理念,不要過分強調貨幣資本優先。出版業的領導層都習慣于貨幣資本優先思維,其實在人力資本上也是需要真花錢的。人力資本對勞動效益要有索取權,這是合情合理的。只有這樣,企業才能使用更多的人才。
第三,要建立人才跨界的思維。早先,IT業、互聯網業曾經從出版業挖過人才,現在,出版業需要反過來從他們那里跨界延攬人才。出版業還要從社會各界尋找人才。這就需要出版企業的領軍人,要有跨界思維,既要向內挖掘和培養人才,也要向外跨界發現和延攬人才。尤其是出版企業的一把手,要真心實意地去做這件事情,對人才形成感召力和向心力。傳統出版業在人才問題上格局偏于狹窄,常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成見,現在需要樹立“非我族類,其才必異”的理念。要敢于使用有一技之長但素質并不全面的人才:只有不拘一格用人才,才可能突破陳規,謀得更大的發展。
“互聯網+”時代正在到來,出版業的改革、發展、轉型還在持續進行。人才問題將是第一位的問題。有了人才才會有出版,有了新型人才,才會有新型的出版,才會有整個行業的創新發展。我們要站在“互聯網+”時代的高度,創新人才思維,把人才工作做得更好,使得我國出版業實現優質、高效、健康的發展。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