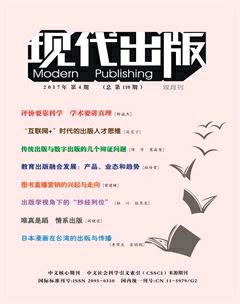出版業供給側改革管窺
黃磊
一、供給側改革的歷史源起
20世紀70年代西方經濟陷入“滯脹”之后,1979年英國執政的撒切爾政府、1980年美國執政的里根政府,針對西方需求提振乏力、經濟“滯漲”的“凱恩斯陷阱”,吸收西方供給學派的理論,大規模地將供給學派的減稅、消減財政開支、減少對企業的干預、嚴控貨幣供應量等政策主張付諸實踐。這些政策實踐都取得了一定的實效,提升了英、美的經濟活力。
從中國歷史上看,以減稅為特征的供給端改革源遠流長。春秋時期,管子提出“征于關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關。虛車勿索,徒負勿人”“關賦百取一”“關幾而不征,市廛而不稅”等一系列放松管制的舉措,為齊國的經濟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齊桓公以此“九合諸侯”,成為春秋霸主。此后,歷代初立王朝,在供給端多采取“輕徭薄賦”、放松管制的政策,經濟得以快速恢復。
結合中外實踐可以看到,供給端改革的顯著特征就是給予微觀經濟主體更多的選擇權,從而在面對需求端的多樣性時,能夠根據市場做出及時和合理的應對。
二、出版業供給側改革的背景
根據開卷最新圖書市場報告,2016年全國全年新書品種數為21.03萬種,連續5年保持在20萬-21萬種之間。新書、重印書合計,年均大致在45萬~47萬種。過于龐大的出書品種,導致實體書店上架率低,上架圖書的動銷率基本在20%~30%,主動對接買方市場的能力較弱,企業經營“廣種薄收”、經濟效益較為低下。鑒于現狀,當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出版業而言,可謂恰逢其時,具有極強的針對性。
三、出版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路徑
出版業與目前產能嚴重過剩的水泥、鋼材等高能耗產業相比,因其內容生產的屬性而具有自身的特點。因此,出版業在尋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路徑時,要既重視目前大環境下存在的普遍性矛盾,也應該因地制宜地分析本行業問題的特殊性。
一是“去產能,強服務”。高產能是工業化社會流水線作業的產物。隨著現代社會思維的多樣化,由出版者單維度地提供價值判斷的“現代性傲慢”,在社會的多樣化背景下逐步解構,讀者的閱讀需求也越來越多地體現為個性化和小眾化。針對這種狀況,作為精神產品的圖書,在供給端面向讀者進行自我調適顯得尤為重要。這種差異化要求更多地對市場進行細分,同時,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務。以當前出版的大學教材為例,紙質文本中,更多地從滿足受眾的學習體驗出發,提供“案例導讀”“知識鏈接”“微課”等多樣化知識學習路徑;市場型圖書則更多地以讀書會、微信群等方式,在服務增值和價值鏈延伸等多維度上進行開拓。
二是“去庫存,輕資產”。自2004年以來,圖書庫存逐年遞增,截至2014年,全行業庫存總碼洋為1010億元,總庫存數66.39億冊,年均增長2.5億冊。過高的庫存嚴重制約了行業的健康發展。因此,去庫存是當前出版業供給側改革“治標”的題中之義,“縮表”是壓縮成本、維護出版業健康安全運營的必然選擇。應當注意的是,部分舊版圖書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價格、版本等方面的價值逐步凸顯,在去庫存的過程中,仍然需要對這部分圖書加以甄別、保留,切忌盲目操作。
三是“去杠桿,重研發”。“輕資產”的潛在含義,是出版者應當通過專業的策劃團隊,專注于核心價值,即內容生產。根據民進中央2015年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國內現有35.7萬家新聞出版單位,其中民營出版單位有32.4萬家,占總數量的90.8%,資產總額占69%,營業收入占69.3%,利潤總額占80.5%。毫無疑問,民營出版機構在文化事業繁榮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占有重要地位;但與之相對的國有出版單位,表現出“空殼化”的趨勢。出版社過于注重碼洋規模的外延式擴張,與社會民營企業“合作”較多,而自身選題開發能力在不斷擴大的“合作”出版中逐步萎縮,甚至最終成為只能依靠收取“過橋費”維持生存的單位。為此,出版社應當摒棄短期思維,強化內容導向,重視研發投入。在2016年財報中,知識密集型企業的行業翹楚,研發經費投入在營收中的占比大致在15%左右。例如,華為的研發占比為14.65%,谷歌的研發占比為13.95%,臉書(Facebook)的研發占比為17.58%。相比之下,國內出版機構特別是國有出版單位在這方面的投入偏低。
除了提高比例之外,研發經費重點投向何處是我們應當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方向不對,投入的經費很快會成為“沉沒成本”,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從供給側改革的角度看,研發經費的投入原則,應當密切對接需求端。需求端可以進一步劃分為政府需求和市場需求。前者以各類財政資金支持的項目為主,后者以讀者的市場購買為主。財政資金的扶持項目,往往具有規模大、周期長、社會效益顯著的特點,對于此類項目,在內容、時間節點等各方面,應當做周密的規劃和長期的安排。此外,傳統出版社在內容生產方面具有一定優勢,也匯聚了一定的作者資源。從更長遠的角度看,出版社應當有意識地向智庫型、平臺化的方向發展,成為政策制定的智力支持者和提供者。對于市場需求,則需要認真測度讀者閱讀偏好角度。在多媒體時代,優秀的市場型圖書不僅在內容上有著上乘的質量,而且在傳播方式上也往往具備“媒介融合”的特征,即傳統紙媒借助于電視、網絡等介質的傳播內容,完成市場對紙媒內容的認知。例如,《人民的名義》一書,即借助電視劇的熱播迅速暢銷。此類的案例非常多,前些年的“百家講壇”系列圖書、《明朝那些事兒》等的熱銷,也是“媒介融合”的典型。
四是“降成本,新機制”。創新機制是出版業供給側改革的重點所在,也是在“三去”之后出版業起步的依托所在;否則,無效產能和高企的庫存又將卷土重來。機制的創新是傳統出版企業實現自我革新的重要舉措。機制創新有兩種途徑:一種途徑是引入外生性變量。根據《關于推動國有文化企業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指導意見》:“按規定已經轉企的出版社、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新聞網站等,實行國有獨資或國有文化企業控股下的國有多元。”因此,就出版單位整體來說,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引入社會資本,激活內部存量,是盤活國有資本的有效舉措。另一種途徑,是通過改變固有的內部組織結構和激勵約束條件,形成新的原動力。傳統的編輯出版體制脫胎于計劃經濟,具有強烈的流水作業特點和條塊特征。生產者的價值,多體現為產品生產的某一環節。而當下的圖書產品生產,更多的是依靠創意和策劃。這一特點要求編輯從單一的生產環節中脫離出來,更多地從市場、讀者、內容、裝幀、營銷等方面做綜合的考量取合,編輯也由此逐步具備了“產品經理”的功能。在此基礎上,一批具備市場競爭力的策劃編輯開始脫穎而出。出版業的供給側改革,應當積極圍繞這些市場敏感度高、產品駕馭能力強的策劃人及其團隊展開。目前,部分出版機構開始通過設立內部工作室、劃小經營核算單位、下放用人權、實行全成本核算、提高激勵比例等舉措,最大限度地貼近市場。
五是“補短板,互聯網+”。傳統出版企業在新媒體興起的浪潮下,除了要實現“媒介融合”外,還需要通過互聯網這一介質,使其產品快速傳導到市場和讀者群中,并通過尋找產品內容的市場共鳴,迅速形成營銷熱點。就實際效果而言,要補上傳統出版的“短板”,僅具有“互聯網+”的手段,還是遠遠不夠的。許多出版單位也開設了微博、微信等營銷賬號,但實際的效果不甚理想,大多成為“自彈自唱”的花瓶式窗口,有新媒體之形,而無其神。因此,“互聯網+”這一手段,仍需要與機制體制創新融為一體,與內容的創作融為一體,真正釋放其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