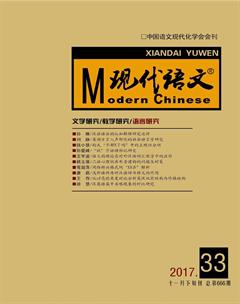人名典故翻譯中譯者主體性的發揮
摘 要:本文以《牡丹亭》汪榕培英譯本為研究對象,主要討論譯者主體性在人名典故翻譯中的發揮。《牡丹亭》中人名典故使用的特點有:人名典故在典故使用中占多數;人名典故多出現于人物對話中;人名典故連用情況較多。結合人名典故使用的特點和譯者主體性,本文提出在翻譯人名典故時,應從讀者、闡釋者和譯文作者三個方面對人名典故進行分析,并選擇恰當的翻譯方法。
關鍵詞:《牡丹亭》 譯者主體性 人名典故
一、引言
《牡丹亭》是我國明代戲劇家湯顯祖最為得意的一部作品,沈德符曾評價道:“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汪榕培,2001:18)。《牡丹亭》有如此高的評價是因為其文字優美,內涵豐富,修辭多樣。自上世紀90年代末期至今,《牡丹亭》有四個舞臺演出版本在維也納、巴黎、羅馬、倫敦、舊金山相繼上演,引起了西方觀眾的興趣(汪榕培,2001:22)。《牡丹亭》中有100多個典故,典故翻譯的優劣對傳播這部作品有著重要的影響。
二、譯者主體性與典故翻譯
傳統譯論一直以“原著中心論”“作者中心論”等來嚴格要求譯者恪守“隱形人”規則,消除自身在語言及文化轉換方面的操作痕跡,忠實完整地傳達原著所有信息(仲偉合、周靜,2006)。在我國,譯者的文化地位一直被邊緣化,被視為兩種語言的轉換器。但事實上,譯者是整個翻譯活動的主導者,也是翻譯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隨著20世紀70年代西方哲學的“語用學轉向”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的《文化轉向》以及斯皮瓦克、韋努蒂和尼南賈納等人翻譯成果的引進,翻譯研究的視野擴大了,西方譯學界開始關注翻譯主體性的研究(侯林平、姜泗平,2006)。目前,譯者主體性是中國譯學界研究的熱點之一。我國不少學者在專著中對譯者主體性作了專門論述,如:呂俊、侯向群(2001),劉宓慶(2001),胡庚申(2004)。
譯者主體性是指譯者“受到邊緣主體或外部環境及自身視域的影響制約下”(屠國元,2003),為實現翻譯目的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一種主觀能動性,核心是“翻譯主體的審美要求和審美創造力”(許鈞,2003),基本特征是“翻譯主體自覺的文化意識、人文品格和文化、審美創造性”(查明建,2003)。譯者的文化意識是發揮譯者主體性進行翻譯活動的前提,應與譯者的人文品格和文化、審美創造性并列,因此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要時刻保持文化意識。有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對譯者主體性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有闡釋學視角(劉暢,2016;屠國元、朱獻瓏,2003)、順應論視角(王穎頻,2015)、生態翻譯學視角(劉國兵,2011)和概念整合理論(金勝昔、林正軍,2016)等。
前人對古詩詞和小說中的典故翻譯進行了較多的探討,如:顧正陽(2004)、廖楊佳(2013)和孫易君(2007)。僅有少數學者關注中國古代劇本中的典故英譯,如:劉珊(2015)、黃采蘋(2010)和杜麗娟(2012)。許多學者從不同視角,如:欠額翻譯(褚雅蕓,2000、李莉,2006),譯者的翻譯取向(廖楊佳,2013)和功能對等理論(曹麗娟,2014)等對典故翻譯策略做了一番深入探討與研究,筆者試將其概括整理為直譯或音譯、直譯加注釋和意譯三大策略。前人對典故英譯的指導思想可總結為兩種:第一,顯化和隱化。不指特定人物時,典故翻譯可以采取“顯化”處理;典故體現詩人情感時則宜“隱化”處理,保留其形象(葛珊,2013)。第二,“詮釋性化入”。典故翻譯應當化隱為顯,化繁為簡,使解釋的語言符合譯詩的韻律和節奏(李瑞凌,2016)。但當采用顯化和隱化思想指導典故翻譯時,過多使用隱化會使譯文不被目的語讀者所理解;過多使用顯化就會使譯文不夠地道。對所有典故都進行詮釋性化入處理,則不利于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譯者主體性強調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文化意識的發揮,為典故翻譯研究提供了新視角和新思路,更能夠凸顯典故所蘊含的文化內涵。
三、人名典故
(一)人名典故
典故是“詩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出處的詞語”(李瑞凌,2013:116),是原作者為增加原文本的文學色彩從古代故事或古書中引用而來。典故具有豐富的內涵和鮮明的形象,有著鮮明的民族和文化色彩。典故可分為事典與語典(袁世全,1999)。前者指典源有故事情節的典故,典源多為神話、歷史故事等,后者指某人或某書首次創造或使用,后人相襲用的詞句,典源多為文獻或名作。典故按內容又可分為文化典故、歷史典故和文學典故(劉珊,2015)。
本文涉及的人名典故是指文學作品中引用的指代人物的人名、官職或外號等,可指虛構或真實存在的人物,與歷史故事、神話傳說有關。人名典故的理解對讀者的文學素養和背景知識有較高的要求,讀者只有與特定的語境或情境相聯系,才能理解典故內涵。
(二)《牡丹亭》典故的使用特點
1.《牡丹亭》100多個典故中大約有65個人名典故。這些人名典故涉及中國多個朝代,其中春秋與漢代的人名典故最多。這些人名典故所指代的人物所在年代距今較遠,典故來源也較為生僻,許多漢語讀者不一定理解,這為翻譯增加了難度。
2.《牡丹亭》中的人名典故多出現在人物對話中。人名典故連用情況較多,往往以對偶形式出現,如“不聞弄玉吹簫去,又見嫦娥竊藥來”。或者有三個連用的情況,如“小娘子畫似崔徽,詩如蘇蕙,行書逼真衛夫人”。人名典故中涉及的不僅有人名,還有官職或外號,如“歌的好。說與他,不是郵亭學士,不是陽羨書生,是本府太爺勸農。”
(三)《牡丹亭》人名典故的作用
《牡丹亭》中的人名典故多出現在人物對話中,用來表達觀點和愿望,描述、評價人或物。
1.人名典故的使用能簡明扼要地表達說話人的觀點和愿望。如《牡丹亭》中杜麗娘之父杜寶寫信給李全勸說他歸順宋朝,引用了“陸賈”和“莊蹻”兩個人名典故。前者以口才出眾傳世,后者的后代歸順朝廷,杜寶僅用了六個字“憑陸賈,說莊蹻”,表達了他勸降招安之意,言簡意賅,內涵豐富。
2.人名典故的使用能形象地描述評價人或物。柳夢梅在拾到女主角杜麗娘的自畫像時贊揚她“畫似崔徽,詩如蘇蕙,行書逼真衛夫人”。句中的這三位女子分別在畫、詩和書法領域有很深的造詣,柳夢梅把杜麗娘和她們相比,贊揚她才貌兼備。
四、《牡丹亭》人名典故翻譯中譯者主體性的發揮
譯者主體性貫穿于翻譯活動的全過程,譯者主體性體現在譯者對作品的理解、闡釋和語言層面上的藝術再創造,譯者需要表現出三種文學身份的能力,即讀者、闡釋者和作者(文學再創造者)(查明建、田雨,2003)。
(一)作為讀者的主體性
譯者在作品理解階段,需調動其文學審美能力,與文本進行對話,與作品達到視域融合,從而更好地完成文本構建。
(1)彭殤真一壑,吊賀每同堂。(湯顯祖《牡丹亭·鬧殤》)
譯文:Long life,short life,a grave contains them all;
For weal,for woe,the guests meet in the selfsame hall.
例(1)是杜麗娘的老師陳最良在杜麗娘死后向杜麗娘父親杜寶所說的話,意在人無論長壽或者短命都有一死,希望杜寶別太傷心。彭殤中的“彭”是指彭祖。彭祖在歷史上有著多重身份,分別是烹飪鼻祖、氣功祖師、房中始祖和長壽始祖。譯者在讀者階段根據文章語境從前面的“先結構”中選擇了“長壽始祖”這一含義進行翻譯。“殤”指“幼年夭亡”。譯者選擇用“Long life,short life”來表達“彭殤”二字,準確傳達了原文的核心意義。
(二)作為闡釋者的主體性
譯者充分理解作品后,需發揮其文學鑒賞和批評能力,對作品中的思想內涵和美學意蘊進行闡釋,同時分析作品的文學價值和社會意義。汪榕培(2001:41)在翻譯《牡丹亭》時提出了“傳神達意”的目標,主張翻譯唱詞和詩句時,在不影響英語讀者理解的前提下,盡可能地保持作者原有的意象。因此在處理各種文化內涵豐富的人名典故時,他選擇提取人名典故中符合原文語境的重點信息并使用簡單英語進行翻譯,方便西方讀者閱讀,這就是譯者在尊重原著內容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發揮譯者主體性。
(2)承尊覷,何時何日來看這女顏回?(湯顯祖《牡丹亭·診祟》)
譯文:You try to cure me but in vain;
When will you come to see me again?
例(2)是杜麗娘因游園尋夢病倒后,其父杜寶喚其師陳最良來為她診脈時,杜麗娘對老師說的一句話。既表達了對恩師來看望自己的感激之情,也表達了自己“命不久矣”的悲痛之情。該句中的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門生,極富學問、素以德行著稱,但不幸英年早逝。杜麗娘用“女顏回”形象地表達了自己有才卻短命的處境。對此典故,譯者如果選擇直譯其名,容易妨礙譯文讀者對原句意義的理解;如果選擇意譯,容易讓讀者感覺杜麗娘自視甚高,與原文表達的人物形象不符合,也失去了典故所呈現出來的含蓄美。因此,譯者汪榕培在闡釋階段省略該典故,僅用“me”來表達原文中女顏回所起的人稱指代作用。
(3)不枉了銀娘玉姐只做個紡磚兒,謝女班姬女校書。(湯顯祖《牡丹亭·訓女》)
譯文:In this way,she will not only know how to spin,
But also be an intelligent virgin.
例(3)中,杜麗娘的父親杜寶希望女兒成為一個既會女紅,又有才學的大家閨秀,于是決定為杜麗娘請一個家庭教師。在這句話中共有“謝女”和“班姬”兩個典故。“謝女”指的是晉代有名的才女謝道韞;“班姬”指的是漢代史學家班固的妹妹班昭,也是有名的才女;而“女校書”則是才女的統稱。三個詞凸顯了父親對女兒的殷切期望。譯者在這三個名詞中提取了“才女”這個重要信息。根據上下文可以發現杜麗娘是一個待嫁少女,所以翻譯時把“才女”與“待嫁少女”這兩個信息相結合譯成了“an intelligent virgin”,還用“not only...but also”句型表現了兩個分句間的邏輯關系。
(三)作為譯文作者的主體性
譯者在充分理解闡釋原作之后,以作者身份構建譯本時,需要注重如何再現原作的思想信息、審美信息和語言風格特征,完成整個翻譯過程。
(4)憑陸賈,說莊蹻。颙望麾慈即鑒昭。(湯顯祖《牡丹亭·圍釋》)
譯文:As I try to persuade you
To stop the strife,
Please take my words in full belief.
例(4)中的句子出自杜麗娘之父杜寶寫給李全的書信,信中勸說投靠金人的李全歸順宋朝。句子引用了陸賈和莊蹻兩個人名典故,前者是西漢政治家、文學家,以辯才著稱,受漢武帝和文帝派遣勸說趙佗王歸屬漢朝;后者是戰國時楚莊王的后裔,曾自立為王,其后代歸順漢朝。杜寶期望以西漢陸賈那樣的口才說服李全,李全也能像莊蹻后代一樣歸順朝廷。這句話中的兩個典故較生僻,所以譯者根據原文本語境把人稱換為第一人稱,用簡單直白的動詞“persuade”表達了劇中典故的內涵,而后文緊跟的“To stop the strife”則是壓了“s”的頭韻,讀起來瑯瑯上口,同時也表達了這兩個典故合用產生的意義,沒有造成語義缺失。譯者在此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僅用十個簡單的英文單詞就表達了兩個含義豐富的人名典故,可謂功力深厚。這種對語言的再創造也與原文的形式和音美相符合。
(5)小娘子畫似崔徽,詩如蘇蕙,行書逼真衛夫人。(湯顯祖《牡丹亭·玩真》)
譯文:This fair lady is good at painting,poetry and calligraphy.
例(5)是戲劇中男主角柳夢梅在拾到女主角杜麗娘的自畫像時給杜麗娘的評價。他用了三個人名典故來贊揚杜麗娘的美貌和才華。崔徽乃是唐代歌妓,與情人分別后,托人寄畫給情人曰:“崔徽一旦不及畫中人,且為郎死。”后人就多用崔徽指美麗多情或者擅畫的女子;蘇蕙,自幼聰穎,是魏晉三大才女之一,織出了一副回文錦《璇璣圖》,共840字,縱橫反復都可成詩句;衛夫人,東晉著名女書法家,師承道士鐘繇,尤善楷書,據傳是“書圣”王羲之的啟蒙老師。原文中僅用短短一句話就生動地表達了柳夢梅對杜麗娘多才多藝的欽慕。如在臺詞中提到三位才女的名字會讓觀眾對柳夢梅的感情歸向產生誤解,所以譯者根據原文語境提取三個典故中的重點信息:畫、詩和書法,直截了當地表明了杜麗娘的多才多藝。譯者考慮到人名過多可能會引發誤解,于是改變句式,把原文本的比較句改成了判斷句。譯者還把“小娘子”譯為“This fair lady”,用“fair”一詞凸顯柳夢梅對杜麗娘的喜愛與欽慕之情。
五、結語
《牡丹亭》使用人名典故較多,且多出現在對話中,對舞臺表演和觀眾理解是一個不小的挑戰。蘊含豐富文化內涵的人名典故需要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自覺充分地發揮譯者主體性。汪榕培先生翻譯《牡丹亭》時處理人名典故的方法值得后來者借鑒:先在讀者、闡釋者和譯文作者三個階段對人名典故進行分析,然后提取典故中符合原文語境的重點信息進行闡釋,這樣不僅可以保留原文內容,也保留了原文的形式美和韻律美。
參考文獻:
[1]曹麗娟.基于功能對等理論的典故翻譯對比[J].語文學刊(外語教育教學),2014,(8):63-65.
[2]查明建,田雨.論譯者主體性——從譯者文化地位的邊緣化談起[J].中國翻譯,2003,(1):22-24.
[3]陳靜.唐宋詩詞中典故英譯研究[D].杭州:浙江工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4]褚雅蕓.也談典故翻譯中的欠額補償——兼與樂金聲先生商榷[J].中國翻譯,2000,(4):64-67.
[5]杜麗娟.試論文學典故的翻譯策略——讀汪榕培英譯《牡丹亭》[J].瓊州學院學報, 2012,(8):86-87.
[6]葛珊,徐坤.從認知角度看中國古典詩詞中典故翻譯的顯化與隱化[J].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2013,(2):133-135.
[7]顧正陽.古詩詞中典故的翻譯[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11/1):46-51.
[8]侯林平,姜泗平.我國近十年來譯者主體性研究的回顧與反思[J].山東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8/3):100-104.
[9]胡庚申.翻譯適應選擇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10]黃采蘋.目的論視角下《牡丹亭》典故英譯的對比[J].科教文匯,2010,(25):127-128.
[11]金勝昔,林正軍.譯者主體性建構的概念整合機制[J].外語與外語教學,2016,(1):116-121.
[12]李莉.從欠額翻譯看《長恨歌》的典故翻譯[J].科技經濟市場,2006,(1):7-8.
[13]李瑞凌.出神入化了無痕——汪榕培翻譯詩歌典故策略管窺[J].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5/1):116-120.
[14]廖楊佳.唐詩英譯中典故翻譯策略試析[J].科技信息,2013,(24):188,190.
[15]劉暢.闡釋學理論視野下譯者主體性的彰顯[J].上海翻譯,2016,(4):15-20.
[16]劉國兵.翻譯生態學視角下的譯者主體性研究[J].外語教學,2011,(3):97-100.
[17]劉宓慶.翻譯與語言哲學[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2001.
[18]劉珊.從互文性角度看《西廂記》中典故的英譯[J].名作欣賞,2015,(18):61-62.
[19]呂俊,侯向群. 英漢翻譯教程[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
[20]孫易君.從圖式理論看《紅樓夢》典故翻譯[J].牡丹江大學學報,2008,(1):95-97.
[21]湯顯祖.牡丹亭[M].郭梅校注.長春:長春出版社,2013.
[22]湯顯祖.牡丹亭[M].汪榕培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23]屠國元,朱獻瓏.譯者主體性:闡釋學的闡釋[J].中國翻譯,2003,(6):8-14.
[24]汪榕培.《詩經》的英譯——寫在“大中華文庫”版《詩經》即將出版之際[J].中國翻譯, 2007,(6):34.
[25]王穎頻.動態順應:譯者主體性的發揮與制約[J].上海翻譯,2015,(4):76-79.
[26]夏征農,陳至立.辭海[Z].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
[27]許鈞.“創造性叛逆”和翻譯主體性的確立[J].中國翻譯,2003,(1):6-11.
[28]袁世全.關于典故詞典的十大關系[J].合肥: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1999,(2):59-64.
[29]仲偉合,周靜.譯者的極限與底線——試論譯者主體性與譯者的天職[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6,(7):42-46.
(呂肅肅 浙江寧波 寧波大學科學技術學院 315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