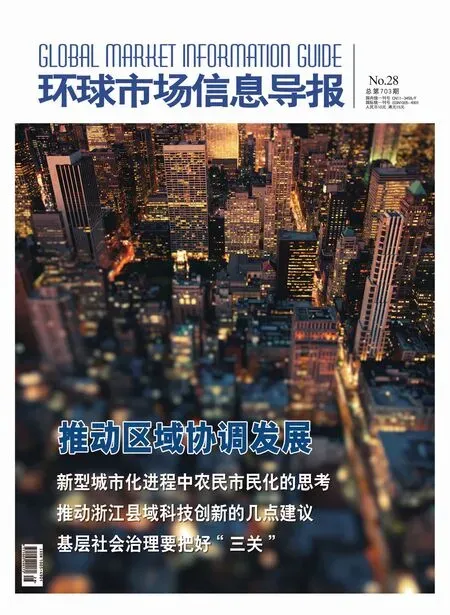致敬:向權(quán)力說明真理
■劉 亭/文
致敬:向權(quán)力說明真理
■劉 亭/文
大約一年后的今天,重讀了《第一財(cái)經(jīng)》彭曉玲的一篇采訪報道:“質(zhì)疑戶籍制度的陸銘說,京滬其實(shí)還不夠大”。
從陸先生財(cái)經(jīng)網(wǎng)上的數(shù)據(jù)來看,這也是最受歡迎的一篇,足有16650人讀過。但可惜的是,評論量還是0,那就讓我來填補(bǔ)一下空白吧!
有耐心讀完鴻篇巨制《大國大城》的,想必還不多。通過記者采訪,將陸銘振聾發(fā)聵的核心觀點(diǎn)昭然于世,從而得以廣泛傳播,這是件好事。尤其是想到處在城市管理權(quán)力頂尖的官員們,百忙纏身,日理萬機(jī),實(shí)在掉頭翻身、無暇他顧。能在極短的篇幅內(nèi),用最淺顯的語言“向權(quán)力說明真理”,實(shí)在更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天大好事了。
關(guān)于城市化問題,無非是一個城和人的關(guān)系如何把握、如何擺布的問題。而在這個基本問題上,又無非是兩種取向:一種是當(dāng)下通行的“以城限人”做法,還有一種就是被人認(rèn)為是“耳目一新”、“顛覆常識”的、以陸銘先生為代表的“以人擴(kuò)城”的主張。
“以人擴(kuò)城”說中的人,主要是指城市新增的外來人口,特別是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或謂文中聚焦的“低技能勞動力”“低端勞動力”(自然還會帶上其就業(yè)后需要共同生活和贍養(yǎng)的人口)。
陸銘的觀點(diǎn)不但旗幟鮮明——“北京、上海不是太大,而是太小”;“上海都市圈的人口預(yù)計(jì)將達(dá)到4100萬,這將是個世界級的都市圈。”“用行政力量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長,影響的不僅是城市,也會波及整個國家。”更重要的,他還在不經(jīng)意間點(diǎn)到了錯誤之所以流行的幾個思想認(rèn)識層面的根源。
其一:“長期以來,在關(guān)于城市和人口問題上,保守的聲音被傳播出去了,其他聲音卻有意無意被屏蔽。”
其二:“當(dāng)中國第二、三產(chǎn)業(yè)G DP已經(jīng)占到經(jīng)濟(jì)總量的90%時,而人們卻依然停留在農(nóng)業(yè)社會思維里。”
其三:“有人可能會說,大城市產(chǎn)業(yè)升級了就不需要低端勞動力了,這是一個巨大的認(rèn)識誤區(qū)。”
其四:“判斷世界上所有國家文明程度的標(biāo)準(zhǔn)是,公共服務(wù)偏向富人還是保護(hù)弱者。”
其五:“當(dāng)今中國特大城市的基礎(chǔ)設(shè)施、公共服務(wù)供給,是根據(jù)歷史上預(yù)測出來的人口增長來決定的,而歷史預(yù)測又是大大低估了人口的實(shí)際增長,所以才造成‘城市病。’”
其六:“現(xiàn)在中國的問題就是,人多(人口集聚)帶來的好處看不見,帶來的壞處卻被夸大了。”
有一個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根源,他沒有直接提及,但在對“以業(yè)控人”等政策和做法作出批評的字里行間,我覺得他早已聲明了,也即:政府官員,恐怕缺乏了一點(diǎn)對于市場的敬畏之心和謙卑之情。以為那種烏托邦式的“一廂情愿”,能通過“自己看得見的手”,令其成為中國大地上的現(xiàn)實(shí)。
但是,政市關(guān)系的背后,歸根結(jié)底還有一個主客觀關(guān)系的認(rèn)識論問題。我們是唯物主義者,無論是認(rèn)識世界還是改造世界,都還是要恪守唯物辯證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都還是要遵循客觀規(guī)律。
城市化的客觀規(guī)律是什么?就是隨著工業(yè)化的興起、以及工業(yè)化對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勞動生產(chǎn)率的提升,眾多農(nóng)民一定會大量地從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中轉(zhuǎn)移出來,進(jìn)入城市。因工業(yè)規(guī)模經(jīng)濟(jì)集聚的人口,一定會伴生出服務(wù)業(yè)的大發(fā)展和相應(yīng)就業(yè)人口的大增加。而二、三產(chǎn)業(yè)及其就業(yè)和贍養(yǎng)人口,在一個狹小地理空間高密度的集聚過程,正是傳統(tǒng)工業(yè)化時代城市的發(fā)生、發(fā)展和壯大過程。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和信息傳播成本的顯著降低,區(qū)域城市化和城市區(qū)域化的趨勢明顯強(qiáng)化,都市圈和城市群開始成為新型城市化的主體形態(tài)。換句話說,以原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為核心,在一定空間距離內(nèi)(如高速通勤圈范圍內(nèi)),帶動周邊中小城市及特色小鎮(zhèn)發(fā)展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將仍然會大量吸納和承載就業(yè)人口,包括所謂的“高技能和低技能”人口,同時也包括其共同生活和贍養(yǎng)的其他人口(闔家老小)。
由此可見,再囿于傳統(tǒng)小生產(chǎn)甚至是傳統(tǒng)工業(yè)化思維的決策,該是多么的不合時宜!如果是平頭百姓拘泥于此,倒也罷了,無非是“蘿卜青菜、各人各愛”。但如果還讓這種思維定勢成為城市管理者工作的運(yùn)行慣性、路徑依賴甚至是固化為某種體制窠臼,那就恰如陸銘先生所擔(dān)憂的那樣:“如果不充分認(rèn)識到未來城市人口和發(fā)展的趨勢,今后造成的城市問題還會更大。”
或因此,我才痛感陸銘先生“向權(quán)力說明真理”的社會責(zé)任感之強(qiáng)烈、之不易,我才即興寫下這篇粗淺的學(xué)習(xí)體會,借此表達(dá)我由衷的敬意!
2017年10月15日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