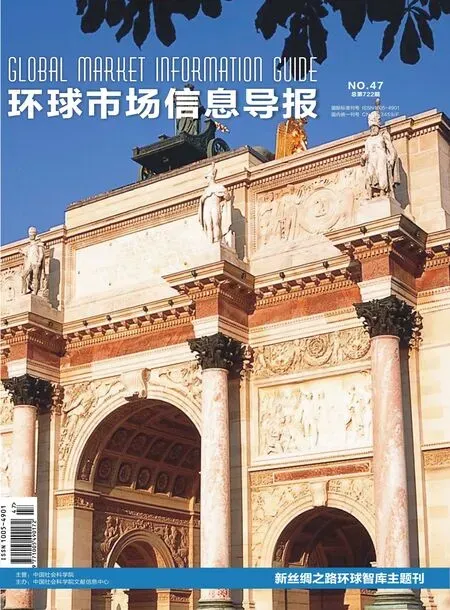于歡刺殺辱母者一案
◎ 孟伊文
于歡刺殺辱母者一案
◎ 孟伊文
于歡在阻止對其實施非法拘禁、侮辱其母的涉黑催債團伙的不法侵害活動時,用尖刀將一人刺死,三人受傷。該案件引發社會廣大關注,一審認定其不構成正當防衛并判處無期徒刑,二審對其改判,認定于歡構成正當防衛且屬防衛過當,因而判處有期徒刑五年。本文對故意與過失、故意殺人與故意傷害、正當防衛與特殊防衛以及防衛過當這幾組刑法概念進行法理上的辨析,從而認定二審判決的正確性。同時我們應看到該案的意義所在,其適當放寬了正當防衛的條件限度,彰顯其立法精神,有助于弘揚勇于與不法勢力作斗爭的良好風氣,為我國正當防衛制度的發展起了良好的推動作用。且其在還原事件真相、堅守法律底線的同時,回應了社會的關切,將公平與正義體現在每一個案件中,既為我國的司法體系注入了一股活力,也為社會注入了一份正能量。
2016年4月14 日,因民間借貸糾紛,被害人杜志浩等催債人員強行將欠債人蘇銀霞及其子于歡帶入蘇銀霞所在公司的辦公樓一樓接待室內進行討債。期間,杜志浩等人多次用污穢言語辱罵蘇銀霞。更有甚者,將褲子褪至大腿處朝蘇某裸露下體。民警到達后,于歡欲隨民警離開,但被杜志浩等人卡頸部阻止,慌亂中于歡持尖刀將杜志浩等四人捅傷,致使杜志浩失血過多死亡,其余二人重傷,一人輕傷。一審法院判決被告人于歡故意傷害并處無期徒刑,于歡不服原判上訴。此判一出,社會輿論嘩然,針對社會上要求法理與情理和諧統一的呼聲,山東省高院對本案重新審理,認定于歡犯故意傷害罪,但其行為系正當防衛,且屬于防衛過當,改判有期徒刑五年。本文將立足于法院判決經過,對其判決進行法理上的梳理,以析其對我國正當防衛制度以及日后類似案件處理的意義。
判決梳理
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于歡沒有正確處理與討債人員的沖突,持尖刀捅刺多人,致使嚴重后果,其行為不存在正當防衛意義上的不法侵害前提,已構成故意傷害罪。同時,鑒于被害人采取不當方式討債,具有過錯,可對于歡從輕處罰,因而判處無期徒刑。于歡不服原判上訴。
二審法院審理查明,(1)于歡捅刺被害人時不法侵害正在進行,其捅刺的對象都是在其警告后仍向前圍逼的人,因此可以認定其行為是為了制止不法侵害,屬正當防衛;(2)整個事件中雙方不存在強迫借貸的事實,因而不屬于搶劫,不符合特殊防衛的構成要件;(3)于歡面臨的不法侵害并不緊迫,其防衛行為卻明顯超過必要限度,致一死三傷,屬于防衛過當;(4)于歡的目的在于制止不法侵害以求離開接待室,而有關證據不能證實其具有追求或放任致人死亡危害結果發生的故意,因此不屬于故意殺人;(5)民警責令于歡交出尖刀,其并未聽從,無自動投案的意思表示與行為,不屬于自首。同時考慮到被害人事發前曾有侮母等行為,因而二審改判于歡有期徒刑5年。
法理分析
于歡對其行為結果主觀上系間接故意。故意與過失二者之間并非對立關系,而是回避危害結果的高低度的位階關系,其主觀惡性相差甚遠。本案中于歡連續捅刺四人,對其危害行為的性質與結果顯然有所預見,當屬故意。其中故意又分為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兩種,二者的根本區別在于,在明知自己的行為會造成危害結果前提下,是希望還是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結合本案案情,被害人的傷口主要在背部,可見于歡的目的在于制止不法侵害并離開該房間,其主觀狀態應是在情緒沖動的情況下,不計后果在實施了危害行為并放任其危害結果發生,屬間接故意。
本案系故意傷害而非故意殺人。學界普遍采納殺人行為必然包含傷害行為,殺人故意必然包含傷害故意的單一理論。二者之間并非對立關系,即在行為人可能預見到死亡結果的情況下,若不能證明其主觀上追求或放任死亡結果的發生,應從存疑時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出發,認定為故意傷害。本案中,沒有證據能證實于歡主觀上有追求被害人死亡的故意,其捅刺對象都是當時圍逼在其身邊的人,且并未針對一人連續捅刺,因而難以認定為故意殺人,一、二審法院對其行為屬故意傷害的定性準確且合理。
于歡的行為具有防衛性質。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于歡的行為是否構成正當防衛,其難點在于對“不法侵害現實存在”、“不法侵害正在進行”這一對概念的認定。從正當防衛的起因條件上看,即要求有現實存在的不法侵害行為,于歡面臨著被害人杜志浩等人用限制人身自由方式的暴力索債,且期間伴有肢體沖突與語言挑釁行為,其人身安全已切實的面臨著現實的威脅;從防衛時間上看,即要求不法侵害正在進行,假使不法侵害行為間斷停止,但全部不法侵害并未完全終止,其仍面臨被不法行為繼續侵害的危險時,仍應認定為不法侵害正在進行。在本案中,雖然杜志浩等人被捅刺時沒有對于歡進行毆打,但當時于歡仍處于被非法拘禁的狀態中,非法拘禁屬于狀態犯,被害人的行為仍對于歡及其母有所威脅,于歡進行正當防衛滿足時間要件;從防衛對象與防衛意圖來看,于歡捅刺的對象都是在其警告后仍向前圍逼的人,其意圖在于制止不法侵害,維護自身安全,滿足正當防衛的對象條件與主觀條件。
于歡的防衛行為不屬于特殊防衛。我國《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于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即對正在進行的搶劫等暴力犯罪,公民有權進行特殊防衛。同時,雖然《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強迫借貸行為適用法律問題的批復》中規定強迫借貸可按搶劫罪論處,但在本案中蘇銀霞系自愿借貸,其對10%的月息的借款是知情且自愿的,因而不存在被強迫高息借貸的事實,因此本案中并不存在搶劫這一前提條件,在此也不能適用特殊防衛條款。
于歡的防衛行為已然超過必要限度。評判防衛是否過當,應當從權衡防衛行為的手段、強度是否與當時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行為的手段、強度相適應,防衛行為是否控制在有效制止不法侵害進行的限度之內出發。就本案而言,于歡及其母僅面臨被限制人身自由,人格尊嚴受辱,輕微毆打的不法侵害行為,對生命安全威脅不大,且警察尚在不遠處,而于歡貿然用尖刀捅刺索債人員,造成一死三傷的嚴重后果,其行為顯然已超出必要限度,應屬防衛過當。
綜上所述,原判認為于歡捅刺被害人的行為不存在正當防衛意義上的不法侵害,該項認定不太妥當。其并未充分認識到被害人實行非法拘禁行為的性質,也未考慮于歡當時所處環境的緊迫性,對正當防衛的時機條件的理解亦有所偏差,因而造成誤判。而二審法院基于案情,對案件進行了全面剖析,對本案是否構成正當防衛重新定義,糾正了一審判決,認定于歡行為屬于正當防衛,其整體判決過程堅持了“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是一例較為優秀的判決。
刑法第二十條關于正當防衛的規定幾經修訂,不難看出國家對于公民實施正當防衛的重視。其立法精神不僅在于國家鼓勵公民在國家財產、個人生命受到嚴重威脅時,免除后顧之憂,挺身而出,勇于同邪惡勢力斗爭。這有助于改變當今大眾害怕出力不討好,袖手旁觀以至于不法勢力漸趨猖狂的現況,同時對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養公民維護正義、保護弱小的高尚品質有著積極作用。但司法實踐中,對正當防衛的適用條件采嚴格認定的態度,正方防衛條款日趨僵化。本案中,二審正確把握正當防衛條款的立法精神,適當放寬了對正當防衛的條件限度,認定于歡系正當防衛并且結合倫理道德因素審慎量刑,既不違背司法判定的原則,彰顯了法律的價值取向,又維護了公民正當的權利,在社會上也弘揚了勇于同不法勢力作斗爭的良好風氣,對今后類似案件的處理提供了優秀范例。
同時,我們應該看到,于歡案之所以成為近年的典型案列,原因不僅僅在于其公開透明審理,更在于本案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社會如此抵觸一審結果,無外乎一審判決結果與大眾的期望與關切發生較大偏離,難以獲得社會的普遍認同。二審的改判,雖是在社會輿論的呼聲中進行的,但卻是在正確適用法律、確保裁判結果公平公正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接近實際情理而做出的,既不違國法,又合乎人們的樸素情感。
悟以往冤假錯案之不鑒,知來日之可追,于歡案的成功改判為司法體系注入了一股活力,也為社會注入一份正能量。追求法律正義與社會正義的和諧統一,是完善司法體系、建設法治中國的一塊硬骨頭,也是司法審判機關必須長期堅持的一種理念。
山東省萊蕪第一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