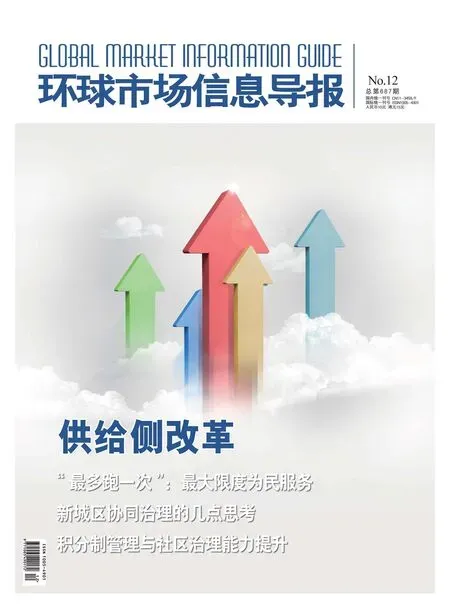城市化改革:“經濟下行”的救星?
■劉 亭/文
城市化改革:“經濟下行”的救星?
■劉 亭/文
◆評論◆
拜讀周天勇先生的宏論,深以為然:“十九大以后確實應該珍惜所剩不多農村休眠土地資產的激活,珍惜時間不等人的城市化潛力人口盡快盡可能城市化。產權改革,取消戶籍,就是城鄉(xiāng)之間的互動,人口和資金等城鄉(xiāng)雙向流動。”
之所以將原文標題中的“那些城市化潛力人口,是經濟下行的救星”的前半句,調整為今文題目的“城市化改革”,主要是刻意強調改革對于當今中國國情的特殊針對性。
記得還是在2006年6月26日,我在看到清華老師胡鞍鋼的一篇文章時,標題中用到了“新型城市化”這個詞兒,那大約是全國最早原創(chuàng)使用的吧?——起碼以我有限的閱知——我信手寫了一篇點評:《這是一個好命題》。在我來看,所謂新型城市化的“新”,起碼有三大要點:一是從“人”的角度,也就是城市化的出發(fā)歸宿,要“以人為本、城鄉(xiāng)協(xié)調、社會和諧”;二是從“物”的角度,也就是城市化的發(fā)展方式,要“結構優(yōu)化、資源節(jié)約、環(huán)境友好”;三是從“制”的角度,也就是城市化的制度安排,要“破除二元、推進(城鄉(xiāng))一體、創(chuàng)新(體制改革)發(fā)展”。
我以為,就“中國特色”而言,城市化說到底,還是一個對傳統(tǒng)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體制改革創(chuàng)新的過程。計劃經濟留給我們的三大遺產中,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體系改得差不多了;“重工業(yè)優(yōu)先”的斯大林模式也改得差不多了;但是城鄉(xiāng)分割的二元結構體制這一塊,一直延續(xù)到今天。雖然其間也經歷了不少的改變,但成績并不可估計過高,戶籍、土地加上公共財政及社會保障等改革都有待于深化,頂多也就是個“半拉子工程”。
毫無疑問,行至中途的城市化,肯定是發(fā)展中的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的一道坎。改革開放以前,中國長期實行人為打壓城市化的方針,為的是在一個極其微薄的人均國民收入基礎上,加速實現(xiàn)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yè)化”。乃至改革開放以后,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yè)化的尷尬局面。只是到2000年,人類社會即將邁入21世紀的當口,我們才在新中國建國長達半個世紀之后,通過“十五”計劃的《建議》及《綱要》,正式將城鎮(zhèn)化(和城市化是一回事)納入執(zhí)政黨的“宏偉藍圖和行動綱領”。
中國大規(guī)模的城市化進程,起步于實行大包干以后的農業(yè)生產力的解放,勃興于城鎮(zhèn)個體私營經濟的崛起和國有經濟的改制,以及與此相適應的城鄉(xiāng)人口管制政策的松動。至于農民工成為一個兩億多人口的龐大社會群體,則是與我國加入WTO、經濟深度全球化的開放有關。伴隨著世界第一工業(yè)制造大國和產品出口大國地位的形成,我國以常住人口為統(tǒng)計口徑的城市化率,順利越過了50%的關口。
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性進步。綜合國力的增強、城鄉(xiāng)面貌的改變、人民生活的提高,都與這一進步相關,并且表現(xiàn)為一系列突破城鄉(xiāng)二元結構體制改革的必然結果。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后,國際經濟大格局發(fā)生重大改變。銳減的出口需求和久久難以有效提升的國內需求,導致經濟增長的動力減弱。一枝獨秀的投資需求,本來就是病態(tài)。加之以大量的貨幣投放和債務支出加以支撐,當然是勉為其難,難以為繼。
那么出路在哪里呢?當然是城市化!為此我曾在危機之后的若干年里,一論再論這一話題。但就像明明知道中國經濟需要走上一條科學發(fā)展之路,但只要不能有效破除阻礙科學發(fā)展的體制機制羈絆,一切無非都將淪落為口號式的空談一樣,城市化也因為戶籍、土地、公共財政及社會保障等相關體制改革的羞羞答答、步履蹣跚,至今沒有也不可能成為應對危機的出路,或如周先生所言,變成“是經濟下行的救星”。
講到這里,我套改題目的用意就很清楚了:沒有城市化配套改革的“開路”,在舊的體制框架下,潛力人口永遠只能潛在水底下,不會成為阻遏經濟下行的“救星”。中國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史尤其是農村大包干、發(fā)展城鎮(zhèn)民營經濟和加入WTO這三個標志性事件告訴我們:“問題導向的改革改到哪里,我們克服了體制摩擦力以后的發(fā)展,就會發(fā)到哪里”。沒有改革而想謀求發(fā)展,對中國特色的國情而言,基本上就是緣木求魚,“墻上掛簾子——沒門!”
昨天下午,我很幸運地在第二期博思發(fā)展論壇上,“主持”了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教授的主題演講:《要素供給至關重要》。開篇第一張PPT,先生就為聽眾展示了一張“三明治”的示意圖。其上層,是以G7國家為代表的發(fā)達經濟體擁有的“獨到性優(yōu)勢”,諸如科技創(chuàng)新、現(xiàn)代金融、成熟的市場體制之類;其下層,是以印度、越南等國代表的后發(fā)國家,他們勞動力、礦產資源、環(huán)境和土地等等的“成本更低”;上下一夾,恰恰是把“成本優(yōu)勢漸失、獨到性優(yōu)勢尚無”的中國,擠到了一個不上不下、兩頭受擠的尷尬境地里。
已然是三明治夾心層這種“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了,那我們的出路又何在呢?先生的結論是沒有什么捷徑可走。無非“兩頭突破”:一是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提高你產品和服務的科技、人文附加值;一是全面深化改革,把半拉子改革工程實施到位。這其中,也包括了周天勇教授文章中大聲呼吁的“城鄉(xiāng)(要素)雙向流動”的“產權改革,取消戶籍”。
正是在此意義上,城市化改革是“經濟下行”的救星!
2017年5月28日成稿
◆背景文章◆
周天勇:那些城市化潛力人口,是經濟下行的救星
十九大以后確實應該珍惜所剩不多農村休眠土地資產的激活,珍惜時間不等人的城市化潛力人口盡快盡可能城市化。產權改革,取消戶籍,就是城鄉(xiāng)之間的互動,人口和資金等城鄉(xiāng)雙向流動。
農地產權和取消戶籍改革是未來中期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
農村土地產權結構上不清,市場體制上不能交易,不能抵押,資產價格幾乎為零,土地的財富效應和財產性收益,通過政府征用低價將農村的土地往城市這邊轉移,這里城市是行政寡頭壟斷的市場,土地和房屋價格暴漲,央行給他放貨幣,最后財富效應非常明顯,形成極大的城鄉(xiāng)之間的收益和分配差距。而農村土地因為不能交易,為因管制而被“凍結休眠資產”。投資就進不來,這與中國臺灣地區(qū)、韓國有非常大的差異,結果是農村資產沒有財富增長和財產收益增長效應,而城市土地及其價格暴漲。
十九大以后確實應該珍惜所剩不多農村休眠土地資產的激活,珍惜時間不等人的城市化潛力人口盡快盡可能城市化。產權改革,取消戶籍,就是城鄉(xiāng)之間的互動,人口和資金等城鄉(xiāng)雙向流動。
從我們一些基礎數(shù)據(jù)的計算,如果戶籍放開,加上財政體制的改革,在城市里,支出結構要把經濟建設這一塊降低,把教育,這些公共服務的支出比例提高。農民帶孩子來,得讓人家上學,類似問題解決了,增長的潛力是非常大的。
(來源:公眾號天勇看經濟zhouty-tjj,本文有刪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