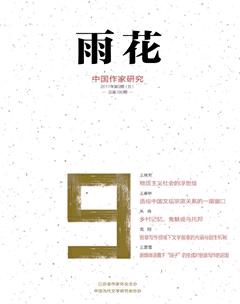透視中國文壇宗派關(guān)系的一扇窗口
王春林
迄今為止,我所認(rèn)真閱讀過的陳為人作家傳記作品一共有四部。這四部作家傳記的傳主分別是唐達(dá)成、趙樹理、周宗奇和馬烽。其中,除了唐達(dá)成之外,另外三位都是清一色的山西作家。山西作家之所以會(huì)成為陳為人集中關(guān)注審視的對(duì)象,原因當(dāng)然在于陳為人自己長期供職于山西省作家協(xié)會(huì),生活寫作于山西文壇,對(duì)于這些傳主的人生與寫作事跡非常熟悉的緣故。既如此,這些作家出現(xiàn)在陳為人的筆下,成為作家的傳記書寫對(duì)象,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在這里,需要多說兩句的是唐達(dá)成。只要是讀過陳為人《唐達(dá)成文壇風(fēng)雨五十年》①的朋友,就都會(huì)知道,唐達(dá)成雖然不是山西作家,但在二十世紀(jì)五六十年代被錯(cuò)誤地打成“右派”之后,唐達(dá)成就被懲罰性地下放發(fā)配到了山西太原,成了太鋼的一名普通工人。當(dāng)是時(shí)也,年輕的陳為不僅人也正在這家大型企業(yè)工作,而且還狂熱地喜歡文學(xué)。唐達(dá)成受懲罰被下放太鋼,但對(duì)于陳為人他們來說,唐達(dá)成的到來卻是天大的喜事。請(qǐng)?jiān)O(shè)身處地想一想,自己身邊突然現(xiàn)身這么一位可謂是國家級(jí)的優(yōu)秀評(píng)論家,可以隨時(shí)請(qǐng)教文學(xué)方面的問題,對(duì)于癡愛文學(xué)的陳為人們來說,可不就等于是天上掉下了大餡餅。有了文學(xué)這樣一個(gè)重要的媒介,唐達(dá)成與陳為人成為患難與共非常要好的朋友,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個(gè)時(shí)候的陳為人,又哪里能夠想得到,人間世事,白云蒼狗,多少年之后,自己口口聲聲喊著叫著的“唐師傅”唐達(dá)成,居然又會(huì)重返京城,居然還成了中國作協(xié)的黨組書記,一度執(zhí)中國作協(xié)之牛耳。正因?yàn)槟莻€(gè)特定的歷史時(shí)期注定了這樣一種特殊的緣分,所以,在唐達(dá)成過世之后,由陳為人來完成如此一本可謂字字泣血、情真意切的《唐達(dá)成文壇風(fēng)雨五十年》,就自在情理之中了。更何況,早在“文革”結(jié)束之前,馬烽就產(chǎn)生過把唐達(dá)成調(diào)到山西文聯(lián)(當(dāng)時(shí),山西文聯(lián)與山西作協(xié)還沒有分家,山西作協(xié)只是山西文聯(lián)的一個(gè)下屬部門)來工作的想法。這里,且以馬烽的一段肺腑之言為證:“……其實(shí),我早就有心把你調(diào)回來。還是‘文革前,我聽說把你打發(fā)到山西了,我就有心把你安排回文聯(lián)來。為什么呢?咱們山西文聯(lián)作協(xié),寫小說的還有這么幾苗人。西戎呀、孫謙呀、胡正呀、我也算一個(gè)。寫得不咋地吧,總能揮舞兩下子。可詩歌、理論就不行,算把手的人不多,那時(shí)候,我就想把你和公劉調(diào)回來。所以,我有我調(diào)人的理由。……李束為不同意。”②因?yàn)樵獾搅死钍鵀榈膱?jiān)決反對(duì),馬烽的調(diào)人設(shè)想受阻無果。完全可以想象,假若沒有李束為的堅(jiān)決反對(duì),或許唐達(dá)成真成了一位山西作家也未可知。總而言之,盡管唐達(dá)成不是山西作家,但因了他與山西文壇或者說與陳為人個(gè)人之間的歷史淵源,他出現(xiàn)在陳為人筆端,成為陳為人作家傳記的書寫對(duì)象,就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同樣是以文學(xué)創(chuàng)作為業(yè)的作家,李束為為什么就要相煎太急?為什么就非得堅(jiān)決反對(duì)把唐達(dá)成調(diào)入文聯(lián)工作呢?還是讓我們來看馬烽的敘述:“李束為當(dāng)然有李束為的考慮。第一,咱們機(jī)關(guān)本身右派好幾個(gè),你再收留外邊的右派?公劉也是右派。”但第二條馬烽卻并沒有痛痛快快地告訴陳為人,一直到很久之后,陳為人再次追問有關(guān)問題時(shí),馬烽才交待說:“不能公開說的是個(gè)啥問題呢?李束為是怕我的勢(shì)力大。李束為總有一種無形的壓力……后來有人對(duì)我說,李束為怎么會(huì)要,弄上你的人就更多了。”②84—85頁我們此處關(guān)于李束為反對(duì)把唐達(dá)成調(diào)入山西文聯(lián)工作的分析,其實(shí)已經(jīng)觸及到了本文的寫作主旨,那就是,對(duì)于陳為人這部作家傳記中所主要揭示出的籠罩中國文壇多年的宗派關(guān)系進(jìn)行相對(duì)深入的梳理與分析。說實(shí)在話,讀陳為人的作家傳記越多,就越是能夠強(qiáng)烈地感覺到他的傳記作品的與眾不同。讀陳為人的作家傳記,總是讓我情不自禁地聯(lián)想到歐陽修那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的名言來。簡(jiǎn)單地說,如果沒有酒,何來醉翁也?離開酒,絕對(duì)不會(huì)有醉翁。這也就是說,只有借助于酒,才會(huì)有山水之樂的出現(xiàn)。因此,要想完整地理解歐陽修的意思,我們還必須注意到那篇《醉翁亭記》中緊接著的下一句:“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由“寓之酒”即可以看出,醉翁自己內(nèi)心是非常明白的,他知道如果沒有酒,就絕不會(huì)有什么山水之樂。借此來觀照陳為人的作家傳記,我們也就可以說,陳為人的作家傳記中往往是既有“酒”也有“山水之樂”的。所謂“酒”,就是指?jìng)髦鞅救恕K^“山水之樂”就是說,陳為人的作家傳記,往往并不只是滿足于把作家的生平事跡展示在廣大讀者的面前,在充分展示作家生平事跡的同時(shí),他總是有更為深切的言外之旨想要表達(dá)出來。據(jù)我的理解,這種言外之旨,在《唐達(dá)成文壇風(fēng)雨五十年》中,是對(duì)于中國文壇長達(dá)五十年之久的風(fēng)風(fēng)雨雨進(jìn)行真實(shí)的描寫與鋪敘。在《插錯(cuò)了“搭子”的一張牌——重新解讀趙樹理》③中,是對(duì)于政治與文學(xué)關(guān)系的再度深入探討,以及對(duì)于趙樹理這一類作家的精神價(jià)值立場(chǎng)定位。這部《馬烽無刺》自然也不例外。在這里,這部作品的副標(biāo)題“回眸中國文壇的一個(gè)視角”就顯得極其重要了。由馬烽而回眸中國文壇固然重要,但更為關(guān)鍵的問題還在于,到底要回眸澄清什么呢?我以為,陳為人在他這部關(guān)于馬烽的傳記中,所欲深究的一個(gè)根本問題,正是困擾中國文壇多年的宗派問題。
話題再回到李束為。人們都知道山西文壇的“西李馬胡孫”是關(guān)系密切的五戰(zhàn)友,但卻很少有人清楚,就在這可謂是親密無間的戰(zhàn)友之間,卻也免不了會(huì)有宗派情緒的生成,會(huì)有宗派主義的問題出現(xiàn)。這一問題,主要就體現(xiàn)在馬烽與李束為他們倆人關(guān)系的復(fù)雜糾結(jié)上。1949年之后,馬烽本來一直在北京中國作協(xié)工作。為了更好地深入生活以創(chuàng)作出更優(yōu)秀的文學(xué)作品,當(dāng)然也是為了逃避所謂周揚(yáng)、丁玲之間尖銳復(fù)雜矛盾的纏繞,用馬烽的原話說,就是“京華雖好,卻是是非之地。惹不起咱還躲不起?三十六計(jì)走為上。”②19頁馬烽斷然決定,離開北京,回山西去。馬烽根本沒有想到,山西也并非世外桃源,雖然較之于中國文壇要小了許多,但山西也還是有一個(gè)文壇在的。馬烽根本想不到,回到山西之后,自己很快就會(huì)陷入到與李束為的矛盾之中。而這李束為,卻并不是什么你死我活的敵人,不僅是自己多年的老戰(zhàn)友,而且還同為“山藥蛋派”的代表性作家。當(dāng)時(shí),李束為作為山西文聯(lián)的黨組書記,主持文聯(lián)的日常工作。馬烽從北京回來,一個(gè)無法回避的問題,就是誰當(dāng)文聯(lián)主席誰在文聯(lián)當(dāng)家的問題。雖然馬烽力辭文聯(lián)主席和黨組書記的位置,甘居李束為之下,只是擔(dān)任了文聯(lián)的副主席和副書記,但李束為卻從此形成了一個(gè)終身都無法解開的心結(jié)。對(duì)于這一點(diǎn),他們共同的老戰(zhàn)友,作家胡正有著一針見血的評(píng)述:“那時(shí)李束為是文聯(lián)主席、黨組書記,馬烽是副主席、副書記。李束為內(nèi)心有個(gè)根本的矛盾,根本的矛盾是什么呢?主要問題是領(lǐng)導(dǎo)地位與文學(xué)成就的問題,這是問題的核心。一是他是山西省文藝界的最高領(lǐng)導(dǎo),但在創(chuàng)作上又次于其他人。這是他的根本矛盾。”②95頁按照邏輯推理,既然身為山西文壇的最高領(lǐng)導(dǎo),身為山西文壇的掌門人,創(chuàng)作成就就應(yīng)該是最高的。但實(shí)際上,在當(dāng)時(shí),李束為的創(chuàng)作成就之不能望馬烽的項(xiàng)背,卻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于是,一方面留戀著文壇的權(quán)位,另一方面卻又因?yàn)樽约旱膭?chuàng)作成就不夠高而心有戚戚忌憚旁人。盡管馬烽心胸足夠坦蕩,但在頗有鄰人之斧心理的李束為這里,情況卻沒有這么簡(jiǎn)單。正因?yàn)槔钍鵀椴粺o先驗(yàn)色彩地認(rèn)定,馬烽回到山西,就是要搶走自己所擁有的權(quán)力和地位,所以,他才會(huì)處處提防馬烽,才把馬烽看作是自己人生中最主要的一個(gè)對(duì)手。于是,也才會(huì)有拒調(diào)唐達(dá)成事件的發(fā)生。不僅如此,李束為與馬烽之間長達(dá)數(shù)十年之久的恩恩怨怨,恐怕也只有從這個(gè)角度方才能夠得到一種合情合理的解釋。endprint
馬烽與李束為之間的恩怨糾葛,固然值得我們關(guān)注思考,但相比較而言,更需要引起我們充分注意的,卻是在更大程度上決定影響著馬烽在中國文壇命運(yùn)沉浮的周揚(yáng)與丁玲之間的更為盤根錯(cuò)節(jié)的宗派矛盾。陳為人之所以要從丁玲開始敘述馬烽的故事,之所以把周揚(yáng)與丁玲之間的矛盾糾結(jié)作為這部《馬烽無刺》的敘事重心所在,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我們?cè)谇懊嬉呀?jīng)提及,馬烽之所以堅(jiān)持要遠(yuǎn)離北京回到山西來生活寫作,正是因?yàn)橐颖苤袊膲邔又軗P(yáng)與丁玲之間復(fù)雜矛盾糾結(jié)的緣故。然而,令馬烽所始料未及的是,回到山西之后,他不僅陷入了與老戰(zhàn)友李束為的矛盾沖突之中,而且也并沒有能夠徹底掙脫周揚(yáng)與丁玲矛盾對(duì)他人生命運(yùn)的制約與影響。這一點(diǎn),集中爆發(fā)在“文革”結(jié)束,周揚(yáng)和丁玲相繼復(fù)出之后的新時(shí)期。對(duì)此,陳為人在《馬烽無刺》中,有著非常清晰的描述和判斷:“客觀地說,唐達(dá)成、馬烽二人,都是淡漠為官而認(rèn)真做事的人,而且,主觀上都不愿意攪合進(jìn)文壇的矛盾漩渦中去。然而,歷史老人卻有喜歡惡作劇的小孩脾性。令唐達(dá)成、馬烽想不到的是,若干年以后,偏偏是他倆,陰差陽錯(cuò)地被激烈沖撞的兩大板塊,選中為各自利益的代言人,竟然因?yàn)橹袊骷覅f(xié)會(huì)黨組書記,此文壇‘第一把交椅的位置,或有心或無意,或正面或迂回,或主動(dòng)或被動(dòng),或淡然或激烈,或身不由己隨波逐流,或戴著面具作為木偶,于1984年、1987年、1989年,三起三落、三進(jìn)三出、上演了‘三上桃峰‘三進(jìn)山城‘三打祝家莊的連本大戲。”②123頁這兩大板塊,不是別的,正是最早萌發(fā)于延安時(shí)期且長期困擾中國文壇發(fā)展的周揚(yáng)與丁玲這兩個(gè)文人集團(tuán)。對(duì)于自己所扮演的這種角色,唐達(dá)成與馬烽都是心知肚明的。“唐達(dá)成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說過這樣的話:‘我們是地球人。我們必然處于各種板塊的擠壓沖撞之中。”“馬烽說:‘由人不由人,我是被夾在了丁玲和周揚(yáng)兩人之間。”②124頁有鑒于此,陳為人才會(huì)有更進(jìn)一步的理解與推論:“唐達(dá)成和馬烽都身不由己地處于兩大板塊的激烈沖撞之中,開始是周揚(yáng)、丁玲兩大板塊;周揚(yáng)、丁玲身后,又演變?yōu)閺埞饽辍①R敬之兩大板塊。”②124頁
需要引起我們關(guān)注的是,這樣的一種板塊沖突,不僅直接影響到了唐達(dá)成、馬烽的命運(yùn)沉浮,而且也還波及到了與此無關(guān)的其他人。山西作家田東照,就是一個(gè)典型的例子。田東照迄今最有影響的一部小說,就是中篇小說《黃河在這里轉(zhuǎn)了個(gè)彎》。這部小說創(chuàng)作于1980年代中期,時(shí)值丁玲主編的《中國》創(chuàng)刊伊始。丁玲要馬烽向她推薦好稿子,馬烽就把田東照的小說推薦給了丁玲,小說最后發(fā)表在《中國》1985年的第2期。然而,小說發(fā)表之后卻沒有能夠產(chǎn)生應(yīng)有的反響。請(qǐng)看陳為人轉(zhuǎn)述的周良沛關(guān)于此事的敘述:“無怪山西作家田東照的中篇《黃河在這里轉(zhuǎn)了個(gè)彎》發(fā)表后沒有獲得大家原先預(yù)期得到的反應(yīng)時(shí),編輯部的同志們都百思不得其解。作者以其深厚的生活底子,冷峻的筆觸,對(duì)貧困山村的寫實(shí),讀得人是心驚肉跳的。在評(píng)論家當(dāng)時(shí)評(píng)薦的作品中,它不一定在它們之上,也決不在它們之下。評(píng)論家可以不認(rèn)同丁玲對(duì)文學(xué)傾向性的看法,總該為作品力透紙背所描繪的人生畫圖所動(dòng)吧。此時(shí)此地,這種文學(xué)現(xiàn)象,也只能從非文學(xué)的角度去看了。無怪丁玲說:‘它要不是發(fā)在我編的《中國》上,早就會(huì)有人出來叫好,給獎(jiǎng)了。我們把它約了來,反把人家埋沒了。真是罪過啊!”②130頁雖然以上的引述似乎有一面之詞的嫌疑,但田東照這部其實(shí)還算優(yōu)秀的中篇小說,在當(dāng)時(shí),既沒有獲得評(píng)論家的相應(yīng)好評(píng),也沒有能夠獲得什么獎(jiǎng)項(xiàng),卻是客觀存在的一種事實(shí)。假若果真如此,那么,中國文壇的宗派關(guān)系之對(duì)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形成的負(fù)面影響,也就實(shí)在是相當(dāng)嚴(yán)重了。
必須看到,時(shí)間一長,這種宗派觀念甚至?xí)饾u地滲透到作家評(píng)論家的精神深處,會(huì)嚴(yán)重地影響到作家們看待思考問題的基本思維方式。在這一方面,馬烽自己就是一個(gè)典型的例證。請(qǐng)看陳為人在進(jìn)行采訪時(shí),馬烽對(duì)于中國作協(xié)“四大”的一種基本評(píng)價(jià):“他(指張光年)就和新起來的混成一伙子了。所以,我就候選人也不是了,原來是候選人。就是因?yàn)樗@次第四次作代會(huì)派性搞得太明顯了,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把原來的副主席保留,只進(jìn)不出,當(dāng)時(shí)他下面那些人,劉賓雁、張賢亮、王蒙活動(dòng)能量也大呢,最后三個(gè)原副主席落選了。賀敬之、劉白羽、歐陽山。三個(gè)老作家,三十年代的作家,在后來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解放區(qū)都是有貢獻(xiàn)的人才能到這個(gè)位置。”②164頁自己原來是候選人,結(jié)果后來又被取消了候選人的資格。想來,馬烽肚子里是比較窩火的。惟其如此,所以他才會(huì)以這樣一種不屑的否定性的語式來談?wù)撝袊鲄f(xié)“四大”。那么,到底應(yīng)該如何看待中國作協(xié)“四大”?如何理解一些老作家的落選,一些新進(jìn)作家的當(dāng)選呢?盡管不同立場(chǎng)的作家肯定會(huì)對(duì)此有不同的認(rèn)識(shí)和評(píng)價(jià),但在我看來,對(duì)于馬烽的看法,我們應(yīng)該取一分為二的方式來加以理解。一方面,由于中國文壇的宗派關(guān)系已然存在了很長一個(gè)時(shí)期,所以,中國作協(xié)“四大”的人事變化,肯定會(huì)受到宗派觀念的困擾影響,這是十分正常的一件事情。但在另一個(gè)方面,我們恐怕也得承認(rèn),從整體上看,中國作協(xié)“四大”仍然應(yīng)該被看作是一次相對(duì)成功的大會(huì)。尤其是其中的人事變化問題,按照馬烽的敘述,劉賓雁、王蒙他們之所以能夠當(dāng)選為副主席,是因?yàn)樗麄兓顒?dòng)能量很大的緣故。這樣一種看法的偏頗之處,是十分明顯的。如果尊重歷史事實(shí),那么,我們就必須看到,到1984年中國作協(xié)“四大”召開的時(shí)候,劉賓雁、王蒙他們這一代右派作家已經(jīng)取得了足夠大的文學(xué)實(shí)績(jī)。與這些右派作家相比較,賀敬之、劉白羽、歐陽山他們這些老作家的創(chuàng)作成績(jī)就明顯地相形見絀了。從這個(gè)角度來看,中國作協(xié)“四大”的選舉結(jié)果,在不排除宗派觀念影響的同時(shí),也應(yīng)該被看作是與會(huì)代表意志的正常反映,并不能簡(jiǎn)單地看作是劉賓雁、王蒙他們私下活動(dòng)拉票的結(jié)果。由此可見,盡管說馬烽自己多年來置身于中國文壇兩大板塊之間,可謂飽嘗了宗派關(guān)系之苦,然而,或許也正是因?yàn)殚L期置身于這種宗派關(guān)系之中的緣故,馬烽自己也自覺不自覺地受到了此種宗派觀念的制約和影響,也自覺不自覺地沿用宗派的思維方式來理解看待文壇人物文學(xué)現(xiàn)象了。endprint
在這里,需要對(duì)于傳主馬烽略作分析。陳為人以“馬烽無刺”來為自己的這本傳記命名,是極為恰當(dāng)?shù)囊患虑椋臀覀€(gè)人的理解,所謂“馬烽無刺”,最起碼具有以下兩個(gè)方面的意思。其一,是指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基本的文學(xué)觀念方面,馬烽他們這一批“山藥蛋派”作家,或者按照作家周宗奇的說法是“《講話》派”作家,所長期堅(jiān)持的都是一種積極配合當(dāng)下政治的創(chuàng)作方式,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批判性明顯不足或者基本沒有這樣一種突出的創(chuàng)作特征。其二,則是指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馬烽秉承打小就漸漸養(yǎng)成的與人為善的基本原則,從無害人之心。這一點(diǎn),既表現(xiàn)在他和李束為的關(guān)系中,更表現(xiàn)在他1989年之后擔(dān)任中國作協(xié)黨組書記之后的工作作風(fēng)上。從陳為人的敘述可知,在李束為與馬烽之間的宗派沖突中,主動(dòng)作梗者一直是李束為,馬烽更多地是在采取必要的守勢(sh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1989年,馬烽作為中國作協(xié)的黨組書記,作為大權(quán)在握的中國文壇的掌門人,在處理歷史遺留問題時(shí)所采取的那樣一種盡可能不處分傷害同志,力盡所能地與人為善的工作作風(fēng)。所有這一切,都極其有力地說明著,馬烽確實(shí)“無刺”。但就是如此一位秉性特別善良的馬烽,由于長期浸染在中國文壇復(fù)雜宗派關(guān)系之中的緣故,也不由自主地形成了按照宗派觀念、帶著有色眼鏡看人的思維習(xí)慣。宗派觀念之流毒遺害之深,于此即可見一斑。
論述至此,一個(gè)關(guān)鍵的問題自然也就浮出水面了。那就是,在中國文壇持續(xù)日久一些影響巨大的宗派關(guān)系究竟是怎樣形成的?是什么樣的社會(huì)文化機(jī)制導(dǎo)致了此種惡劣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說起來,中國文壇的所謂宗派關(guān)系,最遠(yuǎn)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的左聯(lián)時(shí)期。之所以在左聯(lián)時(shí)期開始形成宗派關(guān)系,關(guān)鍵原因與左聯(lián)的組織性質(zhì)有關(guān)。在左聯(lián)之前,雖然也有許多文學(xué)社團(tuán)紛紛涌現(xiàn),但這些文學(xué)社團(tuán)的性質(zhì)都是純文學(xué)的。這也就是說,諸如文學(xué)研究會(huì)、創(chuàng)造社這樣的文學(xué)社團(tuán),并沒有文學(xué)之外的政治勢(shì)力介入其中。某種意義上,左聯(lián)可以說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第一個(gè)帶有鮮明政治色彩的文學(xué)組織。由于有政治勢(shì)力的介入,所以在組織管理上,也就沿用了政治組織的管理模式。一沿用政治組織所謂管理模式,伴隨著權(quán)力的成熟,到底是誰說了才算的問題也就來了。有了權(quán)力的滲透,自然就有了圍繞權(quán)力產(chǎn)生的權(quán)力之爭(zhēng),有了不同的利益集團(tuán)。左聯(lián)時(shí)期之所以會(huì)爆發(fā)規(guī)模極大的“兩個(gè)口號(hào)”的論爭(zhēng),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然后,就是延安時(shí)期,即1949年之后,伴隨著政治勢(shì)力對(duì)于文學(xué)領(lǐng)域更加深入的滲透介入,宗派關(guān)系不僅越來越復(fù)雜,而且也越來越緊張激烈了。尤其是在1949年共和國成立之后,伴隨著中國文聯(lián)、中國作協(xié)這樣一類政治性極強(qiáng)的文學(xué)界組織的形成,由于文學(xué)界的權(quán)力越來越大,因此,原先就已經(jīng)存在的宗派關(guān)系就愈益變本加厲了。陳為人在書中描述的周揚(yáng)、丁玲兩大板塊,張光年、賀敬之兩大板塊,均可以在這樣的意義層面上獲得理解。歸根到底,這所謂的宗派關(guān)系,還是因?yàn)橹袊嬖谥粋€(gè)文壇的緣故。某種意義上說,所謂的中國文壇,也是一種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特殊事物。放眼全球,大約只有我們中國才有這樣的一種文壇存在。別的國家,只有作家,而沒有文壇。即使有所謂的作家組織,大約也都類似于五四時(shí)期的文學(xué)研究會(huì)、創(chuàng)造社。只有在我們這樣的社會(huì)體制內(nèi),才會(huì)有政權(quán)對(duì)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深度介入。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有效地引導(dǎo)作家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活動(dòng)。有了權(quán)力的介入,就有了文壇的形成。既然形成了所謂的文壇,也就有了文壇權(quán)力的爭(zhēng)奪。圍繞中國文壇權(quán)力的爭(zhēng)奪,出現(xiàn)不同的山頭,形成不同的派系,最終導(dǎo)致宗派關(guān)系的生成,也就成為必然之事。之所以是周揚(yáng)、丁玲、張光年、賀敬之這樣的一些作家官員,而不是其他作家成為文壇不同宗派的代表性人物,也只不過是歷史過程的一種隨機(jī)選擇而已。生性善良的馬烽置身于其中所無法徹底擺脫的,實(shí)際上正是這樣一種盤根錯(cuò)節(jié)的宗派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在此,我們也不妨簡(jiǎn)單地設(shè)想一下,假若沒有這樣一種性質(zhì)的文壇存在,假若我們的作家可以不受文壇影響,全心全意專心致志地從事于文學(xué)事業(yè)的創(chuàng)造,那將會(huì)是一種何其理想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景觀啊!在這個(gè)層面上,即使把中國文壇的宗派關(guān)系稱之為嚴(yán)重影響毒害文學(xué)創(chuàng)作發(fā)展的一種極其可怕的毒瘤,也還是很有一些道理的。
最后想提出的一個(gè)問題是,既然中國文壇的宗派關(guān)系實(shí)際上已經(jīng)存在了很多年,但卻為什么只有陳為人才意識(shí)到這一問題的嚴(yán)重性,并對(duì)之做出了深入的梳理反思呢?我想,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gè)原因,恐怕就在于陳為人不僅對(duì)于中國文壇有著格外深切的了解體會(huì),而且身為持有自由主義思想價(jià)值立場(chǎng)的知識(shí)分子的緣故。其實(shí),從根本上說,陳為人的反思對(duì)象,也并不僅僅是中國文壇,不僅是困擾中國文壇很多年的宗派關(guān)系問題。借助于對(duì)中國文壇宗派關(guān)系問題的梳理與分析,把自己的批判反思矛頭對(duì)準(zhǔn)潛藏在這些問題背后的社會(huì)文化體制,才應(yīng)該被看作是陳為人這部《馬烽無刺》真正的思想價(jià)值所在。
注釋:
①陳為人:《唐達(dá)成文壇風(fēng)雨五十年》,美國: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
②陳為人:《馬烽無刺》,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年10月版,第84頁。本文的引文全部來自于這部著作,以后只標(biāo)明頁數(shù),不再特別注明。
③陳為人:《插錯(cuò)了“搭子”的一張牌——重新解讀趙樹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版。
(作者單位:山西大學(xué)文學(xué)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