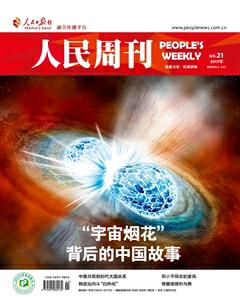《四庫全書》里的洋人書
寶樹
《四庫全書》是中國古書的集大成之作。但少為人知的是,其中也收入了幾部洋人的書,都是明清之際的傳教士帶來或撰寫的。紀昀等四庫館臣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介紹,生動反映出清朝中葉的文化精英對已傳入中國一兩百年的西學的態度,今天讀來頗為有趣。
最受好評的是一部古希臘名著: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明末徐光啟譯,收入子部天文算術類。四庫館臣稱“其于三角、方圓、邊、線、面積、體積比例變化相生之義,無不曲折盡顯,纖微畢露”“自始至終,毫無疵類”,評價不可謂之不高。這多半是因為當年康熙帝對幾何學的喜愛,康熙帝還“御定”了一部試圖融合中西方數學的《數理精蘊》,也收入《四庫全書》中,其中相當一部分內容就來自《幾何原本》,紀曉嵐們自然要給點面子。不過四庫館臣從來沒搞清楚過歐幾里得是何許人也,對于《數理精蘊》的評價也遠遠高于《幾何原本》,說是“從古未有之書。雖專門名家,未能窺高深于萬一也”。按此說來,《幾何原本》有幸對《數理精蘊》有所貢獻,就算是完成了使命。
比起《幾何原本》,其他一些西學著作就沒那么好的運氣。利瑪竇等人撰寫的關于天主教的神學和哲學書籍,如《天主實義》《畸人十篇》等都被扔進了子部雜家類的“存目”,也就是說沒有資格納入《四庫全書》。四庫館臣認為,天主教主要教義是剽竊佛教的,無甚可取,但其實也隱約明白西學和佛教不是一碼事,又說“歐羅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實逾前古;其議論夸詐迂怪,亦為異端之尤。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也就是說,一般人容易被歐洲人發達的科學技術知識所吸引而去學習他們的異端學術,任其傳播必然是心腹大患。
四庫館臣對西學中地理書籍的態度最可玩味。這些書既不像思想類書籍那樣明顯是“異端”,但又不如《幾何原本》那么單純。比如艾儒略的《職方外紀》被收入史部地理類。《提要》中簡要傳達了該書的主要內容:地球上有五大洲,如“亞細亞洲”“歐羅巴洲”“亞墨利加”(美洲)等,不僅有其大致的經緯度,甚至還知道美洲“地分南北,中通一峽”,然而四庫館臣最后話鋒一轉,說本書“所述多奇異不可究詰,似不免多所夸飾。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錄而存之,亦足以廣異聞也”。
另有南懷仁的《坤輿圖說》,其中記載各大洲的地理物產,有些奇特的事物,比如羅德島的太陽神巨像、北極的睡鼠等等,四庫館臣都不予置信,還從《神異經》《癸辛雜識》等冷門古書中尋找依據,說是從中國古書中抄來的。但最后還是寬容地說:“蓋雖有所粉飾,而不盡虛構。存廣異聞,固亦無不可也。”一并收入《四庫全書》。
對當時的中國知識界來說,最可怕的并不是排斥異端的心態——這一點當時的西方人也有,反而是某種和稀泥式的“兼容并包”。大地是球體,分為五大洲等先進的知識,刻進了《四庫全書》,這部書可不是深藏宮廷秘而不宣,而是讀書人都能申請閱覽的。但此后直到鴉片戰爭的七八十年里并沒有任何作用。為什么?因為這些知識不過是“存廣異聞”。只是一種有趣的談資,和《閱微草堂筆記》的談鬼說狐也差不多。
要搞明白洋人說的五洲列國是真是假,非常簡單,派幾個使者跟他們出洋去看看就知道了。不過當時從皇帝到士人都對此毫無興趣。左右不過是些談資,真假又有什么重要呢?在時人看來,《四庫全書》已經是浩如煙海的知識體系,乾嘉學術的求真也僅限于細節的校讎考據,對了解世界本身喪失了熱情,這種深深的麻木才是最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