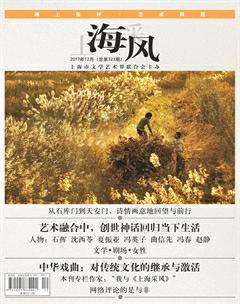中國影壇奇才
盛漢清
1998年5月18日,我國新華社《每日電訊》發表整版文章,題為《文化大師素描》,重點介紹了巴金、賀綠汀、王元化、謝晉、杜宣和夏振亞等六位文化大師,其中這個末尾的夏振亞原來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科教電影導演,一下子進入名人之列,可見其聲譽之隆,地位之高。隨后,中央電視臺以《中國影壇奇才——夏振亞》為題,全面介紹了這位集電影、文學、書畫“三絕”于一身的“三棲藝術家”,更是引起廣大觀眾的注意。一個不易為人們所矚目的電影片種,培育出了一位享譽國內外的杰出人物,以他輝煌的藝術成就,向人們展示了中國科教電影躋身世界的雄厚實力,也證明了他對發展我國科教電影事業所做的杰出貢獻。
國家一級導演夏振亞,從影五十年來,他編導的科教片和紀錄片始終稱雄八方,曾先后八次獲得國際科教電影節獎,兩次獲國際金獎,一次獲國際大獎,十次獲文化部優秀影片獎、中國電影華表獎和其他國家級獎,一次獲中國電影“金雞獎”,四次獲“金雞獎”提名。他被國務院授予“有突出貢獻的電影藝術家”稱號,他是“上海首屆大眾科學獎”得主,被上海市科技協會授予“上海優秀科普作家”頭銜,他的成就被收入多種中外名人詞典。
從泥濘的鄉間小路走來
夏振亞出生于江蘇阜寧一個富豪家里,但還未等到他長大,家庭開始破落,變得一貧如洗,飯都吃不上,窮得叮當響。小時候的苦難,嚴厲的家訓,促使夏振亞堅強奮發,從兒童時代起,爭強好勝就逐漸成為他生命長河中極為突出的個性。
時光定格在1959年,夏振亞高中畢業,二十多年沒有離開過家鄉的串場河,滿懷激情和夢想的他,從泥濘的鄉間小路走來,沿著大運河南下,一步三回頭地走著,第一次看到波濤壯闊的長江,深切感受到了“天塹”兩字的真諦,趕到省城南京報考萬人簇擁的上海電影專科學校攝影系,只收二十個新生,難度極大。在這之前,他連照相機都沒有摸過,難怪親戚譏笑他考影校是“坐地摸天”。可豪氣不減當年的老父激勵他:“憑你的天賦,赴考場一決雌雄,爭取榜上有名不是沒有可能的!”
夏振亞一腳跨進既讓人向往又令人生畏的考場大門,打開試卷一看,是分析電影《鳳凰之歌》。挑戰催發思考,自信醞釀沉著,這不就是像平時寫的一篇作文題嗎?于是他思如潮涌,洋洋灑灑說起了影片的主題結構人物,鏡頭場景氣氛,還斗膽地筆鋒一轉,列舉《鳳凰之歌》攝影藝術的缺陷。他當時不知道面對的主考官,不是別人,恰恰是該片的著名攝影師,即將赴任的電影學校攝影系主任馮四知,這等于是“太歲頭上動土啊”!但夏振亞沉住氣,過五關,斬六將,一直到從容面對口試,解讀俄羅斯畫家列賓的經典作品《伏爾加河上的纖夫》:好,這一根纖繩上的十一個纖夫,神態各異,唯有黑壓壓隊伍中那個紅衣少年,充滿期盼的神色,抬頭凝視著遼闊的蒼茫大地。夏振亞感到和紅衣少年的眼神,有一種無可名狀的心靈感應和呼應……他這股與生俱來的勇氣和超乎尋常的獨到見解,贏得了專家們的好感,使夏振亞在萬里挑一的考生中榜上有名,幸運地被錄取了。
在令人羨慕的上海電影專科學校,夏振亞三年寒窗,刻苦學習,作業用功,讀書萬卷,觀片無數,一心向往去故事片廠大顯身手,創家立業。可壓根兒沒有想到,卻被分配到上海科學教育電影制片廠工作。學藝術的去搞科教片,自己的才情豈不“干枯”發黃,學無用武之地?人們通常認為科學只是理論,藝術才是抒情,兩者似乎不可統一。夏振亞心想,自己既然進了科影廠,要么不干,真要干,一定要干出名堂,闖出一番新的天地。
成功的秘訣在于不斷越界、反叛
進廠頭幾年,夏振亞到攝制組勞動實習,邊學邊干,積累經驗。身在科影廠,自然對科學發生了興趣,滲透了他的愛,這一點非常難能可貴,實現了從愛藝術轉而到愛科學的一次飛躍。 在職務上,夏振亞進行了一次“越界”,從攝影改當導演。與眾不同的是,他一開始著手創作科教片時,就把科學與藝術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他真情地說:“我愛藝術,我愛大自然,我忍不住把深深的感情寄托于科教片中那些光和影,寄托于無盡的知識海洋。科學和藝術在銀幕上不僅可以親密牽手,而且可以熱情擁抱和結合。于是,比興、象征、抒情、靈動,我將抽象的科學知識化為感染情緒的視聽形象,就連‘人造卵也都拍成了詩意的《搖籃》……理智加情感,突破與創新,成為我作品的藝術生命的所在。”
但夏振亞這種觀點,犯了科教片的“大忌”,因為,科教片過去的一貫準則是“純客觀”敘述,絕對不能夾雜個人的“主觀感受”!夏振亞卻反其道而行之,成了另類中的“另類”,他的每一次“越界”行動是一種“反叛”,其實是求之不得的創新!在他編導的科教片《膽結石的奧秘》中,有一段形容各種結石的解說詞:“嗬,這種像透明的瑪瑙,又像閃光的寶石,難道也是從人體膽囊里取出來的嗎?”在審查時有人反對,認為這段解說,缺乏嚴肅的科學性,非改不可。夏振亞據理力爭,堅持己見,非但不改,還進一步把文學性、藝術性、趣味性融全片于一體。他認為“科教電影是科學與藝術的結合,藝術語言最忌的是索然寡味”。在拍攝科教片《冠心病》時,夏振亞自加壓力,把這部影片定位于超越世界先進水平,非要拍到活生生的全離體心臟跳動。先用豬的心臟來拍攝,但一離體,心臟就亂跳甚至跳停了,前后試了三次。而實驗過的豬,由于打了麻醉藥,不能食用。有一些人開始嚷嚷:“眼看上千斤豬肉白白浪費掉,真是勞命傷財。”“人家日本也沒拍到完全離體的心臟跳動,改用動畫來表現心跳吧。”在這關鍵時刻,導演的決心和魄力最重要,夏振亞沒有退縮,堅持科教片求真求新的必要性,進一步與醫學專家分析研究,找出失敗原因不是拍攝方法,而是豬的心臟不夠強壯,假如換用狼狗心臟,成功率會提高。正好有人提供線索,上海醫科大學有一條用作醫學實驗的大狼狗,如果要殺掉,非得經過校長特批。那就請示校長石美鑫,恰巧他是影片的科學顧問之一,完全明白這個全離體心臟鏡頭對整部影片的重要價值,他稍作考慮,提筆就批準。后來,完成片的開頭是:在夜幕下,遠遠的一個紅點在搏動,它由遠變近,越來越大,伴隨“撲通,撲通”的聲音,由弱變強,越來越響。呵,一顆全離體跳動的心臟,好像從神秘宇宙空間的深處向你走來,這紀實、直觀、令人信服的心跳,這象征健康生命、象征青春激情、象征純真愛情的心跳,給觀眾以極大的審美愉悅。《冠心病》影片一舉獲得了意大利第二屆巴馬國際科教電影節的金質獎,達到了夏振亞此片超越世界先進水平的預期目標。endprint
編導《花》和《葉子》兩部生物科教片,夏振亞傾注了極大的精力和感情,以“科學散文”的樣式,把科學和藝術通過電影手段十分完美地結合起來。請聽《花》的解說詞:“花開花落知多少,但落花并非無情物,在花的生命旅程中,落花之時,正是結果之日,它會留下種子,再度繁殖萌發出新的生命……今天,花已成為人類和平的使者,一切美好和幸福的化身,人類的明天將是如何?花又該是怎樣呢……”邊聽邊想,給人以創造思索的空間,讓觀眾對今天與未來展開想象的羽翼,在銀幕內外,盡情地翱翔。《葉子》與《花》有異曲同工之妙,開頭煽情訴說:“秋天到了,落葉飄零,面對這樣一幅圖景,或許會給人一種冷落蕭瑟之感吧。不過你有沒有注意到,在葉子的生命旅程中,曾充滿蓬勃生機,為我們作出過生命的奉獻……令人遐思漫想……”尾聲中又發出深情贊嘆:“秋風吹起今又是,即便是無邊落木蕭蕭下,也總是落葉歸根。它肥沃了大地,催育了種子的萌動,喚起了大地的蘇醒,帶來了春天的氣息,孕育了又一個豐收的希望……”著名劇作家蘇叔陽評論說,夏振亞是“一位用攝影機和電影藝術語言講科學的作家”,“具有作家電影的品位”,上海電影界的一位同行稱贊道:“夏振亞的作品,不僅內容新,而且形式新。是他第一個在中國銀幕上記錄了全離體心臟跳動的鏡頭;是他第一個將鏡頭伸入到人體內部盡情周游;是他第一個用高倍顯微鏡攝下了比頭發絲還細的昆蟲產卵鏡頭;是他第一個在顯微攝影領域展開推拉搖移全方位深入表現……”我國科教片創始人之一、科影廠第一任廠長洪林同志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談到夏振亞同志的創作特色,他是一個不甘平庸的人。他拍影片,寫文章,以及他的講話,都有一種‘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激情。科教片中一些科學道理,本來是理性的,有的還是深奧的,可是在他的影片中,都能拍得有聲有色,令人感動。看他的影片,不會讓人有枯燥、沉悶、乏味之感。這說明他有一種刻意求精的創作態度,也有著深厚扎實的藝術功底。我曾多次對人贊嘆:好一篇科學散文!”
的確,夏振亞的創作,正是從觀眾的興奮點入手,待觀眾興味盎然時,才一步步引入科學本身的規律之門,引人探幽尋秘,在好奇心中去求新知;把科學的深化與藝術的造化有機地融化、強化,化為一體,而不是淡化,更不是“分化”和“異化”;向人們奉獻一種獨特的美,給人有智有趣有情有意的享受。為了達到這樣的高度,夏振亞有自己的創作準則,他認為,揭示科學原理只是科教片的“最低綱領”,傳遞科學之美,讓觀眾熱愛科學,才是科教片的“最高綱領”。
除了創作準則,夏振亞還有一套創作理念和創作規范。一是“雜交”之說,他認為任何一門藝術都是“雜種”,科教電影也不例外,在藝術上要善于“雜交”,糅百家之長,為“我”所用,融于一體。二是“三不”原則:不重復歷史,不重復他人,不重復自己。三是“三格”規定:創作原則要嚴守“規格”,藝術表現要勇于“破格”,努力創出新的“風格”。看來,這就是夏振亞成功的秘訣所在的一個方面,他既能不斷越界、反叛,又會自覺套上鎖鏈跳舞,只有這樣,才能在藝術道路上不斷創新,永攀高峰。
文學和一切藝術都是相通的
勤奮出天才,不用說,夏振亞從求學到工作,一直是勤奮刻苦,問心無愧,晚上12點以前從不上床入睡。這種熬夜的本領,早在孩提時代就練就了。生活的艱辛,家境的貧困,曾經把童年求知若渴的夏振亞一度拒之于學校門外。后來,好不容易再走進課堂,也就特別珍惜寶貴的時間,最喜歡夜晚。農村的夜晚更有寧靜的氛圍,在一支蠟燭或一盞油燈下,徹夜攻讀,很有一種懸梁刺股的仁人志士、奮發圖強的猛勁。夏振亞自幼酷愛文學,在他的家鄉溝墩,連牧童都喜歡在牛背上讀唐詩,深受熏陶,好學成風。他博覽古今中外名著,尤其是祖國的優秀文學經典。要知道這里是誕生施耐庵《水滸傳》、吳承恩《西游記》、李汝珍《鏡花緣》、劉鶚《老殘游記》的故鄉,文學名著像乳汁、如甘泉般地融進了他的心田,強烈地撥動著他心靈深處的情感之弦。他曾經為書中不少悲劇人物的坎坷命運傷感,也會夢幻像李白、杜甫那樣浪游于祖國壯麗的山川秀水之中。
那年頭,北方“神童”作家劉紹棠13歲寫小說、15歲成名的奇跡傳遍家鄉的四面八方,校園的每個角落。他的成名作《青枝綠葉》編進了中學教材,他寫大運河,把雄健遒勁與牧歌柔情結合得那么生動美妙。夏振亞感到與自己的處境、情境、心境相當契合,魂牽夢縈,做起了一個個萬花筒似的文學夢。上中學時,全校每次作文比賽,夏振亞總是名列前茅,文才初顯。于是,在詩情畫意的鄉土文學鞭策和影響下,中學尚未畢業,夏振亞利用課余時間,寫散文,作詩歌,寫小小說,向報刊、雜志投稿,其中他寫的《不夜的串場河畔》等十多篇充滿鄉土氣息的散文,發表在《新華日報》等省級媒體上,被出版社選入集子中。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時代更醉心于文學,捧出了對新生活熱愛的稚子之心,自己的藝術才華閃爍出希冀的光芒,也奠定了他日后躍馬揚鞭的文學基礎和功底。
從事科教片導演工作后,夏振亞更是廣種薄收,才思洋溢,接觸各種文藝形式,并喜歡用文學的眼光,竭力捕捉萬物之神韻,碰撞出藝術之浪花,拍片之余,筆耕不止,深得有關編輯部門的青睞,以專欄作家的身份為報紙撰寫過四百多篇雜文。這中間,他結識了著名書畫篆刻家韓天衡,兩人一見如故,意相合,志相投,切磋琢磨,合作寫稿、著書。無巧不成書,當夏振亞籌備拍攝《畫苑掇英》時,正巧韓天衡被調到上海中國畫院專業畫畫。夏振亞可是求之不得,機不可失,自然請“老搭檔”合作,一起編寫《畫苑掇英》劇本,使未來影片打下一個堅實的文學基礎。后來,影片將17位大畫家各自不同的風格、特點都得到了恰如其分、畫龍點睛般的刻畫與強化,如劉海粟“落筆如翻揚子江”的潑墨,潑彩,膽魄過人的氣概;謝稚柳“用筆如龍飛鳳舞的功力,獨到的古典主義畫風”;朱屺瞻“揮筆橫掃豎抹”的雄視千古的精神力量;陸儼少把“千里峽江險情”濃縮于咫尺之間的絕妙;程十發的“一點一抹”;唐云的“誤筆成鳥”;應野平的“墨分五色”;關良的“點睛之筆”;劉旦宅的“傳神美女”;沈邁士的指畫“手如斗筆”;陳佩秋的“兼工帶寫”;林曦明“惜墨如金”的浩渺意境等等,都被一五一十、錯落有致地突顯在電影銀幕上,構成了一幅幅絢麗多姿、名揚四海的藝術畫廊。endprint
喝串場河水的故鄉人,特別愛說故事,也愛聽故事。小時候,夏振亞耳濡目染了多種多樣關于唐伯虎的故事。盡管版本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十個”唐伯虎有“十個”帶“色”字,見女人就“獻媚”,看美女必“盯梢”的風流人物。事實果真如此嗎?那年,夏振亞出差來到唐伯虎的故鄉蘇州,時間較長,他抽空對唐伯虎的人生密碼作一次探究與破譯,查閱《蘇州地方志》和相關文獻資料,每晚閱讀摘抄,常常通宵達旦……他終于發現,人們心目中的唐伯虎與歷史真實的唐伯虎嚴重錯位,決定為唐伯虎翻案,還其歷史真面目。
數月之后,夏振亞精心撰寫的電影文學劇本《唐伯虎》完成,塑造了一個真實可信,不附權奸的江南才子形象。消息傳到上海越劇院,越劇表演藝術家袁雪芬親自派人登門八次,邀請夏振亞將《唐伯虎》改編成越劇,只因忙于拍攝科教片,夏振亞婉言謝絕了袁雪芬的一片好意。香港電影界也有人獲悉此事,上門游說,夏振亞怕被“戲說”甚至糟蹋唐伯虎,主意已定,出價千金也不賣“虎”。最后,他編劇的《唐伯虎》僅出版了連環畫,與讀者見了面,新書一上架,讀者爭購一空,夏振亞平淡而謙虛地說:“這倒不是我寫得好,因為人們都想看到一個真實的唐伯虎。”
做夢也沒有想到“破門入畫”
有人問夏振亞:你是幾歲開始學畫的?他實話相告:“我第一次作畫,已過不惑之年。那是在紹興拍攝影片《畫苑掇英》外景,接連細雨綿綿,大家只好足不出戶,躲在賓館里看書作畫……”他清楚記得,就在那天下午,走進畫家林曦明房間,幾位大師唐云、陸儼少、吳青霞等都聚在這里,一邊品茶,一邊作畫。林曦明見夏振亞進來,就拉住他:“來來來,我剛才正在畫畫,你也畫幾筆!”夏振亞連忙謝絕:“老林,你的玩笑開大了,我從未畫過,這怎么行?”“不要客氣,斯文人總會涂兩筆的!”不由分說,林曦明把一枝毛筆硬是塞到夏的手里。環顧四周,望著夏振亞的都是名家大師一雙雙鼓勵而期盼的眼睛,畫也不好,不畫也難。問題在于:夏振亞還是念小學時在圖畫課上涂鴉過,那是每個孩子都能做到的。幾十年過去,突然要他畫畫,還真的犯了難。可盛情難卻,只好硬著頭皮干。那么,畫什么呢?前幾天選外景,紹興四周淡淡的山,清清的河,蔥蔥的樹,還有那烏篷船頭戴氈帽、銜煙斗的漁翁……給夏正亞留下深深的印象,此情此景此刻,在他腦海一一浮現,撲面而來,就畫這個吧。他懷著崇敬、學習的態度,“班門弄斧”,大膽下筆,一會兒,畫稿出籠,覺得還缺幾口氣,想再補幾筆,又不知從何著手。這時,陸儼少叫到:“別動,別動,我來加幾筆!”于是,遠山近樹有了延伸。林曦明呼應:“來來來,我也加幾筆!”他補寫一葉輕舟,與夏畫的烏篷船相配。眾畫家齊聲說:“落款、落款……”畫家老林自告奮勇落了款:“振亞同志作江南水鄉圖,儼少先生補遠山近樹,曦明填寫小舟并題,時在甲子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四日于紹興賓館之南樓”。夏振亞的處女作就這樣“破門入畫”,竟然是與大畫家一起動筆“合成”的。
多少年過去了,這幅純真的“處女作”一直陪伴著夏振亞,他常琢磨,甚至百思不得其解,怎么會第一次就“破門入畫”?是因為意象早已孕育,“十月懷胎”,只待“一朝分娩”?是因為他自幼苦練書法,“書畫同源”?是因為當導演,藝術本來就相通?還是終日在畫師中間受到熏陶、浸潤,“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其實,這些綜合元素和基因糅合起來,相互影響,也就塑造了一個自學畫畫的夏振亞。
從那以后,夏振亞拍電影忙得再累,每當更深夜靜,堅持作畫,雷打不動。他鐘情水墨大寫意,大的整幅宣紙,大的斗筆,畫大山大水。用畫家唐云的話說:“膽子大,氣度大,手筆大。”那時,夏振亞還沒有大畫桌,只好蹲在地板上攤開宣紙作畫……他畫得人發“瘋”——不管春夏秋冬,一筆在手,神游其中,廢寢忘食,那是他情懷的釋放;他畫得筆發“狂”——因為他沒有得與失的包袱,只有盡情表述的欲望;沒有理性,只有感性;沒有“條條框框”,只有“無法無天”。一旦畫興大作,抄起畫筆,線條游動,水墨涌潮,濃與淡、疏與密、干與濕、融合與擴散、交融與交錯,頓時在畫幅上變幻莫測。然后,他因勢利導,隨機應變,細心收拾,遙想妙得地描摹出稍瞬即逝的千變萬化的“生象”。夏振亞坦言道:“我的水墨之功不是筆底下的流淌,而是凝聚情感于毫端的噴薄。所以,只有到最后才知道也是我企盼得到的一種特殊的藝術效果。”
真的,他毫無顧忌,什么都敢畫。畫名山大川,也畫煙雨江南;畫漁翁寒江獨釣,也畫少女青春夢幻;畫落霞孤雁晚歸,也畫灘涂白鶴雙飛。總之,山水、人物、花鳥都畫,但最喜歡畫的還是秋風中的“蘆葦”,銀塘里的“魚兒”。因為它們對夏振亞來說,既有迷人的喜悅,也有惆悵的傷感,曾記錄他襁褓時的劫難,艱苦童年和激情燃燒的歲歲月月。“蘆葦”吹響的“蘆笛”是他心中的音符;“魚兒”潑起碧波猶如山澗清泉,載著人生往事一次又一次浪奔,那是流過他心底的歌……有時,在夏振亞幾十幅的作品中,全部是《蘆蕩圖》——各種氣氛、各種景象:晨曦與黃昏,春綠與秋黃,夏茂與冬枯,晴空萬里與風雨交加,一曲漁歌一行雁,一叢蘆葦一片情,訴說他心中的夢。夏振亞在畫幅上題字,也總離不開一個“蘆”字,那就像蘆歌優美旋律中的點睛之詞:“年年只有南來雁,常帶秋聲入蘆叢”“十月天青大雁歸,相呼相喚蘆花里”“數聲蘆笛漁歌晚,一叢蘆葉慰相思”“蘆葦秋風葉葉涼,何處漁郎晚笛吹”。就這樣,《蘆蕩畫》被許多富豪高價認購,《魚兒圖》讓無數名流拍賣收藏。畫家林曦明看了他的畫作,動情地說:“你呀,要是成不了畫家,老天爺也不睜眼了!”大師唐云為他“仙人指路”,語重心長地說:“你不要再去模仿這個那個的,你作畫已經找到了自己,你就大膽走自己的路吧!”
對夏振亞的畫,不能不提到他畫的魚,俗稱“夏氏魚”。畫時好像很簡單,幾乎一筆頭下來,再用線條勾勒而成。其最大的特點是,運筆屏氣,全神貫注,飽蘸濃墨,一氣呵成,墨汁欲滴,濕漉漉的,充滿水汽、才氣、大氣。關鍵還在于他每畫一條魚,都要畫出魚的“活力”和“神韻”,畫出“水中精靈”的獨特風采,這是旁人不易模仿的難點。很快,“夏氏魚”在圈內和外界贏得眾多的欣賞者,其中有蘇叔陽、鄧偉志、奚美娟這樣的文化界知名人士,也一度在上海“朵云軒”招搖過市,生意紅火,掛出一“條”,賣掉一“條”。當時一條“魚”可賣到三千元,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可是一個不小的數字呵!endprint
又一個想不到奇才碰到奇事
小時候,夏振亞在家鄉嚴父督促下苦練毛筆字,無論嚴冬酷暑,風雨交加,專心臨摹,夜以繼日,才練出一手好字,筆觸蒼勁有力,氣貫通暢如流,深得師長好評。后來參加電影工作,接觸的人層次較高,喜歡以書會友,交流書法心得,開始小有名氣,聲望遠揚,以至傳到了南京大學名譽校長、孔學專家匡亞明耳中:“振亞同志,你的書法很好,我早有所聞,能不能給我一幅?”上海著名骨科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陳中偉也十分喜歡夏振亞的字,甚至把導演與他聯系的工作字條,也一直壓在玻璃臺板下,說:“夏導書法很好,既留作紀念,又留作欣賞。”北京劇作家蘇叔陽則稱贊:“你的書法,我非常喜歡,豈止喜歡,簡直稱得上崇拜!”如此看來,夏振亞的書法,在社會上已有一定的口碑和影響,但還沒有發展到令人吃驚的地步。
直到有一天,北京廣電部發來一份加急電報:“夏振亞同志,請你速為《中國電影周報》題寫報頭,完成后特快專遞北京。”剛開始,夏振亞根本不相信,認為是“天方夜譚”似的開玩笑。后來親自接過電報,看了又看,才深信無疑。對此,夏振亞心態很平靜:“要我寫,我就寫,用不用,不是我的事,不用也無傷大雅。”寫好寄出,一個月過去了,杳無音訊。有人問:“題寫報頭,開始催得十萬火急,現在沒有了下文……”夏振亞并不把它當真,認為是“玩玩的”。誰知已忘得一干二凈之時,北京又飛來電報:“夏振亞同志,這次被邀請寫報頭的有諸多名家泰斗,如全國書法家協會、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央美術學院以及文化藝術界名流。經過專家評議和無記名投票,最后再經領導審定,認為你題寫的報頭蒼勁有力,瀟灑渾厚,好看耐看,決定采用了。特此祝賀!”
消息傳出,炸成了鍋。又一個想不到,奇才碰到了奇事。因為事后才了解,啟功、吳作人、范曾這樣的書畫界泰斗級人物也踴躍參與題寫報頭。不少人好奇地問夏振亞:“如果事先你知道有那么多權威人士也為報頭題字,你還敢不敢動筆?”“有什么不敢的?”“為什么?”夏振亞回答:“小時候我就養成了一個倔強的脾氣,對強者贊佩,但決不示弱。長大后,我走向成熟,對學術權威崇敬,但決不崇拜;崇敬讓人清醒,崇拜會陷入盲目和迷信,在現實與未來之間就會顯得困惑和無奈,缺少了科學精神與科學思想的價值取向。”但不管怎么說,夏振亞這次能力壓群雄,脫穎而出,一舉奪魁,難能可貴!
冬去春來,北京廣電部再次電報飛傳:“夏振亞同志,《中國電影周報》要改名《中國電影報》,根據上級領導的意見和大家的呼聲,仍然要你題寫報頭。”這時,夏振亞不像上一次那樣輕松灑脫了,有些私心雜念,“萬一落榜了,沒臉見人啦……”于是,他寫了一條又一條,寫得很沉重,很揪心,總共寫了二十多條,還是吃不準,最后在朋友和行家中間反復征求意見,挑出幾條,寄往北京。最后,他題寫的新報頭,又被采用了,喜出望外,激動萬分。
功夫不負有心人,向夏振亞要字的人越來越多。那天,杭州一個文化人登門拜訪夏振亞,說:“久仰你的書法,今天專程來上海,向你求個墨寶。但聽說你不賣,我也不好白拿,考慮再三,就用墨寶換墨寶吧。”說著,取出一幅裱好的作品,一展開——哎呀,是書法界泰斗沙孟海寫的對聯。夏振亞嚇了一跳,怎么可以拿沙孟海的大作來換我的字呢?“使不得,使不得。”夏振亞嚴肅地說:“快收回去,沙孟海是前輩,他的作品藝術價值我是望塵莫及!你的如此之舉,我不敢當,不敢當!”來者有點尷尬:“請夏導演原諒,我不是故意的……墨寶無價,當然無法交換。如有冒犯,那是對沙孟海的不敬,也是對你的不恭。”夏振亞打斷他的話:“也不能這樣相提并論呀。”“不,我的意思,只是想把沙孟海的這幅作品留在你身邊,作個紀念,別無其他。”見夏振亞生氣,對方換了個說法。“你喜歡我的書法,心又這么誠,字我肯定給你;沙孟海的墨寶,請你一定帶回!”末了,夏振亞把自己書寫的“云煙入畫,筆墨含情”的聯句送給杭州來客,可是,客人臨走時還是把沙孟海的作品執意留下。他是一番好意,而在夏振亞心中卻留下了巨大的壓力,鞭策他快馬加鞭,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想不到“狂人碰到狂人”
夏振亞在構思大型藝術片《畫苑掇英》時,便設想未來影片邀請十多個大師級國畫人物出場,其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蜚聲中外、氣吞山河的劉海粟。可萬萬沒想到,夏振亞專門拜訪劉海老,兩人第一次見面卻發生了“原則”分歧,激烈“爭執”,雙方互不“讓步”,一時出現了僵局……
劉海老:“聽說夏導你要搞一部電影,拍畫家?”夏振亞:“是的,《畫苑掇英》是拍中國當代健在的一流國畫家,盡快給歷史留一份畫壇的電影檔案。因為文化大革命已經耽誤了我們太多時間……”劉點頭:“文化大革命害得我家破人末亡。這次我去香港,有人勸我留在那里,可我還是回來啦!”夏進言:“現在拍電影資金緊缺,我直接給市領導寫信請示,政府已同意財政撥款。”劉再次點頭:“嗯,拍國畫電影,這是一件好事,我支持!你打算怎么拍?”“我構想,影片從實景開始,黃河之水天上來,然后將鏡頭驟然拉出,變成一副您的波濤洶涌的《黃河圖》……”劉欣然回應:“好啊,《黃河圖》,我畫得好啊……”接著,夏振亞簡略地向劉海老匯報今后影片打算要拍唐云、程十發、謝稚柳、朱屺瞻、陸儼少、王個簃……想不到,劉大師直搖頭,話鋒一轉:“我已經十次上黃山,現在我決定陪你,第十一次上黃山,但是影片中不可有甲、乙、丙、丁。”夏導演一聽,非常吃驚:“……請你相信我,我會在影片中充分表現你劉海老和你的作品。”劉仍然堅持:“不!你要是想拍我,影片就不能有甲、乙、丙、丁。”夏振亞心里想,86歲高齡的劉海老果然是個“藝術狂人”,對自己作品的自信和當仁不讓,當然可以理解,問題是不能排斥其他各位名家大師啊!夏振亞急中生智,又膽大包天地勸解劉大師:“《畫苑掇英》肯定要拍甲、乙、丙、丁。如果先生執意堅持,我倒怕今后影片完成了,一大批一流的畫家一一出現在銀幕上,唯獨缺少你劉海老,那會給國內外觀眾留下什么樣的遺憾?社會輿論將會出現什么樣的評說呢?我希望劉海老以民族文化大局為重,三思而行!”這一下,輪到劉大師愣住了。夏振亞也不知哪來的勇氣,斬釘截鐵地說了三個字:“告辭了。”說完起身就走。此時,劉海老真的急了:“慢,請吃了飯走……”最后,劉海老終于被說服了:“那……我寫一幅字給你。”endprint
同時,劉海老的夫人夏伊喬也竭力挽留夏振亞,趕忙鋪紙,備墨。大師劉海粟凝一凝神,筆下墨飽氣盛,飛出八個大字:“云水襟懷,松柏氣節。振亞同志正腕,劉海粟年方八六。”天哪!這位重量級大師,對夏振亞如此評述,他深感驚怵!大師雖“狂”,畢竟明理,顯然用題字接受了夏導演的意見,還讓這個小字輩“正腕”,難以承受啊,更激起了夏振亞對大師的崇敬之情。
過了一關又一關。正逢劉海粟九十大壽慶典,要當場即興作畫,這是攝制組搶拍的極好機會,但要劉海老按照夏導演的影片構思,命題作畫,十分艱難,但又必須這樣做。情急之下,夏振亞不得不找劉海粟的秘書攻克難關。問他:“你知道劉海老現場畫什么嗎?”“不知道。”“有誰會知道呢?”“誰也不會知道。”“那么,就請你轉告,我希望劉海老潑墨、潑彩畫黃山。”“哦,夏導演呀,你真會為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劉海老的脾氣,有誰敢向他命題作畫?他又怎能接受別人的命題作畫?我不會轉告。”“不,這次就破例,只好為難你一回。”“不行,不管你怎么說,我不能這樣做,也不敢這樣做。”說完,劉海粟秘書頭一轉,拔腿就走。夏導演緊追上前,嗓門拉大:“請留步。”接著,惱火地明知故問:“你是不是劉老的秘書?”對方不語。“你知不知道秘書的職責?”秘書仍然不語。“我告訴你,秘書就是上傳下達。如果我的命題有錯,劉海老怪罪的那是我,根本與你無關,你怕什么?”此時圍觀的人很多,也頻頻點頭,夏導演緊接著說:“而你作為秘書,對別人意見不轉達,這就是你的不對,到時,劉海老怪罪的恰恰不是我,而是你……”周圍的人連聲附和:“是的,是的,有道理。”秘書顯得尷尬與無奈,只得向主席臺走去,向劉海老俯身耳語,卻看到劉海老既沒點頭,也沒搖頭,這使夏導演忐忑不安,緊張到了極點……
正式搶拍劉海粟九十大壽即興作畫的電影開機了,只見他略略幾筆涂抹,左右上下揮灑,隨后將兩大碗清水分別與濃墨重彩攪和,先后傾潑畫幅。頓時,一“潑”激起千層“浪”,松濤呼嘯亂云飛,一幅《黃山松云》圖被永遠定格在膠卷上,成為歷史性的經典鏡頭……正是“不打不相識”,后來夏振亞每次見到劉海粟,老人總是逗趣地對夏導說:“我這個狂人總算碰上你這個狂人!”夏導演連忙回答:“豈敢,豈敢。”從夏振亞和劉海粟首次見面,就擊出“釘頭碰鐵頭”似的“火花”,倒是最能折射出兩人視藝術為無比崇高與神圣,對藝術追求的執著而“固執”,顯露了各自獨特的個性和風骨,也從更深的層面上達到了溝通,以至配合默契和諧,水到渠成,完美無缺。
綜觀上述,夏振亞的確是集電影、文學、書畫“三絕”于一身的“三棲藝術家”,究其原因,這“三絕”源于他的“三氣”,即“才氣、靈氣、大氣”,這“三氣”明顯地體現在他的銀幕上,貫通于他的文章里,融化到他的書畫中。這是一個藝術家綜合實力的體現,他的才華有跌宕漫涌之勢,驚濤裂岸之態。他富有智慧,敏于思考,感悟人生,奮力揚鞭,是藝術征途上當之無愧的勇敢騎士。至此,我們亦能破解“夏振亞”這個名字和奇才的確切含義,那就是不畏艱險,不斷振奮,不惜辛勤耕耘的華夏子孫!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