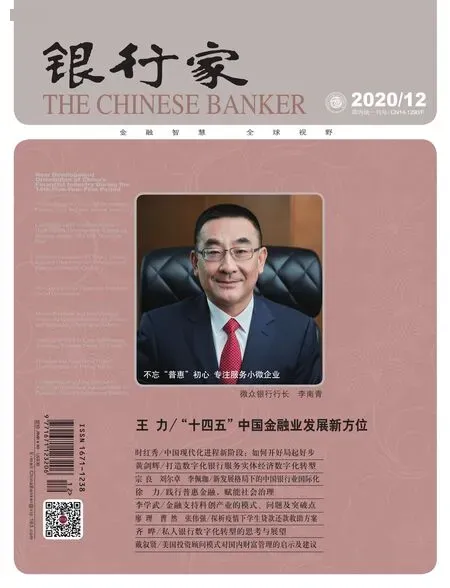中國財政狀況的評估與應對
陳漢鵬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雖然各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但世界經濟普遍復蘇乏力,這直接導致了各國負債率的不斷攀升。許多學者、官員和國際組織都對此提出了警告。但盡管如此,2014年發布的《日內瓦報告》卻發現,當人們都在討論全球經濟如何去杠桿、減輕債務的同時,世界各國的實際債務水平卻在不斷地提高。表1給出了2001~2016年世界各主要國家政府負債與GDP的比值。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世界各國的政府負債率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前都相對平穩,但在2008年以后卻發生了顯著的提升——包括德國在內的各發達國家政府負債率均突破了60%的警戒線,美國的負債率超過了100%,日本更是達到了240%。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目前雖然維持著較低的負債率水平,但隨著危機后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的出臺,政府負債率上升得很快,這同樣引起了部分機構的關注。例如國際三大信用評級機構惠譽、穆迪和標準普爾就分別于2013年4月、2017年5月以及2017年9月下調中國的長期主權信用評級。其中,三大評級機構調低我國信用評級的一個共同的理由就是政府債務累積所導致的財政狀況趨弱。對此,盡管我國的官方機構,如財政部、銀行業協會等,官媒,如新華社、人民日報,以及一些學者,如余永定、趙錫軍等都做出了強烈的駁斥,但中國近年來負債率持續攀升的客觀事實也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引發了人們的擔憂。在此背景下,本文對已有的關于財政可持續性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做了一些簡單的梳理,指出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對中國財政狀況的評估與應對方法。
對財政可持續性問題的回顧
目前國際上對財政可持續性的主要判斷標準是一國的負債率(債務/GDP)在長期是穩定收斂,而不是發散的。要維持財政的可持續性,政府或者可以通過未來的基礎盈余來削減債務,或者通過通貨膨脹來稀釋已有的債務,又或是借助利率期限結構的調整來控制負債率。通過政府跨期預算約束方程可以證明,只要政府在未來各期的盈余或赤字的現值等于當期的債務,則該國的財政便是可持續的。
這些研究無疑為人們判斷一國的財政狀況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參考依據,許多學者也都在此基礎上展開過相關的實證分析。其中實證研究的方法大體可分為兩類:第一類研究側重于回顧過去,即通過歷史數據總結政府負債率與其余主要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并且在假設政府維持過去財政政策不變的前提下,判斷政府長期財政的可持續性。第二類研究則更加關注于對未來的預測,此類研究將政府未來的經濟增長和負債所需承擔的利息率視為外生給定,通過政府對未來的經濟規劃或是各種情境的假定來推測財政支出,以此作為政府負債率或稅收缺口未來走勢的計算依據。相較而言,由于第二類研究更加具有前瞻性,且能夠與政府的其他部門,如預算規劃單位的研究相結合,因此受到了眾多機構,如國會預算辦公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的推崇。
目前對于中國政府財政可持續性問題的研究已有許多,主流(也是官方)的觀點一般認為中國政府的債務規模相對可控,但由于近年來債務率的上升速度過快,因此需要警惕由于債務過高所帶來的其余負面影響。
已有研究存在的問題
上述研究雖然有助于我們加深對政府財政狀況的理解,但就其實用性而言卻比較有限,理由具體包括:
第一,財政可持續性強調政府的“長期”可持續性,這對于更加關注中短期(5年以內)的政府而言沒有太多的指導意義。根據該理論,只要政府在長期維持財政預算的跨期平衡,則無論當期的負債率或赤字率有多高,財政仍然是可維持的。但這種假設通常過于理想化,因為在現實中,一國經濟會受到各種各樣正面或負面的沖擊。當一國政府的負債率達到一定程度時,其受到很小的負面沖擊都有可能引發市場的恐慌,從而令該國的融資成本飆升,財務狀況迅速惡化,這時政府對未來財政能夠“扭虧為盈”的許諾未必能夠給予市場足夠的信心。換言之,傳統的財政可持續性理論只是提出了一種理論上可能存在的假設情境,卻沒有給出如何達到這種情境的具體建議。
第二,通過歷史數據的實證檢驗所得到的一國財政是否可持續的判斷也沒有太多的借鑒價值。一方面,政府的財政政策會根據具體的經濟情況進行相應的調整,因此在過去財政政策框架下所得到的結果并不能作為目前財政政策是否可持續的依據;另一方面,一國財政的收入與支出與實際經濟情況是密切相關的,在通常情況下,政府的負債率在經濟繁榮時期會低于經濟衰退時期。因此在沒有考慮政策與經濟環境時變性特征的背景下,用過去的結論來判斷現在和未來的財政狀況容易產生偏差甚至是誤導。
第三,目前絕大多數的研究都將利率和經濟增長率視為外生給定的局部均衡分析,并沒有與政府的財政變化情況做一個有機的結合,這顯然不符合實際情況。由最基本的宏觀經濟學原理即可知道,政府的財政收支、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和利率這些與財政可持續性密切相關的經濟變量彼此之間有著很強的相關關系。這時,如果只是將各個機構對未來經濟變量的預測組合起來,其所得到的關于財政狀況的最終結論實際上是一種假設出來的結論,充其量只是一種情境的模擬,而非實際論證推導得到的結果,這就令其意義大打折扣。
本文的分析方法
根據上文的分析,筆者認為政府在長期的財政狀況能否持續雖然具有理論價值,但現實意義卻不大。相對的,我們更加應該關注政府債務在有限期內的波動,這才是政府在實際調控過程中所關注的。本文構建了一個能夠反映政府負債率短期波動的財政負債壓力指標,其不僅具有經濟條件和宏觀調控政策的時變性特征,并且所有與該指標相關的經濟變量都是內生得到的,這樣就避免了人為主觀臆斷對結果造成的偏差。
具體的,由政府的跨期預算約束方程可知影響政府負債率的主要經濟變量包括各期的政府財政收入與支出(用與GDP比值表示)、實際經濟增速、通貨膨脹率、名義利率,將這些變量與政府負債率一同構建遞歸的VAR模型,從而預測出各個時期政府負債率的未來實際變化情況。我們知道VAR模型雖然由于缺乏嚴謹的理論基礎而被詬病,但是其便利性以及在預測,尤其是短期預測方面的能力卻是毋庸置疑的。同時,通過對模型的遞歸估計,我們確保了各期的預測值可以反映當時的經濟信息,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指標可以不斷地被更新而不必對過去的指標進行反復的重新。為了簡化分析,本文只考慮財務狀況未來一年的變動情況,即利用年度數據的遞歸VAR模型進行一步向前預測,并將當期的負債率去除預測得到的下一期負債率,從而得到相應的財政壓力指標。顯然,當該指標大于1時,政府負債率預期將升高;反之則下降。
與傳統方法相比,雖然本文所提出的指標無法給出一個關于財政可持續性的具體標準(根據已有的研究和現實世界的例子可知,并不存在這種簡單的判別標準),但它至少能夠向政府傳遞財政負債率在近期將上升或下降的信號,從而起到一種預警的效果,因此筆者認為該方法比傳統方法對政府而言更加具有指導和借鑒價值。
中國的財政狀況分析
圖1和圖2分別給出了中國1981~2016年與財政狀況相關的主要經濟變量。由圖1可以看出,中國政府的負債率在整個樣本區間基本維持著上升的趨勢,尤其是2012年以來,政府為了減緩經濟增速的下滑,政府支出和收入的缺口逐漸拉大,這直接導致政府的負債率迅速升高,從2012年的34.27%上升到2017年的44.29%,五年上升了10個百分點。由圖2可知,因為我國長期以來都維持著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在絕大多數時期中國的實際經濟增速都要高于國債利率與通貨膨脹率的差額(實際利率),因此根據傳統的財政可持續性理論,至少在目前中國的財政可持續性并沒有太大的問題。

根據上文對財政壓力指標構建方法的介紹,本文利用1981~2016年中國政府的負債率、收入比率、支出比率、實際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國債平均發行利率建立二階滯后的向量自回歸VAR(2)模型。我們首先以1981~2000年數據為樣本區間,對VAR(2)模型進行估計,并在此基礎上預測2001年政府負債率的具體數值。接著用2000年政府負債率去除2001年預測得到的政府負債率,即可得到2000年政府的財政負債壓力指標。接著將樣本區間擴大至1981~2001年,以此得到關于2001年政府的財政負債壓力指標,依此類推就可以得到中國財政負債壓力指標2001~2016年的時間序列。
根據上文的定義可知,當財政負債壓力指標大于1時,政府的負債率預計將會上升,反之則會下降。觀察圖3,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政府的債務壓力要小于危機后的債務壓力。在2008年以前,政府的財政壓力指標大多在1附近徘徊,最高也沒有超過1.05,因此這段時期的政府負債率是較為平穩的,基本維持在24%至29%之間。相對的,2008年以后,政府的財政壓力明顯放大,在8個年份中有3個年份的財政壓力指標超過1.05,這使得政府的負債率從2009年的34%上升至2016年的44%。
第二,將圖1和圖3相結合我們可以發現,本文所構建的財政壓力指標具有一定的先導性,能夠反映政府未來負債率的變動情況。例如圖3中財政壓力指標小于1的年份為2005年、2007年和2009年,其基本上都對應著圖1中政府負債率的波峰。同時,財政壓力指標最高的2008年,在其下一年的政府負債率也從27%一躍提升至34.35%,提升幅度超過7個百分點,是整個樣本區間內負債率上升最快的年份。
第三,將圖2和圖3作比對可以發現政府的財政壓力指標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當經濟增速較快,通貨膨脹水平較高時,政府的財政壓力指標較小;反之,當經濟增速放緩,通脹水平較低甚至通縮時,財政壓力指標較大。這一點不僅反映了財政具有逆周期調整的經濟自動穩定器的功能,同時也表明本文所構建的財政壓力指標能夠反映經濟條件變化對政府財政壓力的沖擊。
第四,2016年的財政壓力指標為1.06,屬于較高水平,因此筆者認為中國2017年的負債率仍會有較為顯著的提升。
如何面對不斷提高的負債率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中國目前的負債率仍處在一個持續的上升期。那么政府應該如何面對這一問題呢?筆者認為一方面,我國沒有必要由于一些國際通用標準或評級機構的建議而人為地設置一個界限,如負債率或赤字率。各國由于所處的發展階段和經濟環境不同,很難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評價標準。以著名的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為例,其所規定的赤字率不得超過3%,負債率不得超過60%的標準只是歐洲國家根據自身發展的經驗,不同成員國之間相互談判協商后達成的協議,本身并沒有經過嚴格的科學論證。而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直接套用發達國家的經驗準則顯然是不合適的。事實上從表1可知,即便是德國,其負債率也早已超過了60%。
另一方面,雖然沒有明確的負債率、赤字率的界限,但必須清楚地知道,所欠的債務最終都必須要償還的,因此我們必須密切地關注政府債務的變動以及該變動所可能帶來的影響。當債務率加速上升或下降時,必須清楚地知道債務率波動的原因,如果要控制債務率的話有哪些手段,以及在調控過程中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中國作為一個人均收入較低的發展中國家(2016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為8260美元,在世界銀行公布的216個國家中排名第93位),很多時候需要在經濟發展和財政穩定性之間做出權衡。就筆者所知,目前對財政可持續性問題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一種局部均衡分析,因此無法從全局的角度把握財政收支對經濟各部門所帶來的影響,這在未來有待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