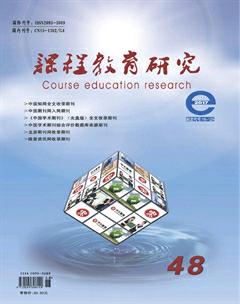雙語雙方言現象與學生筆頭“稚譯”創新性關系研究
【摘要】本論文基于英語專業本科生筆頭“稚譯”問題,研究廣東省雙語雙方言現象與學生筆頭“稚譯”之間的深層關系,為探究教學過程中可能施行的去“稚”方略做研究準備,以利地道標準譯文,規范并優化根植于雙語雙方言地區的各高校英語、商務英語及翻譯專業翻譯類課程的教與學,并為未來研究各地域雙語雙方言現象對地方院校筆譯教學與學習的影響打下基礎。
【關鍵詞】雙語雙方言 筆譯 稚譯
【課題項目】廣東科技學院2016年度院級科研項目:雙語雙方言地區“稚譯”規律性現象研究(GKY-2016KYYB-35)。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7)48-0028-01
學界對雙語雙方言現象研究由來已久,涉及中國境內各個地區近3000種方言,由于筆者供職的廣東科技學院學生生源地主要是廣東省,因此本論文側重研究廣東省雙語雙方言現象,創新性研究普通話與本地話,粵方言與客家方言對學生筆譯產生的影響。
一、國內外雙語雙方言研究現狀
國家語委語言文字研究所曾對我國語言文字使用情況進行過詳盡的調查,其中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雙語雙方言問題,經國家語委問卷設計、調查實施和數據匯總,已基本討論清楚雙語雙方言的概念范疇、各地區常見的方言種類以及使用頻度等,這為本論文的研究以及后續“去稚”方略研究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語言學專家陳恩泉在《雙語雙方言研究的學科思考》中指出,當雙語人進行交際的時候,言語信息庫必須具備同對方所用相同的語碼系列,才能自由選用并以此為基礎生成言語形式(編碼),作為反射信息輸出而形成思想、語言行為,使思想交流成為可能。這是雙語人進行雙語交際的基本功能:代碼變換的能力。對于雙語人來說,代碼變換的功能越強,雙語交際過程就越流暢,“譯文”的質量也就越高。在黃長著等編的《語言與語言學詞典》里,雙語有兩個對應單詞:bilingual和diglossia,前者一般指人們所說的兩種語言,后者多指標準語和方言。在我國,有許多學術著作和論文把diglossia稱為“雙言”。雙語雙方言的界定有廣義和狹義之分,詹伯慧在《雙語雙方言》(二)(1992)明確提出普通話與方言的關系屬于雙語范疇;李英哲在《雙語雙方言》(三)中把普通話與方言的關系稱為“雙方言”,這是較受國外社會語言學家認可的做法;廣義的雙語可包括方言和外語,雙方言的概念也多指兩種漢語方言。黃忠廉在《方言翻譯轉換機制》一文中提到,所謂方言間接轉換機制,指原語方言必經語內轉換才可轉換成譯語方言或標準譯語的過程,呈現為曲折型翻譯路徑。具體表現為:①原語方言→標準原語→標準譯語→譯語方言;②原語方言→標準原語→標準譯語;③原語方言→標準原語→譯語方言;④標準原語→標準譯語→譯語方言。黃忠廉指出原語理解階段多半要經方言轉換為標準語的過程,譯語表達階段可能經過標準語轉換為方言的過程。
美國哈佛大學語言學家Charles A. Ferguson于1959年在Word雜志上發表了Diglossia一文,首次提出diglossia(雙言現象),在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在Diglossia 《雙言現象》(李自修譯)中,把這種方言區的許多人除了會說母語以外,還會說普通話或者其他方言的現象稱為“雙言現象”。Diglossia這個詞源于法語詞diglossie,從而區別了雙語的概念。如今,該理論已獲得學術界的普遍認可,歐洲其他語言也用該詞表示“雙語現象”。在Ferguson之后還有一些語言學家繼續討論雙言現象,Joshua Fishman認為,“雙言現象”說明語言功能的社會分布。前蘇聯的什維策爾(ADBeep)在《現代社會語言學》一書中,將雙語現象定義為:是在同一言語集體范圍內兩種語言并存的現象,該言語集體依據交際行為的情境及其他參數在相應的交際領域內使用其中的某一種語言。將雙言現象定義為:雙言現象是同一語言的兩種并存的變體相互作用的現象,該言語集團的成員依據交際行為的社會情境和其他參數在相應的交際領域內使用這種或那種語言變體。
二、雙語雙方言對學生筆譯的影響
在給英語專業學生和商務英語專業的學生進行《翻譯理論與實踐》、《商務英語翻譯》授課及輔導的過程中,發現學生的筆譯普遍存在以下問題(譯例選自賈一村,單宇鑫,賈文波.《應用翻譯簡明教程》)。
1.英漢詞匯量不足導致“稚譯”。例1:一幢鄉村小學的教學樓,建了7年還是個半拉子工程。在此例中,部分學生不知道“半拉子”的意思,因此翻譯不出類似“never?鄄to?鄄be?鄄finished project”這樣的地道譯文,譯文多帶稚氣。例2:Farmers now sell their vegetables at moving prices determined by their supply and their customers?蒺 demands. 在2013級英語本科1-6班約240位學生中,僅有不到十位同學聽過并會使用“隨行就市”一詞,多數學生的譯文冗余稚氣。經咨詢,發現原因是學生使用的方言中鮮少涉及以上詞語。
2.專業術語、行話、知識欠缺導致“稚譯”。例1:Suspension bridges are frequently constructed in preference to other types of bridge. Suspension bridge意為“懸索橋”,學生“稚譯”如下:吊橋、懸拉橋、斜拉橋、蘇士本斯橋,甚至吊脖子橋!例2:High?鄄speed magnetive levitation (MAGLEV) systems, with top speeds between 250 and 300mph. 學生缺乏基本的常識,甚至疏于思考,“稚譯”為高速磁懸浮列車每小時運行250-300米。
3.選詞用字、語言表達能力匱乏導致“稚譯”。例: Hence my eye was sharp, but so was my ear and my nose, I was open to experiencing aesthetically. And on the way I did take minor pleasure in a bird?蒺s song, a tree?蒺s sway, and a cloud?蒺s contortion. 參考譯文中多使用“目光明銳、聽覺靈敏、嗅覺敏銳、我敞開心扉、所見所聞、鳥雀鳴唱、樹影婆娑、云卷云舒”等優美字眼,但學生很少使用成語或四字句,譯文多呈現“小鳥的歌唱、小樹的搖擺”,甚至“云朵的扭彎”這樣的“稚譯”。
正是由于方言和普通話的語言表達差別巨大,因此,才會出現學生沒有聽說過“半拉子”、“隨行就市”等常見語言表達的現象。通過多年翻譯教學,筆者發現,把學生筆頭“稚譯”全部歸咎于較弱的雙語語言能力或者“雜學”知識匱乏并不科學,雙語雙方言的語言習慣在筆頭“稚譯”中確實起到了較為明顯的作用,并且,我們應該很清楚的意識到,這一現象無法短時期內根除,因此,十分有必要繼續研究雙語雙方言在哪些具體方面影響了學生的筆譯,有哪些措施可以“去稚”,作為教師,在課堂上又應如何引導學生用普通話去思維,去翻譯?應如何在保護好學生方言文化的前提下,讓“稚譯”現象逐漸隱匿呢?
三、結束語
學生已形成熱愛自己方言文化的心理狀態,在日常的生活和學習過程中,有意或無意“回避”普通話,較樂意或習慣接受方言作為傳播語言的電視節目、網絡新聞、音頻視頻等文字資料或口頭資料。導致學生譯文充滿“稚氣”的原因多種多樣,深挖“稚譯”的根本原因在于:學生所掌握的方言,包括口頭形式和書面形式,根深蒂固,自成體系,即“完全方言體系”,而方言大大區別于普通話,造成學生對規范譯文中的許多表達十分生疏。因此有必要繼續挖掘雙語雙方言與學生筆頭“稚譯”之間的關系,為后續研究學生的思維轉換機制,以及可能施行的“去稚”方略打下良好的基礎。
參考文獻:
[1]陳恩泉.雙語雙方言研究的學科思考[J].學術研究,2000.
[2]前蘇聯什維策爾.《現代社會語言學》[M](衛志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3]黃忠廉.方言翻譯轉換機制[J].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4]賈一村,單宇鑫,賈文波.《應用翻譯簡明教程》[M].中南大學出版社,2015.
作者簡介:
單宇鑫(1986.05-),女,漢族,河南信陽人,碩士研究生,廣東科技學院外語系專任教師,研究方向:翻譯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