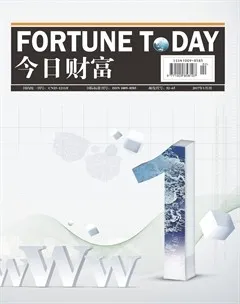人民幣匯率波動性的實(shí)證分析
人民幣匯率頻繁波動,分析其動態(tài)特征具備理論和現(xiàn)實(shí)意義。以2013年1月至2015年7月間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匯率為分析對象,利用GARCH族模型得出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存在杠桿效應(yīng),即壞消息引起的匯率波動大于好消息引起的波動。
一、引言
2017年5月25至6月1日,人民幣連續(xù)飆升,短短4個交易日內(nèi),在岸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最高觸及6.7878,累計(jì)最大升幅1.5%;同期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最高觸及6.7238,累計(jì)最大升幅2.2%。匯率波動給社會經(jīng)濟(jì)帶來巨大影響,研究和掌握匯率波動的動態(tài)特征具有理論和現(xiàn)實(shí)意義。
國內(nèi)有關(guān)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實(shí)證研究成果豐富,但大多數(shù)文獻(xiàn)集中于利用ARCH模型及其拓展模型對其進(jìn)行實(shí)證驗(yàn)證。趙樹然(2012)利用非參數(shù)GARCH模型對美元和日元兌人民幣匯率的日對數(shù)收益率進(jìn)行預(yù)測,并將其結(jié)果與參數(shù)GARCH族模型的預(yù)測結(jié)果進(jìn)行比較,表明非參數(shù)GARCH模型具有最強(qiáng)的預(yù)測能力。夏強(qiáng)(2012)通過設(shè)定雙門限非線性的GARCH模型,結(jié)合GJR效應(yīng),并且利用基于MCMC算法的貝葉斯推斷,來考察非美元匯率收益的均值和波動不對稱的特點(diǎn)。實(shí)證分析結(jié)果表明非美元匯率收益的均值和波動同時表現(xiàn)出非對稱的特點(diǎn)。張欣,崔日明(2013)基于非對稱隨機(jī)波動模型(ASV)與 MCMC 估計(jì)方法,對2005年7月22日至2012年9月5日期間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的波動特征進(jìn)行了實(shí)證分析,得出人民幣匯率的波動過程不僅存在時變特征,而且其波動過程具有很強(qiáng)的持續(xù)性,人民幣匯率波動性對利好利壞的反映存在顯著的非對稱特征。
二、數(shù)據(jù)的選取與處理
本文選取2013年1月4日到2015年7月31日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的每日中間價(jià)為研究對象,記Rt為日對數(shù)收益率,。
觀察對數(shù)收益率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其呈現(xiàn)出群集波動現(xiàn)象。對收益率數(shù)據(jù)進(jìn)行J-B檢驗(yàn),統(tǒng)計(jì)量為287.3433,概率值0,拒絕正態(tài)分布的假設(shè)。
對收益率Rt進(jìn)行自相關(guān)檢驗(yàn),發(fā)現(xiàn)Q-統(tǒng)計(jì)量的P值都大于5%的置信水平,故收益率序列Rt不存在自相關(guān)。由此將均值方程設(shè)定為白噪聲。
三、實(shí)證分析
(一)收益率序列數(shù)據(jù)的平穩(wěn)性檢驗(yàn)
對人民幣匯率收益率序列進(jìn)行ADF單位根檢驗(yàn),t統(tǒng)計(jì)量的值為-24.54367,小于1%、5%、10%顯著性水平下的t統(tǒng)計(jì)量的臨界值,拒絕單位根檢驗(yàn)的原假設(shè),認(rèn)為人民幣收益率序列是平穩(wěn)的數(shù)據(jù)。
(二)ARCH效應(yīng)的檢驗(yàn)
對收益率序列數(shù)據(jù)進(jìn)行ARCH效應(yīng)的檢驗(yàn),對收益率序列異方差性檢驗(yàn)可以看出F統(tǒng)計(jì)量的值為60.18487,相應(yīng)的P值為0,觀察值R^2為56.69066,相應(yīng)的P值為0,所以拒絕ARCH模型殘差項(xiàng)不存在異方差性的假設(shè),即人民幣收益率序列 存在ARCH效應(yīng)。故綜上所述,對人民幣收益率建立GARCH模3r0Y3pjf/FfXX38vS/xT1Q==型。
(三)建立GRACH模型
常用的GARCH模型由GARCH(1,1),GARCH(1,2),GARCH(2,1),對以上三個模型均進(jìn)行擬合, 最終結(jié)果表明模型GARCH(2,1)的系數(shù)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yàn),而GARCH(1,1),GARCH(1,2)均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檢驗(yàn),結(jié)合AIC及SC準(zhǔn)則,認(rèn)為GARCH(1,1)模型能夠更好地?cái)M合數(shù)據(jù)。其條件方差對應(yīng)的方程為:
對GARCH(1,1)模型擬合后的殘差進(jìn)行ARCH LM檢驗(yàn),發(fā)現(xiàn) F統(tǒng)計(jì)量和觀測值的R^2統(tǒng)計(jì)量對應(yīng)的P值明顯大于0.05,故此時模型的已不存在ARCH效應(yīng)。
(四)建立TGARCH模型
對TARCH(1,1)模型擬合后的殘差進(jìn)行ARCH LM檢驗(yàn),結(jié)果表明F統(tǒng)計(jì)量以及觀察值和R^2統(tǒng)計(jì)量對應(yīng)的P值均明顯大于置信度0.05,所以接受原假設(shè),認(rèn)為此時殘差序列已不存在 ARCH效應(yīng)。此時條件方差對應(yīng)的模型為:
四、結(jié)語
通過對2013年1月至2015年7月間的美元兌人民幣日匯率數(shù)據(jù)進(jìn)行分析,得出收益率序列具備群及波動、尖峰厚尾、以及不服從正態(tài)分布的特征。對人民幣收益率數(shù)據(jù)序列進(jìn)行檢驗(yàn)發(fā)現(xiàn)其殘差序列存在ARCH效應(yīng),為了驗(yàn)證利好利壞消息的非對稱性對數(shù)據(jù)建立TGARCH模型,通過反復(fù)對比發(fā)現(xiàn)TARCH(1,1)模型的系數(shù)經(jīng)過了統(tǒng)計(jì)檢驗(yàn),且擬合結(jié)果更好,進(jìn)一步得出,證實(shí)了杠桿效應(yīng)的存在。
(作者單位為湖北工程學(xué)院經(jīng)濟(jì)與管理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