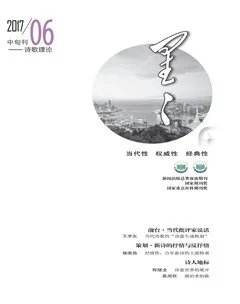詩意世界的展開
一
最初知道李白鳳這個名字,是在閱讀和輯錄朱英誕新詩史料的時候。朱英誕在回憶文章中多次說到李白鳳是他早年的詩友,1934年與他就讀于北平民國學院,為同班同學。其時來兼課的是正在現代詩壇獲得詩名的林庚先生。林庚先生講授新詩創作,朱英誕、李白鳳深受影響,從此走向現代詩歌創作。他們一同寫詩,課余到林庚先生家中拜訪、論詩,后經林庚先生結識廢名,李又先朱一步結識當時文名正盛的周作人[1]。李白鳳夫人劉朱櫻《憶李白鳳》一文也特別提及:“1934年白鳳考入北平民國學院國文系學習,授課教授是林庚先生。他們在新詩創作方面談得很融洽。”[2]八十年代以來,李白鳳不時為文學史家提及,比如施蟄存《懷念李白鳳》,程光煒《詩人李白鳳先生》,陸耀東《中國新詩史1916—1949》相關章節的介紹。
李白鳳(1914—1978),生于成都,四歲時隨父定居北京,家學淵源深厚。少年時曾在天津、青島讀書。現在能見到的李白鳳最早的詩作,是一九三五年發表于《星火》雜志的《無題》《春在人間》等。李白鳳一開始明顯沾染著京派現代主義詩人的風格。隨后兩三年,在《新詩》《小雅》《詩志》發表《小樓》《夜航船》《八個如云的幻想》《一花一世界》等詩作。抗戰前夕輾轉蘇州、湖南芷江等地。抗戰期間漂泊于香港、南寧、桂林等地,寫作、教書當編輯謀生,為抗戰鼓與呼。1946年到上海。這一時期出版詩集有《南行小草》(獨立出版社,1939年),《春天,花朵的春天》(點滴書屋,1948年),《北風辭》(上海潮鋒出版社,1949年)。1950年代初先后到哈爾濱工業大學、太原山西師范學院任教,1954年以后長期任教于河南開封師范學院中文系,多次受到政治運動沖擊。[3]
這樣一個面影,給人感覺更多的是一個“現代主義詩人”。他的詩歌生涯,與朱英誕、林庚、吳奔星、施蟄存、戴望舒交集甚多。幾種選本,也有意無意地將他列入現代派的行列,1948年出版的《聞一多全集》中收錄的《現代詩抄》手稿錄有李白鳳《小樓》一詩,1980年司馬長風著《中國新文學史》也收錄《小樓》,1986年版藍棣之編《現代派詩選》選李白鳳《夢》《白蓮》《花》《星花》等八首,2010年《中國新詩大系》第2卷孫玉石選了李白鳳《小樓》《夜航船》《珍珠集》《月幻想》。司真真、王叢陽等幾位研究者也是從“現代主義”視角入手來透視李白鳳的風貌的。
知人論世,通觀李白鳳三十年代前期至解放后的詩歌寫作,會發現李白鳳不單純是一個“現代主義”詩人,他的詩歌理路的形成要復雜得多,他的詩風并非單一而恒定的。李白鳳先后借助“現代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多種寫法展開了自己的“詩意世界”。
二
所謂“詩意世界”,就是詩人在詩歌中展現出來的關于世界的圖景。美國文藝理論家M.H.艾布拉姆斯在他提出的“作品—藝術家—世界—欣賞者”文學四要素說中,如此解釋“世界”:“一般認為作品總得有一個直接或間接地導源于現實事物的主題——總會涉及、表現、反映某種客觀狀態或者與此相關的東西。這第三個要素便可以認為是由人物和行動、思想和情感、物質和事件或者生命感覺的本質所構成,常常用‘自然不’這個通用詞來表示,我們卻不妨換用一個含義更廣的中性詞——世界。”[4]由此可知,“詩意世界”是在“現實事物”基礎上的“變現、反映”,它的本質是人們的思想、情感、生命知覺,這些本身構成一個“完足的世界”。對這一世界的獲致、抵達,涉及到事物、生命、語言、修辭等諸多要素,簡言之,詩人獲得他的世界,同時也是獲得一種活法(對待世界、對待生命的方式)、一種技法(語言表達的規范、修辭技藝和各種秘密的技術),投入進去,獲得經驗、想象,將其轉化成一個全新、完整世界的構成要素。前面提到的幾種主義,現代主義、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不僅是就風格、技法而言,而且是整個的活法、語言狀態和精神氛圍而言,它們是高度綜合的。
現代主義詩人對世界和自身充滿了不確定的看法,這個“不確定”來源于世界本身的“動”和“反抗”的時代精神[5],及現代人“感覺的分裂”(T.S.艾略特語),因此在言說和書寫時把語言也弄得含混不清,在表達上更是不明言、多方暗示。因為感覺本來就是紛繁交混的,必須以混雜表達混雜,表達得清晰明確,反倒有違真實。所以感覺對象的“肉體化”“玄學化”和“超現實”,表達上的“象征”“多義”“蒙太奇”成為必然。李白鳳的創作,大概從1930年代初到1937年5月的《星花》,這一段基本是偏于現代主義的,正如前面所言,這和林庚、廢名等人的影響有關,和他一開始即身處現代主義詩歌的大氛圍、和他自身的青春期體驗有關。
在形式、趣味上,李白鳳一開始便接近了現代主義。“小病的人是幸福的/乃有更多的幻想/幻想著無數的蓮花燈燃在天上/天有水的波紋了/說是菩提樹不宜于種在沙漠里/這原是沙漠的悲哀/我愿將靈鷲峰移在大海上”(《小病》),詩人審視自我的病體,進入對生命的體驗。“真是不堪其擾/那星子來時多在/夢中”(《曉色》),“月之影/在每一樹濃密的花蔭下/裹著風”(《月之影》),這些詩句,都可看做是富于現代主義色彩的斷片,詩人不時地將自己的在現代社會的經驗、生命體驗和潛意識的內容形象地宣示了出來,使人隱約看到孤獨地徘徊在現代都市街頭、深巷的現代主義詩人形象。
與朱英誕、林庚、廢名的寫法相似,李白鳳的現代主義嘗試很有中國氣派。廢名評價林庚的詩突然地來了一份“晚唐的美麗”,評價朱英誕,“在新詩當中他等于南宋的詞”[6],朱英誕說廢名作詩“是從古人的心事里脫胎出來的”[7],這些說法同樣適用于李白鳳早期的詩作。這一時期中國的現代主義詩人是在統合古今的雙重姿態中走向自己心目中的現代主義理想的。孤獨的現代意緒接通的是古典離人思婦的相思哀怨,對現代社會流動多變的不可把握感接通的是晚唐詩的時空疊合,表達上的象征多義接通的是宋詞寫法上的閃轉騰挪。“紫薇花前紫薇星/曉色迷茫中/微風伴著行人/默默地在花前徘徊/滿身花影由濃而淡——/新月落下樹時/遠處一聲雞……”(《曉色》),甚至可以說是對“獨立蒼茫自詠詩”“漫天花影滿天風”“細雨夢回雞塞遠”這些古典詩詞的復寫,縫合、改寫古典詩詞以表達自己孤獨無依的現代性體驗,詩思的展開,也是中途含蓄宛轉,末尾忽然宕開,試圖重開一個新的意境,類似于“填詞”。那首著名的《小樓》也是如此,在巧妙地渲染了一個文人眼中的水鄉暮色后,寫道:“小笛如一陣輕風/家家鄰水的樓窗開了/妻在點染著晚妝/眉間盡是春色”,也是亦今亦古,難分軒輊。李白鳳的部分詩歌很“廢名化”,借助禪思、禪語實現對“無名經驗”的命名和描述,比如《一花一世界·無題》:“乃有藍天的恨意/古代的牧人遠了/照見梵天的三十二應身/也愛著沙漠和我……/轉入無無明的世界里/兩步兩懸崖”,這樣的寫作陷入了抽象和不可解。
但是,李白鳳的寫法,與真正的現代主義尚有很大的距離和差異,這是不容忽視的。即使是在歸類化的、以流派為視點的批評研究中也應該重視的。現代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文化邏輯”[8],分裂的自我試圖以分裂的語言忠實記錄現代人在現代社會的孤絕處境和荒誕體驗。現代主義者“向內轉”,沉入深廣無邊的內心世界,相信他們心中的那些“無名經驗”,“孤獨和焦慮”是普遍化的,是對歷史的更真實的記錄。從這些方面來衡量,李白鳳顯然沒有上升到這樣的高度,三十年代前期他置身其中的北平、天津、青島等地還是一個半現代半古典的“文化空間”,對很多方面他只是隱約感到。他也沒能像卞之琳、戴望舒那樣借助對西方現代主義“想象的風景”的審視和模仿性體驗,長成一個程度較高的“現代主義詩人”。他的“現代主義想象”指向對生存處境、生命體驗的隱約言說,自我沒有高度分裂,自我經驗(諸如孤獨、荒誕、焦慮)也沒能上升為客觀化的經驗類型。李白鳳代表了非常孱弱的現代主義嘗試,他更多地是借助了現代主義的某些傾向、技法展開了自己的詩意言說。甚至可以稍微絕對地說,整個此一時期的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比如廢名、林庚、卞之琳、戴望舒的,均非純正意義上的現代主義詩歌,他們還顯得“孱弱”。我們對他們冠以“現代主義”“現代派”的稱呼,充其量只是一種暫時的假借。
三
李白鳳大約從1930年代中期開始強化了他創作中的浪漫主義傾向。陸耀東說他的詩喜歡“將見解直接說出來,象征、暗示不太強”[9],這是很客觀的見解。經過短暫的迷離,李白鳳的“自我”很快就結束了分裂,以一種自信、圓整的姿態抒情、想象。浪漫主義者總有太多的熱情需要抒散,于是想象成為吶喊、傾訴、呼告之外的另一種行為。想象,就是設定情境,使得主體得以投入其中,欲望得到暫時的滿足。李白鳳三十年代中后期的詩是在自我想象、愛情沉湎、戰爭激情三個維度上錯綜展開的。
這一時期發表的詩,無論是與死亡主題有關的《安息》,還是很有獵奇色彩的《豹》,都充滿浪漫主義氣息。輕言死亡,向世界道別可以說是二三十年代中國新潮詩人很喜歡做的事情,這種行為當然更多地是在紙面上來實現的。“也許明天是我的安息日/那末,請你們暫時替我/燃起一炷葬香吧”,這是向世界、“你們”的想象性告別,可能有現實的觸發,也可能是內心和世界積怨已久,“不要把我的眼睛/嵌在藍天里當太陽/死后的遺物/墓碑而已——”,“把眼睛嵌在藍天當太陽”,這樣的寫法直接而刺激,甚至引起恐怖而獰厲的感覺,但是這一看都是年輕人的想象。“眼淚”“眼睛”“墓碑”均顯得多余,真正的告別更傾向于無言,說白了還是放不下,有太多的話要說,情感“濃的化不開”(徐志摩語)。《豹》則把“自我”想象成一只孤身行走在荒漠中的“豹”,“豹”有“不可意識的興奮”“不可捉摸的心性”,更重要的是心中有“恨”,“渴望終有一日奔回自由自在的莽原”,這和里爾克那只壓抑著“偉大意志”的現代主義之豹有明顯不同,這只豹盡管也孤獨,“沙漠”雖然也是“現代都市”造成的印象,但它顯得外向多了。只不過是孤獨無侶,而且有奔回自由自在的莽原的愿望和力量,仍然是動感十足的,而非冷凝肅穆的。這里詩人的“想象性死亡”“物化”均指向“自我的孤獨”,是十足浪漫化的,這一“自我”還可以奔突變幻,心猿意馬,和郭沫若的“天狗”相一致,還沒有高度分裂,而且還沒有普遍地對象化為“自我的他者”。近代西方浪漫主義詩人喜歡寫古墓荒林、異域風光,李白鳳也是如此。
李白鳳1936、1937年頗寫了些愛情詩,這一方面和他這一時期戀愛、新婚有關,一方面也是借以投射青春的欲望,宣泄過多的壓抑的心理能量。寂寞人外的孤獨很容易和愛的沉淪合二為一,二者在本質上都和自我進入外部世界時的受挫有關,是一種貌似勇敢、實則孱弱的人生行為。這一類愛情或多或少都帶有自我封閉,逃避世界,沉迷于玄想的傾向,可以看作“真實的白日夢”。1937年5月發表在《新詩》雜志上的《星花》,由“幻想”“祝福”“允許”“感謝”及“星花”五章構成,幻想“我和你”抱著初生的孩子“站在生滿蔥綠苔蘚的巖石上”,站在海邊明月下,“我吻著你的靨/吻著你的長發如吻著天風”,兩人共同游冶在“玉琉璃做成院墻與小樓”的仙界,如夢似幻,“你愛明月/我愛滄海”,這里沉浸愛河,仿佛進入古典游仙詩中所寫的情境。詩人完全放縱了對“自我”的約束,放棄了對“時代”的疏離,跟著感覺走,完全是個人欲望化的抒寫。兩個月后發表在《新詩》上的《八個如云的幻想》是這一方面登峰造極的作品,更加自由自在地漂游在漫無邊際的愛欲想象世界中。“八個如云的幻想”分別是“月幻想”“海幻想”“星幻想”“風幻想”“花幻想”“草幻想”“鷹幻想”“魚幻想”,真是充滿了風花雪月的浪漫風味。八個章節、八種幻想,形成一種書寫套路,難免鋪張和重復。大致而言,基本采取“我”和“你”對話的模式,“我和你”化作相互等待、追逐的星月、風云、小鹿、花草、飛鳥、小船,起初相遇相知,后來相互誤解而分離,最后戰勝阻力重逢,愛得更深。這樣的愛,真是千變萬化,天上地下恣意穿梭,在海天宇宙中相愛相逐,也插入了新鮮而刺激的西化意象、名詞,甚至英文單詞。詩人不是像戴望舒、卞之琳那樣重在雕刻出一個個精美、玲瓏的詩歌文本,而是重在發揮自我的想象,宣泄過多的熱情,甚至帶有明顯的游戲性——是呈給她新婚的妻子劉朱櫻玩味的。從辭藻的華麗、想象的大膽、文風的外放等方面看,李白鳳《八個如云的幻想》堪稱1930年代最具羅曼蒂克風味的新詩創作,甚至可以說,李白鳳把郭沫若、徐志摩等人創造的浪漫主義新詩一途,在三十年代向前推進了一步,構成另一個脈絡。
抗戰爆發后,李白鳳作品中不時提到拜侖(拜倫)、惠特曼、馬耶可夫斯基(馬雅可夫斯基),這些詩人成為他的詩神。浪漫主義以其特殊的詩學特征,可以更容易地對待戰時環境,更容易地調整詩人在戰爭環境中的應對姿態。像穆旦、奧登這樣的詩人,在戰爭中更傾向于采取冷靜審視、反諷抒情的方式來處理戰爭經驗,相比較而言,李白鳳偏向于采取呼告式的,激情式地表達對戰爭的看法,較多從民族主義的視角來看待戰爭,揭露敵人的兇惡,歌頌詩人一方軍民的英雄主義精神,當然有時也能上升到對整個人類現代出境的悲劇性反思的高度,但是這樣的情況很少。
1939年11月在大后方重慶出版的詩集《南行小草》,更多地體現了面對戰爭的激情和意志。“二十世紀的詩人原都是少年/赤膽忠魂的英雄/我們互相用盡了槍與筆/在狼燧四起的祖國草原上/各自擔任了戍卒的辛勞”(《燧火中贈孫望兼柬令狐令德》),詩人一轉自我神經過敏、兒女情長的頹靡,直面戰爭,做“這偉大時代的記錄工作”,詩風變得明朗剛健。他歌頌抗日的新軍,表達對捐軀赴國難的英雄男兒的崇敬,以贈詩的方式規勸、勉勵他的詩人朋友們。“若你不耐于敵人的壓迫/你必須振起有力的臂膀/以精鋼鑄成之雙肩承受苦難/大踏步走上生死存亡的沙場”(《五月柬路易士》),“奏著懷鄉曲/還要學少年的行徑嗎/可惜天風偏要你流落天涯水涯呢”(《呈英誕》)。詩人熱情洋溢地為抗戰鼓與呼,號召朋友們挺起胸膛上前去。戰爭使人同仇敵愾,將個人裹挾進時代的洪流,為“自我”在現代社會面臨的孤獨處境提供了一條暫時的解決之道。
李白鳳整個三十年代的詩充滿了濃郁的浪漫主義氣息,他也曾在現代的荒原上孤獨地徘徊,沉溺在愛情的美幻空間里,抗戰爆發后忘我地鼓與呼,他不斷修復著受損、破裂的現代主體人格,投射、宣泄自我的躁郁的欲望,甚至不惜投入抗戰得以避免向內心世界的掘進。寫詩就是面對自身、面對世界,處理自我和世界的隱秘關系,李白鳳借助浪漫主義并不順暢地展開了自己詩意言說的過程。
四
接連不斷的戰爭、和現代性的曲折推進,可以說是1940年代最重要的兩個主題。一方面我們必須結束戰爭,換取獨立、統一,以便走向整個民族、國家現代化高速發展的道路,另一方面這一美好愿景又必須通過強化戰爭行為來實現。李白鳳這一時期的詩歌完全是符合時代精神的,他強化了在三十年代后期即已萌芽的現實主義寫法,轉向了現實諷諭。
“高空/V形之雁陣/帶著火種,爆炸物/飛來/他們企望著/以火毀滅世界/置新世紀文明于足下”(《火之成長》),這是對日軍空襲情景的直接記錄。“廣告畫將城市/點綴成繁茂的森林了/對于二十世紀人/我有走進野獸群的感覺//永遠失眠的/城市的街/點燈睜著黃昏的眼/這壞血病和患者胃病的城/完全消化不良啊”(《街區》),這是對戰時桂林街景的印象式抓拍。“吃罷!吃罷!//努力地吃罷/你大肚皮的臭蟲們!/張開你那善于大吃的嘴/貪婪地吃著/人們的血罷……”(《吃罷》),這是對國家的“碩鼠”們的控訴和諷刺。“吹打著/淫蕩的音樂/暴露出性的感應/這舞廳是/一只玻璃缸/裝滿了/各色各樣的魚”(《舞廳里的男女群像》),這是對現代性符號“舞廳”中“惡之花”的描摹。
除了不時歌頌未來,李白鳳寫的最多的,是對戰爭的憎惡,對統治階級黑暗腐敗的鄙棄、諷刺,對日益崛起的都市現代性的失望和不安,李白鳳自發地轉變,成為一個有左翼傾向的詩人,詩風與“七月派”詩人近似。他深切地意識到,建立在“自我信仰”基礎上的幻想和歌頌逐漸行不通了, “個人”日益變得孱弱,也走到了自己前期所依戀的“現代”的反面。歷史在線性的時間之路上,按照自身的邏輯狂奔著,歷史的行進是非人的,歷史正在進行的階段——現實,更加混沌不堪,像冰雪、烈火刺激著置身其中的人,因而他在復雜的時刻不可避免地轉向了現實主義。“現世界”、現實因素,統治者的昏聵、人民處境的悲慘、物價的飛漲、道德的淪喪涌入他的詩歌。
他拋棄了文人孤高自許、風花雪月的傳統,拿來了另一傳統——感時憂國,流露出深重的憂患意識,他眼里的世界是千瘡百孔、山河寥落的。他更多地采取了針砭和諷刺的態度、方式。“哦!報紙/你印刷的目的/只為替‘梅毒救星’‘淋病圣藥’/以及‘儻言偉論’做廣告的么?”(《報紙》),“黑色的霉菌/黑色的統治/你擴大,傳播,散步/世界六分之五的土地上/都有種子……”(《黑色的詛咒》)在這種善與惡、光明與黑暗高度二元對立的認識世界里,詩人直視罪惡和黑暗,卻單方面地采取了諷刺的態度,以極端不屑的口吻譏刺甚至詛咒壞的一方,因而也經常流于概念化、口號化的境地,有時直接采用政治抒情詩的模式。給人感覺是他有太多的憤怒卻展示不出來,有時甚至流于偏狹,例如對以“舞廳”“電影院”“霓虹燈”為表征的都市現代性的極端排斥,欲除之而后快,或者完全閉上眼睛。這里流露出左翼詩人“禁欲”的一面。而“都市景觀”“現代感覺”正是他們這一代詩人在三十年代前期、青年時代苦苦追尋的。這里就弱化了對“現代”的展示,沒有上升到細致描摹、高度反諷,深刻拷問的層面,顯得太過簡單,因而也影響了現實諷諭所可能達到的深廣度。這是非常遺憾的。
綜合觀之,李白鳳在現代主義方興未艾的特殊時刻登上了詩壇,他沒能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主義詩人,隨后,他轉向了浪漫主義氣味十足的書寫,繼續自我想象、欲望宣泄,四十年代又倒向了現實主義,傳達自己對政治、社會問題的義憤,對現代性的焦慮。他在“個人”“時代”“現實”“想象”等因素構成的多邊關系中展開詩歌寫作,展開對自己詩意世界的建構。他建構出來的詩意世界顯得駁雜而破碎,他接近然而并未抵達現代主義的真境界,在浪漫主義一途頗有建樹,有時候也能保持與現實的緊密摩擦狀態,但是他未能長成真正的大詩人,他仍然是未完成的。他沒能提供宏大而完整的詩意符號體系,在任何一方面都有些半途而廢,以至于很難從風格學的角度對他進行整體性的概括和描述。這和很多中國現代詩人的情況是相似的,我曾在嘗試評價聞一多新詩貢獻的文章中說“在新詩史上,幾乎沒有一個詩人的藝術生命不是過早枯萎的,郭沫若、艾青、穆旦……”[10]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肯定是多重的。也許,新詩要誕生像葉芝、T.S.艾略特、李白、杜甫這樣完整的大詩人,還需要時間的積淀。
(作者單位:嶺南師范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南方詩歌研究中心)
注 釋
①朱英誕:《梅花依舊——朱英誕自傳》,《新詩講稿》,廢名、朱英誕著,陳均編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07頁。
②劉朱櫻:《憶李白鳳》,《新文學史料》,1992年第1期。
③參看于玲《李白鳳年表簡編》,《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13年第1期。
④ M.H.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酈稚牛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5頁。
⑤聞一多:《〈女神〉之時代精神》,《聞一多全集 文藝評論 散文雜文2》,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111頁。
⑥ 廢名:《廢名1946年回北平后續寫的談新詩文章》,《新詩講稿》,廢名、朱英誕著,陳均編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45頁。
⑦朱英誕:《1940-1941年北大講稿》,《新詩講稿》,廢名、朱英誕著,陳均編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291頁。
⑧詹明信:《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文藝研究》,1986年第3期。
⑨陸耀東:《中國新詩史1916-1949第三卷》,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417頁。
⑩程繼龍:《聞一多新詩實踐得失芻議》,《打開詩的果殼》,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