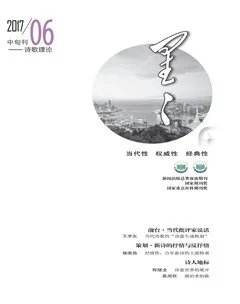困頓詩學:沉悶與警醒
一、網絡時代的理性與希望原理
如果我們曾經對古典的意象美學反復膜拜,并至今依然瞻仰其不朽的風采;如果我們曾經以抒情言志為詩之首要功能,以“無邪”為詩之精神,以歌為詩之韻律,那么,在當代,或者從后現代主義美學誕生以來,詩之功能,之精神,之韻律,之何為詩學,恐怕都要進行重新定義。但有一點顯然不會改變,那就是,詩歌,作為一門語言之藝術——這一特性是讓我們對詩保持欣賞,甚至保持迷戀,保持不能放棄這樣一門技藝之姿態——之最關鍵的理由。然而,在我們的“認同規律”中,必然還會帶出一種傳統的態度,一種數千年的詩詞演變所授予我們的對于詩的基本概念和品質的認知。無疑,這一特性也使得“詩之傳統”有效地構成當下詩學之不可或缺的材料,使得被否定,被淘汰的詩寫方式以后備的身份得以適時地重新進入詩行。某種程度上,我幾乎不反對任何一種形式,但是,毫無疑問,如果詩歌的語言,不足以引起新的體驗,那么,就像其他藝術不引起任何感觸,將面臨讀者的兩種態度:要么無視,要么無法容忍這種純屬浪費資源和時間的形式。在當前,網絡的巨大的信息量正在引起人類史無前例的集體焦慮癥,如果文學創作只打算在這巨大的信息流中再增加一些流量,那么它就只能加劇我們的焦慮。有鑒于此,我同樣認為,當前的閱讀是一種比以往更艱辛的閱讀,平庸的作品是對我們生命時間的侵略,因此,不能規避平庸的我們,或者在不得不從大量的平凡中找到那一“卓越的存在”的現實中——如何節省時間,將是關于閱讀本身之方法的問題,也是生命本身對于世界所加諸其上的形式和內容的處理方式之關鍵。然而,在閱讀的相對面,寫作本身卻成了作者閱讀世界的方式,在語音技術還未加入到網絡世界之時,整個英特網世界是一個以寫作替代言語的地方,這個充滿語言符號的地方,催生了網絡文學——何為網絡文學?它無疑首先是一種試圖打破正統文學之種種“主義”的寫作形式,是一種本著不拘泥于任何意義或無意義寫作的精神之寫作,但正因為如此,它又是可以不講究創新而只進行“高仿”的寫作,同時它最顯著的特征,無疑是對故事本身的傳奇性的側重——越傳奇,則越引人注目。網絡文學對于傳統的文學起到了何種影響,這幾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們不妨指出:它實在地拓展了文學的想象力,它迫使正統文學藝術作為一向注重創新精神的領域,去構建一種新的語言美學,去創造一種新的敘述方式——或者,它并非一種“被迫”,而是自然而然地在網絡的天馬行空的精神模式下產生的一種語言自身的運動變化。我們的散文詩無疑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產生了超越傳統新詩和傳統散文詩的語構性質變。不過,在網絡環境中,最大的一種語言勢態卻是“否定”與“批判”——它是網絡匿名時代之精神放縱本身的反映,也是信息本身的壓力下,精神的自我防衛形式。
在這樣的趨勢中,保持理性是一種理性的進展,而無批判,無否定的形式卻除了“嚴肅的褒獎”和“浮華的褒獎”之外,還存在一種形式,這一與當前一般語言勢態保持一定距離的形式——它存在于哪些文本中,具體指什么,源起于什么,其統計和追溯也許是繁瑣的,但是,十分有幸地,筆者從詩人伍榮祥最新出版的詩集中讀到了這一“存在”,并在其中找到了一些線索,得以大致地勾勒出這一形式的輪廓——它無疑是一種獨立的存在,甚至帶有些許封閉的屬性。在這個充滿語言攻擊的網絡時代,影射、諷刺、嘲弄、預言和寓言代表了當前世界的主要態度,每個人都在巨量的信息中養成了一種鳥瞰世界的自負與自信,同時又作為信息的反射儀器而進化成了“刺猬”式的生物。相比之下,伍榮祥卻采取了向內自觀,他在詩中演繹著自我的彷徨和迷茫,演繹著一種“懸浮”和“下沉”,演繹著時空中的每一個瞬間的狀態——一種既不能預言前方,也不能總結來路的“懸著”狀態——他既不把這種狀態歸咎于世界,也不把它歸咎于自身的歷史,一種細致、具體的當下,在詩人看來,似乎并不能輕易地把某種理由加諸其上,他選擇了純粹的“狀態自述”,并因此而體現了客觀。這或許又是一種“遺世獨立”——在這個獨立的世界中,幾乎是完全脫離了“網絡屬性”,有意地割斷了與外部的千絲萬縷的關系,從而又仿佛是一種“獨自承擔”:沒有嘲弄,沒有埋怨,甚至也不自責。——伍榮祥幾乎使所有的動詞都失去了明確的對象,或者,雖然發出了行動,但這種行動并不明確自身最終的著落處,對象只是臨時的對象,不代表任何可以鄭重表述的意義:“這是真的。有時,我想用手中的刀子在房頂的天空和檐下的墻壁上深深地劃上一條口子,尤其雙臂噼啪地著響的時候。無可諱言,當夜的燭光在我的窗欞重新照亮,我就想讓我這把生銹而不帶血的刀子在一些不是生命的東西上用力劃上幾下,讓我細心看一看這些堅硬或柔軟的東西的腸和胃,還有那顆視而不見又隱隱跳動的桃形心臟。”(《檐下之音》第4節,《伍榮祥詩選》,四川民族出版社2016,第66頁)——讀伍榮祥的詩給人一種感覺,“刀子”(在整部詩集中,它至少出現了三次)是一種必要的出場,盡管“刀子”本身或許是尖銳的,但它幾乎是他“無批判”空間中唯一的一種突圍形式——這種形而上的尖銳,被如此誠實地命名為“刀子”,假如我們是尼采,抑或是波德萊爾,我們一定會為之同樣振奮,因為在如此眾多的隱忍的詩行中,它恰恰代表著一種飛翔,一種仿佛是在鎩羽而歸的灰色中重新崛起于天宇的閃電,它是沖破層層包圍,希圖重獲自由的靈魂自身的一種具象化。然而——即便如此,詩人卻強調這是一把“生銹的”刀。這種對破壞性的、損害性的有意識的減弱或規避,強調了“非截然的對立”,并且使得對象的屬性變得模糊,甚至傾向于消解。正因為如此,它十分接近于一種“希望原理”——恩斯特.布洛克指出:“我們關于傷害的夢的稀缺,不是變得更少,而是變得更多。它因此防止我們習慣于損失。所有傷害我們、壓迫我們,使我們衰弱的東西都將隨時光流逝。”【見恩斯特.布洛克:《希望原理》(The Principle of Hope),馬塞諸塞:劍橋大學MIT出版社1986,第451頁】伍榮祥對夢的態度正好是這一原理的注腳:“深夜,夢中有人放火!人打哈欠,駿馬跨不過柵欄,終日徘徊在秘密的山崗遠離風景。/有歸有宿,鳥兒應該回巢;蟲兒應該在藻草或巖縫中安閑。噢!祈禱無言,季節來自偶然。”(《入秋殘夢》,《伍榮祥詩選》,第56頁)——人們常常遺忘夢中生動的戲劇場景,對于這一現象,與其說,在夢中,人們試圖突圍,在清醒時,人們卻選擇了退守與忍耐;毋寧說,人們更多地以無視傷害來避免更多的傷害——這是否屬于妥協?——布洛克的《希望原理》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正在于回答這一問題:如果這看上去是一種妥協,那么,它的更普遍、更本質的心理動機卻是“希望”本身。按照希望的這一原則,伍榮祥的規避或避免針鋒相對,就成為一種積極的原則——正如布洛克又認為“希望之量遠比信仰、私生活日常來得更大”。但是,在常規化的閱讀中,或者在現象的表層上,我們畢竟只會從上述詩句中看到一種無意識的宣泄,甚至,在弗洛伊德心理學的角度上,我們還會把它視為一種壓抑下的行為。這種解讀,常常是我們自身對某種危險的警覺性的反應,因此,這樣的理解更應當被視為我們對自身的解釋。顯然,當詩歌試圖陳述某種隱秘的東西,它恰恰體現了理性的審視,并且是理性發現的結果。所以——恰恰不是在明顯的否定性意象中,而是在修飾性的內容中,才體現了理性對于對象的把握與節制的表達。同樣地,我們的閱讀,如果只對顯在的意象產生敏感性,那么,閱讀本身也還不在理性自身的程度上。
二、困頓詩學:緘默與尊重之春秋筆法,以及它與古典理性的比較
毋庸諱言,閱讀的快感常常來自那些對我們更具刺激性的意象,所以快感常常是疼痛,是黑夜,是毀滅,恰恰不是日神意志下的那種陽光普照。這種源自感官本身的特性使得詩歌同樣不免要關注這些快感的源頭。但伍榮祥更擅長處理那些沒有快感的細節——它是一種霧中穿行的狀態,它是一種不能擺脫某種狀態的困頓。伍榮祥常常警覺于這種困頓的包圍,并通過這一警覺,恰當地給予那些無刺激的意象以某種程度的凌厲,冷峻。但是,由于他對“無批判”的選擇,他的冷峻與凌厲顯然是亞于冷峻和凌厲本身的:“其實,我愿意拱手與你作別。這是真的,而許多日子我們都在霧中穿行,雖然前方的路途時時有一縷陽光在引領。”“可是,我們常常像一匹瘦弱的黑馬,除了疾走還是疾走,整日在一個沒有終點的路上不停地追趕。/不停地追趕。我們困頓無比,并且被時間消隱在黑夜。”(《當彩云被遮掩時》,《伍榮祥詩選》,第108-109頁)“樹梢之上,我仿佛看見一粒雪花在俯視我。/困頓無比。瞬間我內心的一千只鳥停止了飛翔。”(見《雪花吟》第5節,《伍榮祥詩選》,第106頁)——不妨如此認為:詩中的伍榮祥是一種高度自制和收斂的符號本身的解釋學,這個符號向內凝壓成自我的一種質量,一種不散發,不招展的姿勢:“不想驚動,只想以一只手/用一句古老的語言輕輕呼喊/或者,在雨季/以一種寧靜與你擦臂而過/然后,傾聽雨的聲音,并且在霏霏的路上怔怔一眄。”(《傘下之物》,《伍榮祥詩選》,第76頁)——正是這種無聲與緘默,這種類似不蔓不枝的姿勢,作為一種內在屬性之外現,在建構著一種城堡式的“困頓”:內部充滿驚悸與華麗的樂章,充滿靈魂的輕疾靈敏的翔舞,而外部卻沉默、莊嚴——這種保守的“城堡”景觀,與其說是“困頓”的具象,毋寧說,它是一種以“困頓”本身命名的詩學——困頓詩學,要表達的是一種軀體或物質對精神的圍困。究竟是什么讓我們緘默,是什么讓我們避諱?又是什么讓我們失去方向,舉步唯艱?詩人并未向我們提問,但是他卻一再強調著“緘默”與“困頓”,這種緘默與困頓,在真實的緘默與困頓中,又在兩者之外,或者說——詩中所表達的兩者,其實是一種規避,和拒絕開放,正如筆者在前文所說:伍榮祥所選擇的是“無批判”——如果不批判,不斗爭,就只能選擇緘默。然而它又并非真正的緘默——詩人在不停地言說,在某種方式里尋找突圍的缺口,但它又完全不同于修辭學對事實的隱諱曲折的敘述,相反,它在修辭本身的生動之外,在一種形而上的此在與彼岸的相對性中,以“一種呈現”遙遙地鑒照著“另一種現實”:“蟋蟀在悄悄低吟。這時,一種預感油然沿著檐下窗欞來回踱步,還圍著墻面驚詫地繞了幾個大圈。/雞鳴,三更已過。/煢煢孑立,此院無路可尋。”(《宅內之事》,《伍榮祥詩選》,第53頁)——誠然,依然存有修辭,但不是事件本體的修辭,而是概念本身的抽象在具體的、特殊的形式里獲得了對現實的某種透露的權利。——然而,這還遠遠不是事件本身,它依然是緘默的,依然在困頓自身的表述中。
無疑,困頓詩學,本身正通過這樣的“緘默”方式,在進行著它自身獨有的批判。這類似烏托邦形式對于現實的否定,但更類似慈善行為對于現實的既支持又否定的意義呈現——但詩人顯然不是慈善家,比起慈善,其實他更接近于堅持和平,反對戰爭的潛在的改革派——他期待著改革,而不是期待著起義;他敏感于外部世界的變化,但并不贊同激進的破壞式的運動,因此,在詩人的敘述中,詩行的最后總是歸于一種出奇的平靜或者啞默,或者有著懸置傾向的疑問(一種在問題本身中預設無法解答的提問方式)——這種起伏,又總是通過精神自身從內部的一番驚心動魄的風景回歸到闃寂的過程來體現:“這時,琴樣的實物勃然在桌上跳躍起來,睽睽地眼里射出兩束刺目的綠光,飛濺的光點將墻面碰得噼啪作響,還揮動一雙無形的臂仿佛在昭示著什么。/月色在驚恐時褪去,桌上的實物逐漸平靜如初。”(《極處風景》,《伍榮祥詩選》,第39頁)“噢,鴉鳥掠過森林,心事在白雪中踽踽行走,然而我的柳河終于被冬季全部侵占。/大雪封天,爐火曛黑眼眸。/我的天空是內心,宇宙的天空是什么?”(《檐下讖語》,《伍榮祥詩選》,第37頁)
靳曉靜女士在《大自然的合掌祈禱聲——讀伍榮祥的詩歌》一文中,敏銳地指出:“對大自然,詩人很少俯瞰,像‘黃河之水天上來’這樣的大視角,他絕少采用。他是從自己的環境去察看自然的……他的這種小視角很有個性……能喚起人們的相似經驗從而產生親切感。”——不難看出,“很少俯瞰”同樣是困頓詩學的一種表現方式,正因為“很少俯瞰”,詩歌才自動形成了一種低處的“困頓”。然而,這實在是詩歌中最難守的一塊美學陣地——在眾多自負、任性、飛揚的意緒中表達著一種生動的、挑釁的、反叛的、妖嬈或嫵媚的情感之精靈的詩作中,伍榮祥的敘述與抒情,既不打算以恣意的情感流光溢彩,也不打算以悲憫之態俯瞰眾生,更不企圖以超脫世外的清醒來睥睨眾生,他老實地守在大地之上,以最樸素的姿態,講述著這種幾乎是人人皆有的源自物質世界的客觀的困頓。相對于烏托邦話語在其彼岸世界的游弋、修辭學在修辭中為人類打開的無窮可能性和某種被稱為“任性的詩學”對情緒和情感的放縱,伍榮祥的“困頓詩學”恰恰在某種意義上體現了“最現實主義”。而節制和隱忍作為“困頓詩學”中最突出的形態,常常又成為“尊重客體”“維護客體”的一種態度和體現。——不得不說,文學本身是節制的,它本質上體現了一種文明的尺度,一種語言自身的風度和禮儀,但是,這還僅僅是一種文學的基本要求,表現為個體寫作特征的節制,是比基本要求更顯著的一種禮儀,比如,伍榮祥對于諷刺和批判的規避,無論從外現形式和內部根源來說,都遠比諷刺和批判本身的否定性更直觀地顯示為“尊重對象”,這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近似于春秋筆法,例如伍榮祥寫災難,既不試圖再現悲慘的命運現場,以現成的悲劇復制氛圍膚淺地感染讀者,也不試圖尋找人類命運的根源,或以叔本華式的清醒來反映世界對人而言的“無可期待”,換言之,他從不悲天憫人,也不沉痛絕望,但這又并不代表詩人絲毫沒有悲憫,沒有沉痛——他的顯而易見的克制恰恰揭示了所克制的對象的存在:“噩耗傳來,去年親人逝世的事情確實難以置信,至今仍兩袖掩面,以一種沉重的感覺動步。/雙掌擎燈,紅云斜掛房檐。/孤獨碰響黑夜!/仲夏,藥物已經無效。”(《域外之音》,《伍榮祥詩集》,第59頁)——詩人把噩耗引起的悲痛和打擊——這種本該是生動具體的感性活動展開的權利,禪讓給了理性的懷疑和探究,把痛哭呼號的自然生命的情感行為轉讓給了幾乎婉約的“兩袖掩面”——我們在古典文獻中或者曾經邂逅過類似的語言形式,不過,這并非重點——重點是,伍榮祥的隱忍實際上正是古典理性的某種恢復,然而,這也不是單純的“古典復興”——如果說民族獨立與解放斗爭使得整個世界的步伐朝著一種精神自身的“外向化”行進,也即朝著大膽、直白,而不是含蓄、內斂的方向前進,那么,在藝術的表現方式方面,現代性的抽象化發展形式中,卻既包含著內部的外在化,又在抽象本身中體現著隱晦和含蓄。這就是說,伍榮祥的節制與隱忍既有著古典性的再現,同時又有著現代抽象化的表述屬性。然而“困頓詩學”決不是一種古典的完美主義,也非純粹的抽象,恰恰相反,它是不足和局促,并有著困頓的具體形式;但又不僅僅如此,如果古希臘完美的雕像在它自身的圓滿中昭示著日神式的光明前景,那么,在伍榮祥的“刻意的撫平”中,在某種“化激烈之沖突為空茫之無”的宗教式的退守中,卻是表層修復的平滑——作為同樣看上去無毀損的外觀(古典式的完美理念之顯現,區別于古代社會從精神到外觀的完美主義實踐),在包圍著內部的矛盾。無疑矛盾需要尋找它自身的解決途徑,但表層的平滑,卻封住了它的出口——這是困頓詩學本身的呈現,很顯然,這種“困頓”的表達,恰恰又在同一時間構成了對困頓自身的舒緩和解放,換言之,表達本身正是解放困頓的缺口。后者,事實上,又是困頓詩學對其自身的產生和存在之原因的最根本的說明。就抽象而言,“困頓”完全以另一種形式的困頓言說著現實的困頓,乃是徹底的抽象;但就“另一種形式”本身試圖影射現實的困頓的具體方式而言,卻又是具象的。
三、困頓詩學與散文詩的關系,及其與傳統詩學的區別
但我們又要把伍榮祥的困頓詩學與小說和詩歌傳統中常用的修辭“影射”,與“隱喻”,嚴格區分開來。這實際上是一種在散文詩這一體裁中才能應用的詩學——為何這么說?這就不得不對這些文體的特征作一個簡要的說明:散文詩是一種對瞬間的、流動的情緒、情感的抓捕形式,而小說以及傳統的詩歌,更傾向于對階段性的生存現實,或具體的事件(有時間始終,有地點)進行藝術化敘述和抒情。換言之,后者的對象相對是確定的,而散文詩的對象更具有不確定性,有時甚至只是抽象的,可能的存在形式。也因此,散文詩更傾向于內在圖景的表述與抒發(也即我稱之為“第三種心理現實主義”或“第三空間的現實主義書寫”)。——正因為如此,困頓本身就既包含著階段性的被困,和瞬間的情緒、情感的圍困。無疑,這樣的困頓事實上既是短暫的,又是常態的。它代表著我們日常中停頓,也象征著我們的生活本身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無論在何時何地,總是體現為非連續的狀態。它既是被迫停頓,也是我們自身在反思和自省中,或在思慮的間歇性空白中表現的暫停形式。然而——把這種形式視為困頓,并加以表述,卻是對表象世界的充實——它連接了純粹的私人領域與公共地帶,構成了整體的真實的連續性,并同樣試圖揭示現象背后的本質,乃至揭示人類之共同命運。
事實上,在一切歷史社會,困頓正是“禁忌”的同義詞,人類無疑始終受到各種禁忌的包圍,正如在無明顯禁忌的地方,所謂的自由和開放同樣在原則和規定的保駕護航下才能展現它的模式。因此,困頓事實地構成了一種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環境下的生存之主要狀態。強調困頓,則揭示了突圍的必須——它是突圍的前兆或預備狀態,同時,它顯然也是自由或破繭的潛臺詞。
然而,在另一個角度上,個人的困頓并非總是與公共禁忌一致,個體的禁忌無疑更為具體、瑣碎。有時,甚至表現為公共禁忌的對立面。而這恰恰為困頓詩學提供了藝術的個性化契機。伍榮祥關于禁忌的闡釋,無疑同時包括了可理解的公共禁忌范疇,和無可奉告的某種純私化的禁忌——后者也可以說是對前者的一種深化形式,例如在《孤旅手記》中,他曾寫道:“一千年只一句話。/晌午,街道已經染紅,躁動也在河心泛起了水花。/或許,神秘的的預言不止一句。”(《孤旅手記》,第204頁)——這種諱莫如深的表達,正是純私化的禁忌,但它與其他規避時代大主題和社會重要內容的純私化表述又有著本質的區別——后者的領域有著它自身的自由,即恰恰不是表達圍困,而是相對純粹的自我釋放;前者則不然,讀者并不能從中窺視到任何關于禁忌的具體內容,它更是沉默的有聲化表述,并在這一“特殊的沉默”中,恰恰使得禁忌本身的意圖變得更為強烈。這種方式,幾乎反襯出意象主義、象征主義或者隱喻等傳統手法上之表述的高度透明,但恰恰又是這種透明,反襯出了困頓詩學的“保護主義”——正如弗洛伊德常常從文學藝術中試圖洞察人類精神的反常——他所指出的病態的精神常常意味著對社會本身的反常,乃至反動——顯然,只有相對的透明,才能為這種心理學的臆測提供材料,而伍榮祥的“保護主義”恰恰有某種讓心理學診所趨向關門大吉之虞,同時,它也實在地保護了某個不可知的對象(當然,這還遠遠不是犯罪心理學范圍的對象),它甚至保護了讀者,使后者免于從象征和隱喻的能指對象集合中受到中傷——這種牧師式的保護主義,相對眼下口誅筆伐,宣泄和充滿非理性的批判之網絡世界,它無疑是一種可貴的自律,一種批判的延遲,一種做出行動前的理性自身的停頓。它使現代世界人與人之間那層脆弱的關系不再進一步薄弱和斷裂,使得普遍的信任危機得到了延緩,使存在本身,尤其是單薄的個體存在作為整體的構成因素得以重建整體的自信。因此困頓詩學也可視為現成世界價值體系內部的一種常規的事務處理方式——即在已知條件和已知價值目標的情況下,如何尋找一種不損害體系又能完成目標的類似數學命題推演的方式。如果量化的批判與否定,并不能真正地提供一種更進步的實踐和解決的方案,或有效地促進人類福祉,那么,“困頓”雖然有保守之虞,卻相對成為詩學自身對時代的慎重的建議和擔當。同時,在詩歌的本體論角度上,它無疑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話語方式,而鑒于它本身又是一個普遍的社會命題,因此可望發展成一種代表性的時代書寫形式和新美學——這是一種詩歌流派的前景,毫無疑問,每個時代都有它自身的不足,這種不足是困頓的前提,也是困頓的不同時代之內容,因此,它不僅是永恒的命題,也是不得不面對的命題。而伍榮祥的意義則在于——他首先通過量化的特征化書寫為我們建構了關于這一命題的形式和范疇,并明確地指出了它的名稱。其次,他引起我們對困頓及困頓之源頭的思考,他的文本中顯示的“停頓”,不是其他詩歌文本中顯示的繼現實之后的“繼續現實地戰斗”,而是“現實的停頓”——作為一種可見的寫作經驗,它啟示我們困頓本身就是一種豐富的礦源,不僅是文本開拓意義上的,也是社會問題本身所包含的某種財富形式的提示。最后,他以抽象派繪畫的形式,利用自然意象作為具體的心靈圖景描述(與古典的寓情于景有相似性,亦有本質的不同,在古典的意境原理中,情景盡管是交融的,但風景仍然保有其作為外在的真實現象的身份,而不單方面地僅僅作為心靈的象征;在伍榮祥的詩中,景致亦真亦幻,它更傾向于主觀心靈話語自身的物化呈現)為我們揭示了困頓所內含的主動與被動兩種線索——其一是瞬間心靈圖景的象形化對困頓的能指功能;其二則是困頓對于具體個體的形態塑造——這是兩條剛好呈反向的線索,前者由內向外,后者由外向內;前者在發現的主動性里使困頓成為主動的調節方式和態度;后者在被塑造的方向上,以內部的的困頓暗示著外部的困頓——構造內部困頓的外部形式,無疑本身就包含著困頓的屬性。根本上,外部的圍困是外部自身突圍的方式,就像特洛依戰爭中,希臘人圍攻特洛依只是為希臘人解圍,以便重新挽回某種榮譽。
四、庭院文化以及其他歷史文化現象對“困頓詩學”的注解
在此意義上,《孤旅手記》作為一種孤獨旅行者的心路,它之強調“形單只影”就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尼采的另類解釋。當尼采在《重估一切價值》中,宣布舊的價值體系應當作廢時,尼采恰恰被自身的體系所圍困,并因自絕于舊的價值體系,成為孤島之人。但是這種孤島形態,在尼采生前并不彰顯,斗爭中的尼采無疑是世界中較為活躍的一分子,直到尼采告別世界之后很久,世界才發現了這樣一座孤島,并產生了一股解釋尼采的潮流——這種解釋,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對尼采的解放。毋庸置疑,正是人們對孤島的一種普遍的共鳴(就像對“魯冰遜”的共鳴,一種在被放逐的孤獨中所產生的既自由又恐慌的心靈共振,它是理想和絕望雙重幻象——孤島無疑是令我們自由呼吸和飛翔的時空,也是心靈無助的象征),在促使尼采最終被解放。對于尼采自身而言,希望獲得世界的認同遠勝于承認自己是一座孤島,因此,尼采的自覺形式顯然不是一種困頓的形式,而是試圖突圍的形式,而突圍就意味著主動攻擊,這種斗爭在勢力不均的情況下,絕對的少數恰恰將被圍困。正如王爾德的唯美主義同樣遭到現實的圍困一樣。這種歷史的個人境遇,揭示了個性化的創造或者激進的思想,在立刻融入集體的意愿和自覺遠離之間命運差異似乎只取決于時間本身。而困頓詩學的誕生恰恰是在對時間的這一屬性的洞察之下顯示了必然性。當然,我們并不主張這里或那里,總是存在著一種斗爭哲學。這又恰恰說明,斗爭本身是被大多數人所避諱的,尤其是在儒家文化之“仁”“和”主義浸潤下的中國,對和平的趨同無疑更勝于對斗爭的需求,事實上,和平本身在我們看來正是道德的正義(顯然,并非任何民族都如此)。這樣的觀念和認識背景從根本上解釋了錢鐘書的《圍城》之所以受到本國讀者廣泛關注的原因:圍城正是普遍的命運,它是現存價值體系對個體的圍困,也是拒絕斗爭所造成的圍困。不過,《圍城》是宏觀視野中的某個明確的單一主題的闡釋,即主要是針對婚姻關系而論,這顯然是一個更為通俗化、社會化的命題。伍榮祥的困頓詩學卻是微觀環境中的一種不明確的困頓話語,即它是時光中的每個短暫瞬間的一種困頓的感悟,它以不清晰來揭示困頓本身,以“顧左右而言它”的方式來強調另一端的某個事實的存在——這是一種金蟬脫殼式的“困頓”,也是高度形而上的困頓,它的非通俗構成了困頓詩學的內部質量,甚至,構成了對圍困本身的道德評價的懸置,這就同樣體現了一種“和”的文化要旨。它意味著,困頓作為一種“和”形式,根本任務不在于揭示困頓,而在于化解困頓。當然,化解本身對詩人自身來說,并非是十分明確的任務,但困頓詩學卻作為“和”形式的演化,無疑在文化自身的傳統中,代表著民族精神如何與新的時代審美形式和藝術觀念達成一致,并向其簽署通行證以示表彰的途徑。
在伍榮祥已出版的詩集中,《院中看云》和《檐下疏影》,無疑也都在書名自身的直觀中體現了一種“孤旅”形式。這種把自身置于方寸之地,似乎有意要與外部世界隔離開來的“自約”,始終體現了靳曉靜所說的“很少俯瞰”或很少采用“大視角”。這樣的視角,與其說是閑情,毋寧說是謙和。更恰當地說,它實際上是一種相當悠久的傳統,一種與宋詞有著淵源的詩風——宋詞固然不乏豪放、開闊的情境,但更多的卻是一種庭院文化抒情,這種庭院文化向外延伸,便成為別致的野外小景的景觀史。但后者本質上又與園林景致相類,因此依然屬于庭院文化的范疇。但宋詞的這種庭院地理文化與城市的繁榮和人民的安居樂業有很大關系,這種安于一隅的生存形態,即便在南宋政府流亡期間,依然影響著宋詞的基本格局,這一顯著的“向內而安”,昭示著南宋最終被迫打開大門,接受外族統治的命運。伍榮祥的“向內而安”當然不能與南宋同日而語——詩人自覺到這是一種“困頓”,與南宋詞人的不自覺有著本質的不同,更何況構成困頓的內部材料也完全不同,因此,伍榮祥的庭院抒情更多的意義在于詩學自身建構與發展方式:他無疑發現了宋詞與散文詩在外形和意境上的類似,盡管我們不能武斷地認為伍榮祥在有意識地運用宋詞內核演化散文詩,卻不能否認,即便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其精神與宋詞一脈相承的事實。只不過,宋詞本身與古詩和近體詩一樣,風景多為原本就存在的外部客體,而不是內部意識的外化。其次,伍榮祥的散文詩強調著一種簡約,而不主張無節制地敘述和抒情,這又是一種傳統的中國詩學精神的繼承。在古典的收斂與現代的開放之間,伍榮祥無疑有著他自身的尺度,作為一名有著豐富的美術創作經驗的詩人,他更懂得意象與空間,詩意與節制之間的關系。這種美術經驗使他在繼承傳統之簡約這方面幾乎毫無困難和猶豫,如果我們要拿他與其他散文詩人比較,那么,在對古典的意境與簡約的繼承這一面來說,他無疑與散文詩家耿林莽更為接近。但是,伍榮祥又是多元化的,他的內在化的圖景屬于后現代(包含著解構主義以降的那種無結構、無中心的特征)甚至屬于意識流;他在九十年代創作的抒情散文詩,更具有早期散文詩的普遍特征——散文化;同時,他也受到波德萊爾的影響,試圖在他自身的庭院之外,在古典的大自然抒情形式之外,展示一種宗教與罪孽,女人與命運,以及生死存亡相關的激烈的矛盾沖突與人類終極話語審美圖景。然而這種試圖從庭院中突圍的圖景,卻是從西方繪畫中借鑒過來的——這本身說明伍榮祥骨子里是一種純中國文化符號,卻又并不失去在“去中國化”的形式中去創造和建構其詩生活、借以反映開放與審美能力的活力。
——伍榮祥的這種多元屬性,同樣在某種意義上解釋了困頓詩學所包含的方式與范疇。究其實,困頓存在于每一種既成形式中,只是我們并不承認那是一種困頓罷了。比起我們在困頓中手舞足蹈,意氣風發,比起我們善于建立自己的規則,并以規則為正義,伍榮祥卻坦然承認困頓,這與其說是一種妥協,不如說是一種警醒:我們都被好的、壞的規則包圍著,沒有人能逃避規則,尤其是自身的規則。這意味著困頓恰恰是一種適應規則的形態和過程,是生命自然進化意義上的詩學,它更誠實地體現著生命,并因此無可避免地改造著生命,推動著生命,直到生命獲得它自身的意義。也因此,承認困頓,雖然有沉悶之虞,卻恰恰是一種醒著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