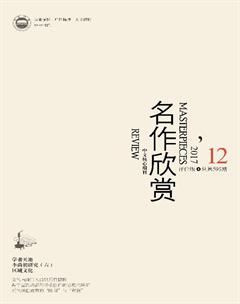寂寞飄零赤子情
摘 要:蘇軾一生宦途坎坷,輾轉飄零,從1071年自請外放到1101年死于歸途,從鋒芒畢露、豪放灑脫到云淡風輕、超逸曠然,蘇軾用三十年時間體味世間冷暖,用畢生的赤誠來抒發內心所感。本文將分析蘇軾初入詞壇的率性之作《醉落魄·離京口作》與其人生盡頭的清曠之詩《汲江煎茶》,來管窺東坡顛沛流離境況下融入生命的“赤子之情”。
關鍵詞:蘇軾 《醉落魄·離京口作》 《汲江煎茶》 赤子之情
三十載宦海浮沉,三十年倏然一瞬。葉落未歸根,飄零無依存。東坡人生的后三十年,用顛沛流離的行跡續寫著孑然一身的孤寂,借皎皎明月與濯濯清酒澆心中塊壘。無論是飄零伊始的率性而為,還是生命盡頭的曠然超逸,無論是呼朋引伴的狂歡,還是形影相吊的獨酌,蘇子從未忘乎本心,詞句之間無不體現其至真至純之心。
1071年,反對新政的蘇軾自請外放杭州,在這吳儂軟語之地,潛移默化之中也開始了詞的創作。在他留存于世的作品中,有時間可考的最早詞作便是作于1073年的三首《醉落魄》了。《醉落魄》源于唐教坊曲《一斛珠》,在締造之初便奠定了凄苦落寞的情感基調,流傳至宋經過文人的別創,使其進一步典雅精致,文人化情味更濃。本文分析的這首《醉落魄·離京口作》作于熙寧六年(1073)冬,當時蘇軾在杭州任滿三年,要遷任密州太守,于離開京口時寫下此篇。引人注目的是使用頻率并不高的詞牌名《醉落魄》,蘇軾一生共作過四首,有時間可考的三首均創作于同一年。想必當年的蘇軾時值中年卻遭遇一貶再貶,只能以酒為伴排遣心中煩悶。那因失意而酒醉,因酒醉而更見落魄的心境由詞牌名亦可見一斑。
醉落魄
離京口作
輕云微月,二更酒醒船初發。孤城回望蒼煙合。記得歌時,不記歸時節。 巾偏扇墜藤床滑,覺來幽夢無人說。此生飄蕩何時歇?家在西南,長作東南別。①
上闋寫酒醒。云霧輕輕,月色微微,二更時分,詞人酒醒,船亦離岸。詞人從艙中回望,只見身后的那座孤城煙霧迷蒙。這一切仿佛是夢中的情景又似乎真實發生,只記得飲酒高歌卻不曾記得何時踏船歸來。開篇一句“輕云微月”霎時間將我們帶入朦朧的畫面之中,“云”和“月”是中國古代詩詞中常見的意象,無論是“山抹微云”②,還是“曉風殘月”③,都曾讓我們產生無數遐想,而這一句置于即將遠調之人的離別詞中,或許更有一種特殊的內涵。詞作中常以云的飄逸靈動比喻游子的漂泊流離;月則代表一種永恒的存在,成為文人懷歸思鄉的寄托。此處云與月連用,不僅是對現實情景的描摹,更是離別之思以及懷鄉之緒的表達。醉眼惺忪,目之所及不只是空中微亮月色下的輕云游走,還有云煙繚繞中佇立的孤城。詞人借著酒意回望這朦朧夜景,意識也漸漸模糊,“記得歌時,不記歸時節”,此處或許是醉態下記憶的缺失,亦或是借踏歌起舞之興去遮掩離別之悲吧。
下闋為詞人醉酒夢回的情形。他頭巾偏向一旁,扇子墜落于艙板之上,藤床光滑萬分,似乎連身體也無法固定。詞人記起來他方才做了一個夢,但天地之間,僅一葉扁舟托著他的軀體浮游于江海之上,親朋好友都已天各一方,又有誰人可以聽他訴說夢中的情形?這樣飄蕩不定的生活幾時才能結束?故鄉在西南眉山,作者卻要遠調到東南為官,歸心似箭卻越調越遠,可悲,可嘆。中國古代藝術審美追求傳神精切,而蘇詞中也不乏對現實情景的生動描摹。“巾偏扇墜藤床滑”,這短短七個字,就將詞人醉態酣睡的形象展現得栩栩如生。在多少個萬籟俱寂的夜晚,精神無依無靠的蘇軾只好與濁酒相伴,以月色為朋,而此時此刻“覺來幽夢無人說”的蘇軾留給我們的是一個滿懷孤寂的凄涼背影。這種孑然獨立的畫面在他《永遇樂》“寂寞無人見”④一句中也有體現,而在柳永的《雨霖鈴》也有過相似的說法:“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⑤或許這就是所謂的“堂皇轉眼凋零,喧騰是短命的別名”,相聚短暫,唯有孤獨才是永恒。縹緲的幻想沉積著真實的生活體驗,蘊含著切身的情感積淀。此處蘇軾雖未詳細講述夢中的情形,但“覺來”的“幽夢”將離鄉背井、四處飄零的生活帶給他的凄楚與悵然蘊藉而又生動地呈現出來。都說蘇軾豪放曠達,而我認為他悲切起來簡直教人淚下。且看,這一句午夜夢回道出的“巾偏扇墜藤床滑,覺來幽夢無人說”,豈不是硬生生地把傷疤揭給人看?千年以降,知其者又怎能不為之一慟?此時的蘇軾坦率得可愛又可憐,不顧及理性克制,更不管音律妥帖,只剩下“至真之情由性靈肺腑流出”⑥。他寂寞、悲切,厭煩了官場的蠅營狗茍,更厭倦了浮萍般的四處漂流,無人排憂的蘇軾只能對著天空,對著月亮嗟嘆:“此生飄蕩何時歇。家在西南,長作東南別。”然而他可曾料到,這才只是他一生飄蕩的開始。
如今,我們已知東坡的結局,回過頭來審視他坎坷的人生歷程,再讀《醉落魄》,便更多了一絲同情。從 1071年因與新派政見不和自請外放杭州到1101年遇赦北歸死于途中,整整三十年,他的足跡遍布東南沿海的十五個城市卻始終再未回到過自己的故鄉。念鄉心切,欲歸不能,從“此生飄蕩何時歇”到“四十七年真一夢,天涯流落淚橫斜”⑦,再到“飄零江海,身非己有,未知歸宿之地”⑧,從嗟問埋怨到感嘆人生如夢,再到認清血淋淋的現實,蘇軾的鋒芒不再,棱角也漸漸磨平,而他那少有的赤子之情也日漸含蓄。詩詞本身就長于表達細致微妙的情感,而蘇軾詞中這種細膩的情感更是觸處便生。
在他的詞作中,自問“吾歸何處”⑨,自稱“身如不系之舟”⑩。在當年三首《醉落魄》中均有思歸之情的直接體現,除了本篇的“家住西南,長作東南別”,還有“蒼頭華發,故山歸計何時決”{11}以及“西望峨眉,長羨歸飛鶴”{12}。蘇軾詞的結尾往往意境深遠,余味無窮,達到“辭意俱不盡”的藝術境界。正如本篇中“家在西南,長作東南別”,平淡的遣詞造句之中道出一聲悲苦無奈而又凄楚悠遠的呼喚,甚有天地之大卻“恨無人會”的悲愴,意味綿綿。蘇軾說過“此心安處是吾鄉”{13},可“安”是片刻,漂泊懸蕩才是他長久的狀態。
當我們回顧蘇東坡的人生際遇,當我們去懷想他所遭遇的風風雨雨,再回到那個冷落的月夜,蘇軾形影相吊,含著醉意袒露自己的性情是多么真誠而又可貴。當月與酒不期而遇,當酒與人完美融合,醉了的是歸鄉夢,碎了的是赤子情。之后的三十載宦海浮沉的歲月,于東坡而言寂寞早已成了習慣,飄零成為常態,超然曠達之風便成為絕望中盛開的花朵,但即便開始收束感性隱去鋒芒,他樂天自解的赤誠之情雖日漸含蓄蘊藉但始終不曾忘卻。
晚年的東坡或許是擺脫了情感困擾以及歸鄉執念,遣詞造句越發灑脫不羈,亦或是人生意境逾高,詞已無法表達其“率而成章,即興成詩”的高遠心境,東坡晚年詞呈衰退趨勢,文學創作轉向小品文和格律詩。且看他作于元符三年(1100)的這首《汲江煎茶》,當時的蘇軾正流放于海南儋州,據記載“此地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14},蘇軾亦稱“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15}。而恰恰是在這種幾近人生低谷的境遇中,蘇軾寫下了這首平淡空靈、清曠靜寂的佳作。楊萬里在他的《誠齋詩話》中毫不吝嗇地贊揚道:“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
汲江煎茶
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處腳,松風忽作瀉時聲。枯腸未易禁三碗,坐聽荒城長短更。{16}
首聯明確闡述了詩人的煎茶理論——煎一壺好茶需要水質良好且水流不竭的凈水和竹木炭的旺火,即詩人所言的“活水”和“活火”。而在偏僻的嶺南之地自然沒有鮮馥的清泉雨露,從而引出第二句詩人親臨江邊垂釣之處,就地取材汲水煎茶。楊萬里分析道:“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處取清者,二也;石下之水,非泥土,三也;石乃釣石,非尋常之石,四也;東坡自汲取,非遣卒奴,五也。”{17}值得注意的是,首句兩次用“活”字既表明煎一壺好茶對水質火候的精致要求,也巧妙地暗示了東坡深諳茶道,而第二句的“深清”筆者認為過于理性分析反而失去其本身的趣味,或許這里只是作者淡淡地講述其親尋江邊清澈之水的事實;亦或許給讀者描繪一幅清凈深邃的畫面去闡釋其隨欲自適就地尋材的豁達。
頷聯寫月夜取水,對仗工整,妙想奇絕。月夜之下,詩人用水瓢汲取江水,大瓢下去仿佛將一輪明月盛入
春甕,小杓輕舀似乎把江水分流歸入夜瓶。楊萬里評此兩句詩“其狀水之清美極矣”{18},王河在《茶典逸況》中寫道:“這兩句寫得很有氣魄,充分體現了作者的浪漫之思,豪放之情,瑰麗之想,大瓢能貯月,小勺可分江,如此橫溢的才思,竟從屢遭困頓的鬟發皓白老人的心中流出,那詩意茶情是何等的出類超群。”{19}這是全詩想象最為豐富,情感最為豪邁的兩句。在詩人眼中,此時已經不僅僅是為了煮茶而汲江中之水,更有貯水中之月,氣吞山河的豪邁氣概。在此,蘇軾大概將月賦予了光明、澄澈的意義來表達其恬淡曠達又略顯孤寂的心境。或許面對月夜下的一江清水,詩人忘卻了年齡與不幸,而是帶著欣賞美的眼睛和純凈通脫的心靈去享受自然的饋贈;亦或是物我兩忘,以一顆靜寂禪心去體悟天人合一,去探索生命的終極追求。很顯然,這里汲江水已不只是為了煎茶滿口腹之欲,更多的是給自己一個契機去融入天地,凈化心靈。
頸聯寫煎茶、沏茶、煮茶之時,白色的茶乳伴著煎得翻滾的茶腳漂浮上來。斟茶之時,茶水緩緩傾入碗中,發出“颯颯”的聲音,仿若一陣輕風吹過松林,卷起的松濤層層翻滾的響聲。五六句收去了大瓢貯月、小杓分江的豪邁情思,取而代之的是雪乳翻煎、松風如瀉的細膩美感,詩人精心將“雪乳”“松風”二詞置于句首,給人以視覺的沖擊感,將斟茶時詩人所思所見的畫面呈現在讀者的眼前:入眼便是雪色皎潔,閉目則聞松音如濤。我們難以想象,作者的內心該是如何的空明曠達才能體會到這般細微雅致的美感。
尾聯寫詩人飲茶枯坐。“枯腸未易禁三碗”源于典故:“一碗喉吻潤,二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七碗吃不得也,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20}原典盡顯新茶之美,而蘇軾卻出其不意地反其意而用,說自己難進三碗就臥于床上,荒城之夜,凄然悲愴,教人傷感。夜深人靜,孤身獨坐月下品茶聽更,長長短短的聲音傳入耳中,東坡心里是否泛起了舊事的漣漪,是否感慨自己的境遇?我想是有的,但是這種抱怨或者質疑大概是一閃而過的。那時的東坡已經是生命即將走到盡頭的白發老人,繁華滄桑在他眼里都已看開,因此才能在如此困境之中依然苦中作樂、雅致生活。但是末句我們仍然可以明顯感受到一種無奈,前面六句越是平淡清雅,結處的荒城聽更就越顯凄涼慘淡。即便是有“此心安處是吾鄉”的超然灑脫,也依然難以抵擋那長夜難眠無人訴說的落寞。茶,或許是蘇軾在那段歲月里凈化心靈、釋放煩憂的澄凈慰藉,或許是漫漫長夜伴其聽悠遠更聲的精神寄托。
縱觀全詩,空寂坦然的內心,閑淡優雅的茶興以及與天地合一的視角,讓人在清麗的語句中透視到一種常人難以達到的境界。“奇”已不僅僅局限于楊萬里所說的用詞造句了,反而是那種略帶禪意超脫通達的境界更顯其“奇”。或許,這就是平淡的最高境界,正如蘇軾自己所說的:“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21}
從直抒胸中苦悶到內心波瀾不驚,從思鄉心切到豁達釋然,三十年遷轉調度,浮浮沉沉,經歷過無數次生離死別的東坡漸漸習慣了“覺來幽夢無人說”的寂
寞,接受了“此生飄零何時歇”的現實,才得以在晚年表現出超然物外的釋然。
一闋是飄零伊始的真情流露,一首是命不久矣的閑適悠然,年輕時對故里流流連連,對故人心心念念,直到暮年終于認清現實放下執念,汲水煎茶風輕云淡。時光流轉,心境變遷,年歲有加,越發率真自然。無論是三十年前凄然悲切的東坡,還是三十年后禪意通靈的蘇子,不變的是無人相伴的寂寞,不變的是四處奔波的飄零,還有那透過文字,暈染千年的至純性情。
{1}④{9}{11}{12}{13} 〔宋〕蘇軾著,〔清〕朱孝臧編:《東坡樂府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頁,第124頁,第225頁,第57頁,第67頁,第217頁。
②③⑤ 宋祖 :《宋詞賞析》,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95頁,第33頁,第33頁。
⑥ 陶文鵬:《至真情語 樸拙渾厚》,《古典文學知識》2007年第5期。
⑦ 馮應榴:《蘇軾詩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4頁。
⑧ 蘇軾著,孔凡禮校注:《蘇軾文集》(卷五十),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458頁。
⑩ 《蘇軾詩集》(卷四十八),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641頁。
{14} 《蘇軾文集》卷五十四,第四冊第1596頁,《與程正輔書》。
{15} 《蘇軾文集》卷五十六,第四冊第1695頁,《與王敏仲書》。
{16} 〔宋〕蘇軾著,孔凡禮、劉尚榮選注:《蘇軾詩詞選》,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207頁。
{17}{18} 〔清〕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誠齋詩話》,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39頁,第139頁。
{19} 王河:茶典逸況———中國茶文化的典籍文獻[M],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
{20} 陳貽 :《增訂注釋全唐詩》卷377《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版,第2冊,第1934頁。
{21} 四庫全書本侯蜻錄紀昀等撰,子部,小說家類,雜事之屬,侯鰭錄,卷八,蘇軾《與二郎侄書》。
參考文獻:
[1] 王麗麗.【醉落魄】曲牌的流變考[J].黃岡師范學院學報,2011(1).
[2] 張拓.蘇軾詞中酒的情感內涵[J].文學教育(下),2016(6).
[3] 張燕.在曠達和超脫的背后——談蘇軾的情感世界[J].襄樊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0(4).
[4] 鄭毅.漂泊的孤鴻——論蘇詞中所蘊涵的“孤獨感”[J].黑龍江社會科學,2006(1).
[5] 韋衛妮.論蘇軾詩詞中的思鄉、歸隱意蘊[J].廣西教育學院學報,2005(1).
[6] 錢時霖.茶詩談趣(四)──蘇東坡茶詩賞析[J].茶葉機械雜志,1995(3).
作 者:李育倩,西南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在讀本科生。
編 輯:李珂 Email:mzxslk@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