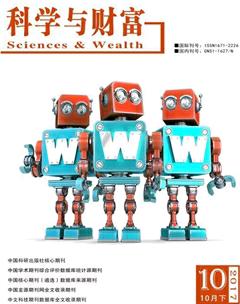IPO企業中“三類股東”法律問題分析
摘要:“三類股東”在中小企業融資過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更是市場逐漸僵化背景下活躍精靈。我們不應視其為企業IPO的障礙,而是要順應這一價值規律選擇的結果,了解其信托關系的內涵,透過現象看本質,正視其風險,完善其發展。
一、背景分析:監管困難,進度凍結
所謂“三類股東”,是指新三板公司中以契約型私募基金、集合資金信托計劃和產資管理計劃為形式的股東。“截至2017年7月5日,1146家新三板掛牌公司被“三類股東”投資;在參與定增的機構投資者中,“三類股東”占20%,出資共計456.5億元,”以上數據說明,“三類股東”在中小企業融資過程中起著巨大的作用。
然而由于“三類股東”非獨立法人、無法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可能導致申報企業股權不清晰、不穩定;私募產品接受規范監管的時間較短,各類私募產品真實形態復雜,明股實債、變相融資問題,層層嵌套、持有人權利不清、普通合伙人與有限合伙人職責錯位多有出現等原因,證監會對攜帶“三類股東”的申報企業的IPO進度予以“凍結”。以新三板掛牌企業海容冷鏈(830822)、有友食品(831377)、波斯科技(830885)為例,其首次申報時間大致在2015年底或2016年初,但直到2017年8月2日,三所企業才得到監管層的預披露。又有數據顯示,在若干家攜帶三類股東的新三板企業申報IPO的背景下,截至目前,僅有常熟汽飾(603035)、海辰藥業(300584)、碳元科技(603133)、長川科技(300604)、中原證券(601375)五家企業成功完成IPO。
二、理論分析:三類股東”的法律性質
首先從業務內容來看,契約型私募基金是以非公開方式向投資者募集資金設立的投資基金,并且基金管理人、投資者和其他基金參與主體按照契約約定行使相應權利,基于合同享有投資收益,承擔相應義務和責任。資產管理計劃的運行模式是證券公司、基金公司子公司或期貨公司向特定客戶募集資金或者接受特定客戶委托,擔任資產管理人,由托管機構擔任資產托管人,按約定為資產委托人的利益,運用委托財產進行投資的一種標準化金融產品。信托計劃是由信托公司擔任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為受益人的利益,將一個及以上委托人交付的資金進行集中管理、運用或處分的資金信托業務活動。
從業務內容可以看出,三類股東的業務本質都是由金融機構通過非公開方式向特定的出資人募集資金,由管理人合理運用資金獲取收益,管理人和出資人之間按事先約定分配收益、承擔風險。其不同之處在于發行產品的金融機構不同。
筆者認為,“三類股東”的法律性質可以總結為合同約定下的信托關系。
三、沖突分析:透過現象看本質
目前,“三類股東”問題表現有三:第一,前述分析了“三類股東”事實上均屬于信托關系,關系內涵是于已投資的公司,管理人代表三類股東行使股東權利,所產生的收益歸出資人,形成了事實上的委托持股,而委托持股又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股權清晰”,由此帶來障礙;“第二,三類股東以契約為載體,可能到期終止,出資人購買、轉讓或贖回份額無需對外公布,會影響IPO審核過程中“股權穩定”的判斷;”第三,三類股東非獨立的法律主體,不允許工商登記,因此在主體確定上缺乏權威的信息來源,而且投資門檻較低,單只產品投資人數較多,最終出資人身份及其關聯關系難以核查,將可能導致規避200人股東限制、實際控制人及戰略投資人規避鎖定期、持續經營要求的情況,也容易出現關聯關系、利益輸送、資金池投資、不符合股東適格性、突擊入股、實控人隱藏持股等問題。
攜“三類股東”IPO的風險表象如上所述,但筆者認為,“三類股東”成為企業IPO攔路虎的本質在于三類金融產品背后的核心運營理念和運營方式與跨類別(IPO)監管制度目標之間存在價值上的迥異與沖突——即民商法價值追求同金融法價值追求的沖突。三類金融產品的理念更多側重于追求效率與利益原則,同時由于委托人無論從標的財產投資領域、期限、內部份額轉讓變動等條件都可以通過與受托人約定決定,其產品具有相當的靈活性,本質上講雙方通過合同約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屬于民商事關系。民商事法律關系價值追求在于維護“個體利益”,其講求意思自治,雙方在簽訂信托類合同時并不會考慮整體金融安全和后續可能產生的宏觀制度的問題,而金融法卻在追求效率的基礎上強調“整體金融效益”,而維護金融效益的基礎在于維護整體金融安全,因此其受民商法調整還是金融法調整的界限就在于是否會影響到整體金融安全。正因為該類產品進入到金融領域可能會引起整體金融風險,所以金融監管機構才會針對三類金融產品設置相應的規則去調整。但目前相關規則僅是對三類金融產品的成立和正常運營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問題的“基礎范圍”進行了規范,當初制定相應規則時由于受到客觀金融發展水平的限制并未考慮到可能會出現的跨領域的“衍生范圍”的法律問題與制度沖突,因此才會出現一個具有“積極意義”金融產品同具有“積極意義”的監管制度的裂縫與錯位,從而產生了目前的僵局。
四、目標分析:信托關系主體化
由于三類股東并非同擬上市公司的其他股東一樣具有獨立法人地位,其在背后運營模式上亦是靈活多變、持有份額、持有人等可以相對隨意轉讓,加之實務上對三類金融產品備案登記制度并非完善,因此穿透核查至三類金融產品背后的自然人并保持持續的動態監管在監管角度可能存在相對高成本與難度的問題。因此,是否應當將依托“信托關系”產生的股東賦予一定的法人地位,將其視為“類法人”看待,值得探討。
參考文獻:
1、丹尼爾·F.史普博:《管制與市場》格致出版社,2008年7月
2、喬治·斯蒂格勒:《人民與國家:管制經濟學論文集》,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中文版:1994年,臺灣遠流出版社
3、喬治·本斯頓:《被要求的披露和股票市場:1974年證券交易法評估》
4、威廉·鮑莫爾:《可競爭市場:產業結構理論的一次革命》
5、李東方.《證券法學(第三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1月1日
6、朱錦清.《證券法學(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8月1日
6、李東方.證券發行注冊制改革的法律問題研究——兼評“證券法修訂草案”中的股票注冊制[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5,(3):44-49.
7、李東方.證券監管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18.
8、譚軍:《大資管時代信托業創新發展的國際比較研究》,東北師范大學,博士論文,F832.49
9、李寧:《商業信托委托人的法律地位》,法學論壇,2012年9月第5期,D922.282
10、李建華、張立文:《私募股權投資信托與中國私募股權市場的發展》,世界經濟,2007年5月10日,F830.91;F832.51
11、龍云:《完善信托財產登記制度的若干建議》,上海金融,2004年1月20日,D922.282
12、劉陽:《資產收益權信托法律問題研究》,華東政法學,碩士論文,D922.282;D920.5
作者簡介:
孫沁(1992——),女,河北省張家口市人,民族漢,職稱無,碩士研究生在讀,經濟法專業證券法方向.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