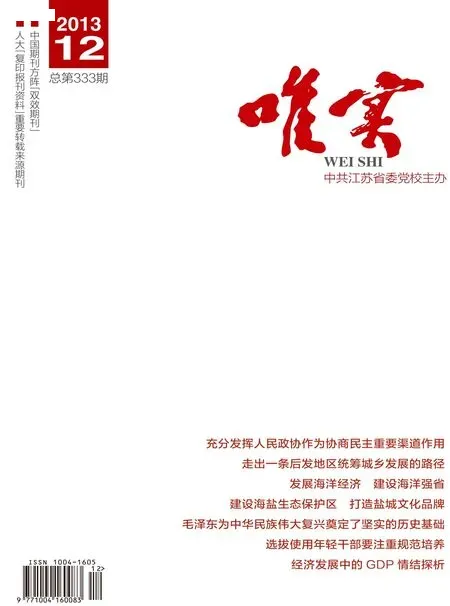實現江蘇勞動力流動與城鎮化協同發展
樊士德+++張堯+++吳勝
改革開放近40年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極大地推動了城鎮化進程。2015年和2016年中國城鎮化率分別達到56.1%和57.35%。作為國家首批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地區、發達省份的江蘇更是分別高達66.5%和67.72%,盡管超過了55%的世界城鎮化平均水平,但與西方發達國家約80%的平均水平仍有較大差距。與此同時,無論是對全國的城鎮化率還是江蘇的城鎮化率指標而言,地區間、城鄉間抑或部門間的勞動力流動在城鎮化進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所說:“過去的五年,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2個百分點,8000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李克強總理在近年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多次強調,新型城鎮化的本質是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而這一工作的中心在于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進城落戶,尤其是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然而,從城鎮化的本質內涵和要求看,中國近2.82億農民工呈現“漂浮式轉移”或“鐘擺式轉移”的非穩態特征,顯著區別于西方發達國家永久式的“市民化轉移”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貧民化轉移”。換言之,這一龐大的進城務工群體和其他常住人口并未實現真正的城鎮化。推動勞動力流動與江蘇城鎮化協同發展任重而道遠。
江蘇勞動力流動與城鎮化的演化脈絡與現狀
本文以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所確定的常住人口統計口徑計算城鎮化率,以勞動力流動規模、城鎮化水平及流動人口市民化程度來衡量江蘇省勞動力流動與城鎮化的協同程度。根據二者演進過程的特征化事實,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低度協同和低速發展階段(1978~ 1991年)。勞動力流動規模小,城鎮化水平低,二者增速慢且協同度低,構成這一階段即改革初期的基本特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獲得自己勞動的支配權,鄉鎮企業蓬勃發展制造大量非農就業機會,吸引數百萬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江蘇小城鎮數量由1978年的115個增加到1990年的517個。然而“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蘇南模式也造成了城鎮化發展的扭曲:小城鎮數量多,但規模小,勞動力流動緩慢,城鎮化水平長期低于全國均值,甚至在1989—1991年期間鄉鎮企業出現負增長,導致一部分民工被解雇,形成農民工的“回流潮”。
第二階段,低度協同和高速發展階段(1992~ 2000年)。勞動力流動規模與城鎮化水平增速快,但重效率輕質量、二者協同度依舊較低,是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征。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后,江蘇抓住經濟體制改革的契機,開啟轉向以市場化為主導、開發區為載體的城鎮化道路。從1992到2000年,江蘇城鎮化率從23.8%提高到41.5%,年均提高2.21%;勞動力流動規模由1073.1萬增加到1853.93萬,年均增長9.1%。到2000年底,流動人口占城鎮人口比重超過50%。但這一群體主要以兼業為主,農村與城市兩棲,呈現所謂的“候鳥式”和“鐘擺式”特征,勞動力流動與城鎮化二者間的協同程度仍然較低。
第三階段,中度協同和中高速發展階段(2001~2010年)。在這一階段,勞動力流動與城鎮化均實現了穩步增長,但是增速相比上一階段有所下降,而且流動人口落戶條件開始放寬,表明勞動力流動與江蘇城鎮化協同度有所提升,但勞動力流動內生于城鎮化的質量相對較低。2001年中國加入WTO,長三角地區也開始加快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江蘇吸引大量外資,外向型經濟之路的開啟助推經濟快速發展,引致大規模勞動力涌入。同年《江蘇省城鎮體系規劃》提出“三圈五軸”的城鎮發展空間格局,城鎮化發展進入新階段。2001到2010年,江蘇城鎮人口由3040.81萬增加到4367.63萬,年均提高4.8%;城鎮人口比重由42.6%上升到60.6%,年均增長2%;勞動力流動規模從1994.83萬增加到2983.81萬,年均增速為5.5%。流動人口市民化成為勞動力流動的必然趨勢,勞動力流動與城鎮化協同度有所提高。
第四階段,中度協同和深入推進階段(2011年至今)。江蘇勞動力流動增速放緩甚至停滯,而城鎮化開始深入推進,外流勞動力的真正市民化,即城鎮化由速度型推進向質量型推進轉向成為這一時期的重要戰略任務。江蘇基本形成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為重心,與中小城市相配合,以小城鎮為紐帶的城鎮發展體系和空間格局。2011到2016年,江蘇省城鎮化率年均增長率為1.15%,盡管增速較上一時期有所下降,但仍保持較高水平。勞動力流動規模于2011年首次出現負增長,2015年略有回升。到2015年底,流動人口占城鎮人口比重為43.93%。《江蘇省新型城鎮化與城鄉發展一體化規劃(2014—2020)》明確提出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對勞動力流動和城鎮化二者間的協同發展產生了較為顯著的政策示范效應。
勞動力流動與江蘇城鎮化推進中的突出困境
從勞動力流動與江蘇城鎮化間縱向的演進脈絡看,重大歷史事件、中央的宏觀政策及地方的微觀措施對于江蘇勞動力流動和城鎮化產生了重要影響,二者均呈現逐步遞增和改進的總體態勢,并呈正相關關系,但二者間的有機協同度仍然相對較低。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勞動力流動的社會經濟政策由最初的“嚴格控制”,到“限制”,再到“默許”,又轉向“管理”與“服務”,促進地區間、城鄉間、產業間和部門間大規模勞動力流動的形成,而大規模勞動力流動也加快了江蘇省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另一方面,截至目前,大部分外流勞動力并未獲得真正的城鎮戶籍身份,更未享受附載在“戶籍”背后與城鎮居民同等的醫療、子女教育、養老、住房等諸多公共服務與社會福利。換言之,大規模勞動力流動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城鎮化。因此,加快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步伐,以下幾點問題亟待解決。
勞動力流動與真實城鎮化水平間的不協同。長期以來,江蘇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迅猛發展,吸引大量勞動力流入,然而,這一流動依舊主要呈現“候鳥式”和“鐘擺式”特征,永久性遷移的模式并未形成,進而并未內生于真正的城鎮化,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巨大差異便是直接體現。例如,2016年江蘇省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7.72%,而2014年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29.45%,二者相差38.27%。這種“不完全”的城鎮化導致突出的市民化推進困境,阻礙城鎮化的推進及質量的提高,進而阻礙了農業現代化和城鄉真正一體化的深度推進。endprint
勞動力流動與城鎮化增速間的不一致。2011年以來,江蘇省勞動力流動規模增長緩慢甚至出現停滯,其原因是:一方面,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有所降低;另一方面,近年來勞動力尤其是老一代農民工返鄉回流趨勢有所增加。與此同時,江蘇省城鎮化水平盡管保持較高水平,但是增速有所放緩。從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統計指標看,勞動力流動規模的下降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城鎮化推進的速度。近年來蘇南地區甚至蘇中地區民工荒和技工荒問題便是典型例證。
勞動力流動與城鎮化進程在區域間的不平衡。因不同的地理位置、歷史條件、自然資源、政策觀念等因素,江蘇省區域間經濟社會發展呈現不協調和不平衡特征,而這一差距構成了省內地區間勞動力流動的主要誘因,同時也決定了各地區勞動力流向的差異化特征。長期以來,蘇南地區為勞動力流入地,而蘇中地區和蘇北地區則為勞動力流出地。一般而言,勞動力的大規模流入對城鎮化水平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而且要顯著強于勞動力流出的效應,進而造成江蘇城鎮化在蘇南、蘇中和蘇北不同區域間的明顯差異。到2016年底,蘇南、蘇中、蘇北地區城鎮化率分別為75.9%、64.0%和60.7%,蘇南地區城鎮化率最高,蘇中次之,蘇北地區最低,即呈由南向北梯度遞減特征。
勞動力流動與城鎮化質量上的不匹配。大規模勞動力流動并未從根本上融入城市,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顯著差異便是典型例證。與此同時,江蘇部分城市的地方城鎮建設存在規模擴張過快、占地過多等問題,借城鎮化之名“攤大餅”的現象依然存在,進而導致人口城鎮化滯后于土地城鎮化和經濟發展水平,土地利用效率和城鎮化質量有待進一步提高。在人口規模方面,2011—2016年,江蘇城鎮人口由4889.36萬人增加到5416.7萬人,新增城鎮人口527.34萬人,年均增長2.07%;城鎮化率則由61.9%提高到67.7%,年均增長1.81%;而在土地規模方面,2011—2016年城市建成區面積由3494平方公里增加到4299平方公里,累計擴張了23.04%,年均增長率也達4.24%,與包括流動人口在內的城鎮人口10.79%的累計增長率和2.07%的年均增長率形成顯著差異。在經濟規模方面,2016年第二、三產業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達94.6%,2011~2016年年均提高近9.36%。
勞動力流動與江蘇城鎮化不協同的誘因
促進勞動力流動與江蘇城鎮化間的協同、共進與耦合,是深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戰略的重要依托,是實現“強富美高”新江蘇的必然要求,而深入剖析二者未協同發展的根本原因是解決問題進而實現健康發展的關鍵。
制度因素是二者不協同的根本原因。長期以來,一方面,橫亙在城市和農村之間較為森嚴的戶籍制度構成了外流勞動力融入城鎮的主要障礙;另一方面,土地流轉制度的不完善導致外流勞動力擔心進城落戶會失去土地,構成了市民化意愿度不高的主觀成因。此外,盡管包括江蘇在內的諸多省份取消了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的區分,但附著在戶籍背后的住房制度、就業制度、教育體制、社會保障制度等仍然未發生根本性改變,二元特征依然存在,構成了農村剩余勞動力進一步轉移和流動人口市民化的多重制度障礙。
落戶成本是協同推進的主要障礙。《江蘇省新型城鎮化與城鄉發展一體化規劃(2014 ~ 2020年)》預計在規劃期內實現農村轉移人口進城落戶達800萬這一目標。然而,根據測算,僅就落戶過程中所涉及的社會保障、保障性住房、就業及子女教育四項內容而言,財政負擔的農民工市民化人均成本約為3—4萬元,即使以3萬元為標準進行計算,最低將需要新增財政投入2400億元,占2016年全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75%以上。當前,江蘇正處于城鎮化深入推進和產業轉型的關鍵時期,流動人口落戶的高昂成本及經濟增速放緩使得城鎮化繼續推進的壓力巨大。
地區不平衡是發展不協同的直接原因和外在表現。受區域間不同的區位環境、資源稟賦、發展政策等因素的影響,江蘇經濟發展呈現較明顯的區域差異。近年來,蘇南、蘇中和蘇北經濟發展水平均不斷提高,盡管蘇中、蘇北與蘇南的相對差距有所縮小,但絕對差距仍然較大。2016年,蘇南、蘇中和蘇北地區的GDP分別為44796億、15319億和18160億,三個地區的GDP占全省比重由2012年的59.9:18.3:21.8變為2016年的57.2:19.6:23.2。2013—2016年,蘇南、蘇中和蘇北地區的GDP年均增速分別為8.8%、10.5%和10.6%。這一區域間的不平衡造成了勞動力流向的不同,導致城鎮化水平在空間上的差異。
片面追求速度的政績觀是發展不協同的主觀原因。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城鎮化戰略提出之初,因政績觀的主觀扭曲,全國諸多地方存在重城鎮化推進速度、輕城鎮化質量的現象,片面追求城鎮人口、土地和經濟規模。這一方面導致城鎮數量增長迅速,人口城鎮化速率迅速提高;另一方面,也帶來城鎮化效率較低,品質提升慢的弊病。在江蘇部分城市,經過長期累積,形成了城市蔓延、交通擁擠、資源緊缺,以及環境保護觀念滯后等發展現狀。這些問題既是勞動力流動與城鎮化未協同發展的結果,更是二者協同水平進一步惡化的原因,嚴重阻礙了新型城鎮化推進過程中所強調的經濟、社會、生態和空間效益的有機統一。因此,激勵相容的政策機制設計顯得尤為重要。
江蘇勞動力流動與城鎮化協同發展的路徑
基于勞動力流動與江蘇城鎮化演進過程的特征化事實,以及二者未協同發展存在的困境及其誘因,可以采取以下路徑選擇,多管齊下,推進二者的協同發展。
推進制度創新,為勞動力流動與城鎮化協同發展提供驅動力。為推進勞動力合理流動,提高江蘇城鎮化水平和質量,需要分管農業、國土、教育、衛生計生、住建、財政、人社等領域的多部門聯動,突破現行管理體制束縛,加快體制機制改革創新,促進以往推進勞動力流動和城鎮化的行政主導模式向以市場為主進行調節的激勵模式轉變。具體而言,制度創新應著眼從勞動力流動過程中的農村推力和城鎮拉力兩個維度發力,囊括勞動力流動和城鎮化協同推進過程中最為關鍵的人口管理和服務、土地管理、就業、住房、養老、醫療、教育等多個方面,統籌推進,最大限度地消除勞動力流動障礙及其根本上融入城鎮的擔憂和不確定性,為高質量城鎮化的推進提供有效、系統的制度環境和制度保障。endprint
建立流動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擔機制,為二者協同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從短期看,流動人口的城鎮化存在多重的顯性和隱性成本,但從長期看,勞動力由農村向城鎮流動,以及城鎮化的推進,必將產生巨大的外溢效應。江蘇可以充分調研各層級地方政府、企業、個人的積極性,明確相應的責、權、利,建立成本分擔與激勵相容機制,降低不同主體因城鎮化推進所產生的各類成本,推動流動人口市民化,提升城鎮化質量。政府需要承擔義務教育、基本養老和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基礎設施等公共成本,在地方財力缺乏的情況下,可以通過發債等方式設置城鎮化專項基金來提供資金支持;企業要承擔外流勞動力融入城鎮過程中與城鎮居民相同的工資、培訓成本,以及相應的五險一金等社會保險成本;外流勞動力個體也要承擔在融入城鎮化過程中由其個人所要承擔的成本,如參加城鎮社會保險的個人認繳成本、職業技能提升過程中的培訓和受教育成本等。
各區域因地制宜,發揮比較優勢,實現二者協同發展的空間均衡。勞動力流動對流入地的“乘數效應”與對流出地的“擴散效應”之間存在著效率差異,這種差異是蘇南、蘇中和蘇北不同區域間城鎮化和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的重要原因,各區域需因地制宜、因勢利導。蘇南地區應提高城鎮發展質量,努力實現內涵式發展;蘇中地區要加快寧鎮揚一體化進程,承接長三角地區的產業轉移,在自身崛起的過程中推進勞動力流動和城鎮化二者間的協同度;蘇北地區要實施點軸式開發戰略,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進而改變以往傳統的、單純的務工經濟思路,逐步留住優質勞動力,形成人才集聚和產業集聚的良性互動。對于蘇北和蘇中地區而言,尤其要重視主導產業的培育、人文環境的營造,以及就業規模的創造等方面的工作,進一步加快城鎮化速率,縮小與蘇南地區的差距。
優化產業結構,為二者的協同和耦合提供產業載體。無論對于勞動力流動,還是城鎮化,都離不開合理的產業結構支撐,因為勞動力流動過程本身就是勞動力在產業間的流動,城鎮化進程本身就是產業演進和推動的過程。因此,必須推進農業產業化,加快二、三產業發展,進一步提升服務業比重,優化和調整產業結構,為外流勞動力提供就業空間,并實現就業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良性互動。在這一過程中第一產業比重的下降,以及勞動力生產率的提升,將進一步對勞動力外流形成推力,進而促進勞動力向二、三產業流動,并推進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實現勞動力流動和城鎮化之間的相互協同和耦合。與此同時,蘇南、蘇中和蘇北地區根據自身不同的區位優勢和資源稟賦,優化產業布局,完善產業鏈分工,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以產業梯度轉移引導勞動力要素梯度轉移,做到“以產引人、以產找人、以業控人”,實現外流勞動力、產業與城鎮化三者之間的協同聯動和在空間上的優化布局。
〔本文系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勞動力流動與江蘇新型城鎮化協同機制研究”(2014ZDIXM016)、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中國勞動力流動的地區福利效應研究”(16YJA790012)、江蘇省第五期“333工程”科研項目“江蘇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對就業結構的影響與政策研究”(BRA2017460)、江蘇高校“青藍工程”資助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樊士德、張堯,南京審計大學;吳勝,南京大學)
責任編輯:戴群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