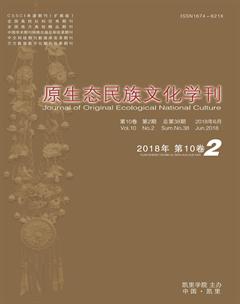“法治雙軌制”:我國社會轉型期少數民族習慣法與國家法的互惠機制
杜鵬
摘 要: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而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需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以我國侗族款約法為例,認為在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和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背景下,少數民族習慣法具有獨特的整合價值。厘清習慣法與國家法的地位和功能,整合兩者之間的內在關系和雙向資源,實行“以國家法為主,以習慣法為輔”的“法治雙軌制”,有利于實現國家對少數民族社會最佳的實際治理效果。
關鍵詞:少數民族;侗族款約;民族習慣法;國家法;雙軌制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21X(2018)02-0079-07
侗族主要聚居于我國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湖南省的新晃、芷江和通道侗族自治縣,廣西壯族自治區的三江侗族自治縣。此外,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也有少量散居侗族分布。侗族總人口約288萬人(2010年),以信仰原始宗教為主,其民族語言侗語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侗水語支,分北侗和南侗兩種方言。歷史上,侗族無本民族文字,20世紀50年代,根據拉丁字母形式創制了侗文,現通用漢文。通常認為,侗族的祖先由古代百越的一支發展而來。其自稱“仡伶”最早見于宋代文獻中。明清時期,侗族被稱為“洞蠻”“峒人”和“侗僚”,民國時期被稱為“侗家”,新中國成立以后才被統稱為“侗族”。侗族自稱為“Gaeml”,而“侗族”或“侗家”是漢族對侗族的他稱。在侗語中,“Gaeml”的原初意義是指“用木條和樹枝等作為障礙物對本族進行遮攔和保護”,以對外進行隔離和設防。而“Gaeml”用作侗族的族稱,引申義即為“生活在被山嶺層層阻隔、被森林濃密遮蓋的人們”。侗族世居的地區多為山地丘陵,其中有很多被當地人稱為“壩子”的山間小盆地。長期以來,侗族依山傍水而居,倚靠世居地獨特的自然地理和生態環境,以種植水稻為主,兼營林業,農林業發展歷史悠久,素有“水稻民族”之稱。由于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歷史發展,侗族社會迄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遺存了侗族款約的影響力。在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和全面實施“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下,如何厘清少數民族習慣法與國家法的地位和功能,整合兩者之間的內在關系和雙向資源,實現國家對少數民族社會最佳的實際治理效果是一個極具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學術話題。本文即以我國少數民族侗族的款約法為例,對此進行相關探討和分析,并且提出有效整合二者之間張力的互惠機制——“法治雙軌制”。
一、侗族習慣法概述
侗族作為一個民族,大概形成于隋唐時期,在此之前,侗族一直處于原始社會發展階段。唐代中央政府開始在我國南方侗族地區設立州郡,建立羈縻制度。侗族首領們由此逐漸歸附于中央王朝,并且長期向朝廷進貢,朝廷則許以他們土官世襲。“峒”是當時侗族社會內部的傳統行政區劃,由侗族地方大姓出身的“峒主”把持著峒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大權。隨著中央王朝勢力對侗族地區的不斷深入,侗族社會也開始受到其他民族尤其是漢族的影響,其政治、經濟和文化都有了較快的發展。在中央王朝影響力所及的侗族地區,開始出現城池、集市和學堂,并且出現侗族社會內部“熟戶”與“生界”的分化。所謂“熟戶”,是指環居在以峒首城池為中心、受到漢文化影響較大的峒丁,“生界”則是指更為邊遠、受到漢文化影響較小的侗族深山區。清代初期,中央王朝對侗族地區進行“改土歸流”,委任流官直接管轄侗族各地土司,侗族地區出現“土流并治”的局面。侗族土司的權力開始受到流官的節制,侗族社會被進一步納入到中央王朝的統治體系之中。
但是,由于侗族生活的地區相對邊遠,歷史發展和文化傳統較為特殊,歷代中央王朝對侗族的實際政治控制力和文化影響力畢竟有限。不論是在“熟戶”區域,還是“生界”,都仍然普遍不同程度地殘存著侗族發展早期的部落氏族組織,而以地域為紐帶、兼具原始氏族農村公社和原始部落聯盟雙重特征、一直留存于清末民初的“款”組織就是典例。“款”又稱為“合款”,是侗族歷史上特有的民間社會自治組織和準軍事自衛組織,可謂“前國家組織形態的活化石”。按照規模來看,款有大小之分。特大款也稱為“聯合大款”,由若干大款聯合而成,這是一種幾乎涵蓋了侗族全民族的侗族款組織的最高形式,具有民族性;大款由若干分布地域范圍較廣的小款聯合而成,具有地域性;小款又由地域分布更小、彼此相連的若干村寨組成,具有血緣性。每個大小款的首長稱為“款首”,大款首由小款首民主商定而出,而小款首則由寨間公推產生。特大款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最高款首,只是由各大款的款首聯合構成,正如侗族學者鄧敏文先生所說,侗族傳統社會是一個“沒有國王的王國”。侗族每個村寨都實行“長老”統治,而長老又依據侗族習慣法——“款約”維持村寨的社會秩序。歷史上,侗族的最高權力機構是款民大會,只要是侗族成年男子都必須參加,以原始民主的形式共同商議款內的事務。而由款首們共同議定的款約,則要求全體侗民必須共同嚴格遵守,款首和寨老也不例外。
侗族雖然并無本民族文字,但是侗族地區歷來被人們稱為“詩的家鄉,歌的海洋”。侗族民歌作為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其多姿多彩的藝術類型和極具魅力的藝術感染力,深受侗族民眾的喜愛,在侗族社會中始終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早期的侗族款約主要通過講款、多耶和唱侗族大歌等口頭形式得以世代相傳。后來受到漢文化的影響,漢字傳入侗族社會,侗款的傳承方式開始出現文本形式,諸如石頭文本、碑刻文本和款詞文本。侗款的內容極為豐富,幾乎涵蓋了侗族生產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創世神話、民族起源、區域界定、生產秩序、行為規范、道德倫理、宗教信仰和民間禁忌等,可謂一部折射侗族社會秩序和解讀侗族文化密碼的百科全書。從類型上來看,款約具體可以分為約法款、創世款、族源款、款坪款、出征款、英雄款、習俗款、請神款和祭祀款等。其中,約法款是侗族傳統社會的基本大法,是侗族款約的主體部分,它對侗族成員的各種行為進行了較為全面而系統的規范。約法款包括“六面陽”“六面陰”和“六面威”三大部分,每個部分又包括6個子方面的具體內容。“六面陽”針對罪行較輕者,一般以適當罰款、令其敲鑼喊寨使其蒙羞責其悔過等輕微方式進行處罰;“六面陰”針對罪行嚴重者,通常以活埋和沉塘等極刑方式進行嚴懲;“六面威”則是對社會成員日常生活禮儀和道德規范的要求,包括諸如倡導彼此尊重、和睦相處、熱情好客、寬容友善等鼓勵性規范以及諸如反對奢靡、避免紛爭等禁止性規范,對違犯者以教育和勸誡為主。“在諸多少數民族習慣法中,唯有侗族習慣法通過以類似憲法性質的《約法款》為依據,創設了很多關于生活、生產、婚姻等方面的規約,并以此成為侗族社會的法律體系,我們將這個法律體系稱為款約法。這是侗族習慣法不同于其他少數民族習慣法的特別之處,也是侗族習慣法的魅力所在”[1]。
二、侗族習慣法與國家法的沖突與契合
少數民族習慣法在我國不同的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中有著不同的稱謂,例如侗族的款約、苗族的榔規、佤族的阿佤理等,此外,還有諸如古法、規約、章程等。而“習慣法”這一現代性概念,是晚近從西方以西方法學、西方人類學的形式傳入我國的。它指的是依據一定的民間組織和社會權威約定成俗,旨在調整一定民族和一定地域范圍內的社會關系以維護本土社會秩序,具有原生性、自發性和強制性的一整套民間行為規范總和。習慣法是相對于國家制定法而言的,它相對獨立于國家法之外,與國家法有著不盡相同的價值取向,甚至有諸多與國家法相抵觸的條款。在19世紀民族國家興起的西方世界,由于國家法的普遍確立,“法典萬能主義思潮”一度占據社會主流,習慣法受到國家法的強烈排斥。雖然后來西方法學家們發現,由于現實社會的多元性和復雜性,國家法并不是萬能的,習慣法才逐漸受到重視,甚至成為國家法法源的重要補充。但是即便如此,在當今社會中,習慣法也只是在民事領域具有一定的適用性,在刑事領域卻因其條款和實踐普遍有悖現代國家制定法“罪刑法定”的原則而遭到嚴格排斥。
在侗族傳統社會,侗款中“六面陰”主要規定了涉及刑法方面的內容。其中的生命刑、資格刑和財產刑等刑罰種類,與我國現行刑法大體相同,但是兩者具體刑罰方式卻大相徑庭,出發點也各異。傳統侗款中的刑種除了極刑以外,多是以羞辱違犯侗款者為目的的羞辱刑,而且極刑的具體執行方式也極為殘酷,例如活埋和水淹等,以彰顯侗款的權威性,同時警醒再犯者。而我國現行刑法中除了生命刑以外,刑罰以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為主,主要是以教育為目的的自由刑。在今天以國家法的視角來審視,傳統侗款中諸多刑種的處罰方式,顯然與國家法嚴重違背,例如活埋和抄家等,這些本身就是國家刑法明文規定的嚴重侵犯公民生命權和財產權的犯罪行為。“驅逐出寨”和“吞食亂棍”也是兩種顯然有違國家法對公民自由權和生命權依法保護的侗款規定。驅逐出寨在20世紀90年代我國的部分侗族地區仍然存在,例如有人由于失誤導致侗寨失火,造成全寨巨大生命和財產損失,這在侗族習慣法看來,就是較為嚴重的過失罪。寨老們會根據侗款的相關規定,對肇事者通常做出將其開除寨籍、驅逐出寨的重罰。當然,對于驅逐的空間距離和時間長短因具體的情況會有所不同,但是由于被驅逐者一旦是家庭中的主干,往往就意味著其全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牽連,與其一起遷移到寨外被全寨孤立地生活。可以想見,在侗族山區閉塞、交通不便、生活環境較為惡劣的村寨,那種被強行隔離而獨自應對各種生活困境的嚴酷性不言而喻。吞食亂棍指的是侗族全體寨民對自己所集體仇視、深惡痛絕的當事人進行亂棍打擊的群體性暴力懲罰行為。在20世紀末期的部分侗族村寨中,一些偷盜者被寨民發現后因吞食亂棍而導致斃命的案例仍然時有發生。如上所述,傳統侗款中的刑法內容,由于對一些侗款違犯者的刑罰過于嚴酷,多涉及嚴重侵犯公民生命權和財產權的條款和實踐,因而基本上已被廢止使用。此外,侗族普遍信仰風水之說,認為盜墓行為會破壞墓地的“龍脈”,進而影響整個侗寨的安危,因而侗族習慣法將盜墓行為定為死罪,侗款約法款中的“六面陰”中對盜墓者給予活埋和沉水的明確嚴懲。侗族主要居住在深山之中,其住居多為由杉木建造的木質干欄式建筑,一旦發生火災極易導致全寨毀于一旦,因此侗族的防火意識極高。“六面陰”中對縱火燒山毀房者也有著極為嚴厲的處罰,規定當事者若有錢就可以以錢代償全寨損失,若沒錢就償命。但是另一方面,侗款對經濟詐騙的行為處罰卻很輕,僅僅要求詐騙者如數歸還被騙者的金額或者相應物質損失而無任何其他處罰,這又與國家法的規定迥然不同。如上所述,與國家法相比,侗族習慣法由于缺乏先進的現代法學理論和系統的法律體系指導,在諸如法律分類、罪行裁定、刑罰方式、具體量刑等方面存在認識上的模糊和混亂,在實踐上也具有較大的人為性和隨意性,因此具有先天的缺陷。
如今,侗款的主要調整方向是一方面繼續保持部分原有涉及民事方面的內容,并且加以改革和優化,這些民事條款涉及調解民事糾紛、維護生產秩序、社會行為規范、家庭婚姻倫理、財產繼承制度、社會治安和山林保護等方面,另一方面也與時俱進,吸收增設一些新的符合時代發展的道德規范。即使侗款仍然存在關于懲罰方面的內容,例如財產刑和名譽刑,但也只是作為傳統懲罰方式的替代手段,且多具有象征性,完全摒棄了以往那種具有嚴重暴力性、嚴酷性的懲罰方式。這些象征性的懲罰方式主要有:小額罰款(如今侗族習慣法罰則的主要類型)、罰酒肉(寬泛意義上也可以看作是罰款的一個變種,即責令當事人出錢請全村人喝酒吃飯以賠罪)、責令當事人鳴鑼喊寨、放炮或洗臉(最典型的羞辱刑)等。此外,孤立當事人也是傳統“驅逐出寨”懲罰方式的延續,只不過不再以強制驅離的嚴厲方式進行,而只是全寨人在心理上對侗款違犯者進行集體孤立,在現實生活中表現為不與違犯者接觸和交往,從而給違犯者以精神層面上的懲罰。至于如今在侗族地區發生的諸如殺人和放火等嚴重犯罪行為,侗族習慣法通常都不再干涉,而是直接移交當地公安機關進行處理,體現了對國家法在刑事領域具有絕對權威的尊重。
傳統侗族習慣法尤其是其中涉及刑事領域的內容在與國家法存在沖突一面的同時,其民事領域內容卻有著諸多與國家法相契合的一面。這些民事習慣法涉及侗族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諸如生產秩序、財產保護、婚姻倫理和生態保護領域等,都有著明確而詳細的規范。在生產秩序方面,由于侗族主要居住于山地之中,土地和水源對于他們來說都是維持生存必不可少的稀缺資源,侗族歷來就有“讓得三杯酒,讓不得一寸土”的說法。為了使復雜的土地有較為明確的權屬,從而避免紛爭,侗族款約規定:“講到坡上樹木,講到山中竹子。白石為界,隔開山梁。不許越過界石,不許亂移界標。田有坎,地有邊。金樹頂,銀樹梢。你的歸你管,我的歸我營。”[2]這些界限的劃分都是在寨老的主持下,由涉及邊界利益劃分的各方協商確定,一旦形成協定并且以款約的形式予以固定,即具有了一定的“法律”效力,各方都不得反悔,也不得隨意更改界限、破壞界標或者越界作業。但是對于水資源,侗族則倡導合理分配、資源共享,對肆意偷水、浪費水資源或者損毀水利設施的行為予以處罰。侗款中對于人們的私有財產有明確的保護條款,對于借用物品者要求有借有還。只是由于歷史上侗族社會商品經濟發育緩慢,過去的交易和借貸多是以物易物和以物還物,因此侗款中沒有“借貸”的概念,這反映出侗款的內容受制于侗族社會發展的具體歷史條件。關于婚姻的條款是侗款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從戀愛、訂婚到結婚,從婚后的婚姻倫理、離婚到再娶或改嫁,都有著相應的具體規定,可謂面面俱到,涵蓋了婚前婚后的方方面面。在侗族社會發展早期,侗族實行“同姓不婚”的婚俗,當時侗族聚族而居的部落式社會只能“遠娶遠嫁”,這給居住在深山之中交通不便的人們帶來了諸多不便。直至清代乾隆年間,貴州和廣西侗族地區眾多的款首集聚今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縣境內的中朝款坪,共商侗族婚姻變革事宜,最終定下“破姓開親”的盟約,以使侗族今后可以就近婚配。所謂“破姓開親”,實質上是對以往“同姓不婚”的一種變通,指的是將大姓房族劃分為若干更小的小姓房族,實行“內姓制”和“外姓制”,即對內各小姓房族各有一姓,但是對外則仍然共用大姓。如此一來,各小姓房族之間就可以實現就近婚配。但實行“破姓開親”絕非提倡“近親結婚”,它的目的只是為了解決侗族以往“遠娶遠嫁”的婚俗弊端。在侗款中,明確規定了人們只有出了“五服”才能夠結婚,嚴格禁止近親結婚。侗款對侗族婚前婚后極為詳盡的規定和相應的處罰,體現了侗族對維護家庭穩定的重視,實質上也是一種從婚姻習慣法的角度對侗族鄉土社會秩序的維護。侗族普遍信仰原始宗教,相信萬物有靈。他們認為人類只是浩瀚宇宙中的“滄海之一粟”,大自然是他們賴以生存和棲息的家園,人類是大自然之子,因而對能夠提供給他們各種生產和生活資料的大自然有著一種本能的崇敬和熱愛。侗族這種樸素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觀,也鮮明地體現在侗款之中。在侗款中,規定人們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要有節制,對亂砍亂伐、燒山毀林等肆意破壞森林資源的行為予以嚴厲懲處。正因為如此,侗族地區迄今仍然極為完好地保持了當地生態環境的平衡,植被郁郁蔥蔥,河流清澈淙淙,生物多樣性顯著,人與自然水乳交融、和諧共處。這不得不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侗族原始宗教信仰中樸素的生態和諧意識,以及侗款中對于保護生態環境的高度重視和對于濫用自然資源、破壞生態環境者嚴厲的處罰規定和實踐。
三、“法治雙軌制”:少數民族習慣法與國家法的互惠機制
少數民族習慣法具有鮮明的民族性,而侗族款約法就是一種起源較為原始而又發展相對成熟的少數民族法制形態,是侗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整套具有一定權威性和強制性的民間行為規范總和。它源于侗族自身獨特的歷史傳統和生活實踐,相對獨立于國家法之外,因而具有較強的穩定性。侗族款約法作為一種少數民族法文化和法意識形態,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并不會隨著社會制度的根本性改變而迅速消失。它即使是在形式上銷聲匿跡,但實質上仍然會以各種方式繼續不同程度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具有較強的“文化慣性”。因此,“試圖依靠國家強制力將民族習慣法消除不僅不科學,而且也不現實。所以,在堅持國家法制統一的前提下,允許少數民族群眾的習慣法觀念、習慣法情感和某些習慣法效力的存在是可行的、必要的”[3] 。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第一章總綱中的第五條規定,我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里的“依法”,當然主要是指依據“國家制定法”。但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是,這里的“法”是否也一定程度上包含在不違背國家法的前提下經過革新后的少數民族習慣法呢?對于這個問題,我們認為至少不應當不加思考地完全斷然予以排除。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是實現國家治理法治化和現代化的一場深刻革命,要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以良法來促進發展和保障善治。考慮到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特殊國情和我國目前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各民族發展并不平衡。況且我國還正處于社會轉型過渡期,社會結構的二元性在一定時期和一定地域內仍然會長期存在,而總體發展相對滯后的少數民族地區,其社會結構的二元性無疑更加明顯。一些少數民族由于獨特的生活環境、歷史發展和文化傳統,仍然較為濃厚地保留了自身的民族習慣法傳統。從廣義法文化的視角來看,法文化包括了“作為觀念的法”“作為制度的法”和“作為實踐的法”。少數民族習慣法無論在共時性角度上作為一種事實上與國家法仍然并存的“邊緣法”,還是在歷時性視角上作為一種獨立于國家制定法之外的“原始法”,它都具有“準法律”的特征。在現代社會,國家倡導國家法的統一性和權威性,少數民族習慣法即使被排斥在國家法律體系視野之外,失去“作為制度的法”和“作為實踐的法”的生存空間,但是卻無法立即失去“作為觀念的法”在少數民族思想觀念中的強大文化慣性和文化影響力。誠然,這些民族習慣法畢竟產生于少數民族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存在諸多不合理、不科學、有違現代法治精神的內容,這在一定程度上與國家法的理念和實踐相沖突,與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法治精神相抵牾。但是,我們也應當理性、辯證、務實地看到,少數民族習慣法畢竟根植于少數民族的生產生活實踐和深厚的歷史傳統,具有廣泛的民意基礎。如果能夠恰當地利用其中不與國家法律尤其是刑事法律發生抵牾的其他合理部分,摒棄落后于時代、有違國家法基本精神的不合理部分,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與時俱進,積極革新,使少數民族習慣法在國家法的積極引導下得以自我重塑,這對于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維護當地社會穩定和加強民族團結、有效解決少數民族民間糾紛,以及創新少數民族地區社會治理機制,都無疑具有重要作用和綜合效益。
在國家對少數民族地區進行“送法下鄉”的國家法宣傳教育活動中,國家法律工作人員應當充分尊重當地少數民族習慣法中合理性的一面,使國家法與少數民族習慣法之間形成一種良性互動,在少數民族習慣法不違背國家法的前提下,做到兩者互學互鑒。一方面,少數民族習慣法要主動向國家法靠攏,在少數民族文化精英對本民族習慣法進行自我革新的同時,也可以繼續保持當地少數民族自身法文化中的優良因子。例如,少數民族習慣法在形式上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獨特的宣傳教育方式,在內容上繼續堅持符合本民族和本地區實際的習慣法條款;另一方面,國家法律工作人員也應當深入少數民族地區,結合少數民族實際,對少數民族習慣法的改革進行積極引導,甄別少數民族習慣法中的“精華”和“糟粕”,辯證取舍,穩步改革,不僅做到少數民族習慣法改革的“合法化”,也要做到“合理化”和“合情化”。《憲法》雖然強調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強調憲法法律至上,但是同時也強調各民族都有保持或改革自身風俗習慣的自由,并且明確指出民族自治地方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特點制定相關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因此,在堅持國家法在國家法律體系中主導地位的同時,也應當充分考慮到少數民族風俗習慣,通過合理運用法律變通權,做到二者之間張力的平衡,積極引導少數民族習慣法的改革不僅朝著理性化和規范化的方向發展,也要做到“民族化”和“地方化”,適當兼顧少數民族良性的傳統法文化習俗和地方性“小傳統”。此外,少數民族對習慣法的宣教方式具有獨特優勢。以侗族為例,侗族款約法要么以簡潔凝練、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述形式呈現在人們面前,要么索性以唱詞的形式進行法文化展演。這種形象生動、寓教于樂、以少數民族喜聞樂見的通俗藝術形式的習慣法宣傳教育,必定會在少數民族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易于使他們潛移默化地內化接受、轉換理解和共同遵守,也易于使少數民族習慣法在他們之間進行廣泛的傳播和發揮深刻的影響。北京大學法學教授朱蘇力先生認為:“國家制定法有國家強制力的支持,似乎更容易得以有效貫徹。其實,真正能得到有效貫徹執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與通行的習慣慣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規定。”[4]國家法律工作人員也應當學習借鑒少數民族習慣法獨特而高效的宣教方式,將國家法的理念通過不斷“有機嵌入”改革后的少數民族習慣法——例如介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鄉民規約” 中,使廣大少數民族逐漸接受國家法的主導地位。只有使少數民族深入了解國家法的現代法治理念,熟悉國家法的一般性法律原則,明確國家法的主導地位,才能更好地引導少數民族在遵守本民族習慣法的同時也遵守國家法,才能真正有效地推進國家法治化進程。
從發生學的視角來看,法文化通常分為內生性法文化和移植性法文化兩種。在一個文化高度一元化的國家或社會中,內生性法文化和移植性法文化通常無法并存。但是,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尤其是處于社會急劇轉型期的發展中國家,這兩種法文化往往鮮明地并存。這種并存不僅體現在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民族之間,也體現在同一民族尤其是少數民族社會內部之中。在發展相對滯后的少數民族文化語境中,“內生法文化”往往指的就是其民族習慣法。少數民族習慣法體現出少數民族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是遺留迄今的少數民族思想觀念中的“活的法”。雖然以西方法律體系或者以國家法為代表的移植性法律在當今少數民族地區具有文化強勢地位,但是它想要真正有效地在少數民族地區發揮效力,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倚賴少數民族習慣法——以其為“嵌入性中介”才能更好地發揮實際效力。在少數民族社會轉型中,充分利用其傳統文化資源和本土法治資源,順應少數民族傳統法文化的慣性路徑,將國家法和民族習慣法有機結合,靈活運用少數民族法律變通權,能夠有效規避或者減少少數民族地區司法審判的阻力,降低司法審判的時間、精力和金錢成本。總之,在當前我國處于社會轉型的過渡時期,作為“準法律”的少數民族習慣法在不違背國家法的前提下,完全可以與國家法并行不悖,并且互相憑借,互相借鑒,互相補充,在各自層面發揮各自作用,形成對少數民族社會治理的雙向合力。
四、結語
我國著名法學家和政治學家鄧正來先生認為:“法律哲學的根本問題,同一切文化性質的‘身份問題和政治性質的‘認同問題一樣,都來自活生生的具體的世界空間的體驗:來自中國法律制度于當下的具體有限的時間性,同時也來自中國法律制度所負載的歷史經驗和文化記憶。”[5]在我國少數民族社會轉型過渡期,厘清習慣法與國家法的地位和功能,整合兩者之間的內在關系和雙向資源,實行“以國家法為主,以習慣法為輔”的“法治雙軌制”,有利于實現國家對少數民族社會最佳的實際治理效果。在此過程中,要防止兩個極端,一是過度強調國家法的唯一性和權威性,完全否認和排斥少數民族習慣法的固有功能和獨特價值,忽視其所具有的符合我國現實國情和少數民族地方文化傳統的合理性的一面;另一個則是過度拔高少數民族習慣法的地位和作用,甚至以其獨特性將其凌駕于國家法之上。事實上,這兩種觀念都是有失偏頗的,要么過窄地理解國家“依法治國”的本質精神,要么違背了少數民族法治建設的底線原則。從法人類學的視角來看,國家法是國家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重在“社會管制”,而民族習慣法則起著少數民族社會內部“社會調解器”的作用,重在“社會自治”。盡管少數民族習慣法與國家法有著不盡相同的價值取向,但兩者在社會內在和諧秩序的本質追求上卻殊途同歸。一方面,少數民族習慣法作為少數民族重要的傳統文化事象,必定含有不符合時代發展和現代法治精神的內容,因此必須自我革新;另一方面,它作為一種“民間智慧”和“地方性知識”,也必然含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蘊含著與國家法相契合的理性精神。因此,靈活、變通、適時、適當、合理地運用少數民族習慣法,充分利用少數民族本土法文化資源中的原創智慧和優良因子,不僅有利于少數民族民間糾紛的法律解決,同時客觀上也有利于維護當地的社會穩定和民族團結,實現民族地區社會治理的創新,達到少數民族地區社會治理中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機統一。
參考文獻:
[1] 胡月軍.侗學之絕唱,法學之離騷——《侗族習慣法研究》問世的意義[N].中國民族報,2013-03-15(006).
[2] 鄧敏文,吳浩.沒有國王的王國——侗款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75.
[3] 戴小明,譚萬霞.論民族習慣法與國家法的沖突及整合[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6).
[4] 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10.
[5] 鄧正來.中國法學向何處去——構建“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時代的論綱[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4.
[責任編輯:吳 平]
Abstract: A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tated in the report to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dvancing a law-based governance in all areas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and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hile unswervingly following the road of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need to develop the theory of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venant law of Dong minority, aimed at proving the unique value of the customary law of ethnic minoriti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a new era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clarify the status, function and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stomary law and national law can help build a “dual-track law system” that is “mainly based on national law and supplemented by customary law” for improved governance on ethnic minorities.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ies; Dong minority; customary law; national law; dual-track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