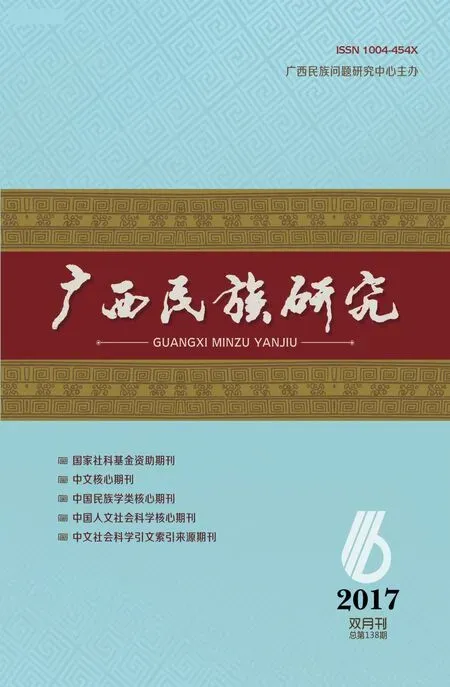黍作文化的代表*
——基于秭歸土家族薅草鑼鼓的研究
袁 玥
黍作文化的代表*
——基于秭歸土家族薅草鑼鼓的研究
袁 玥
薅草鑼鼓作為黍作文化的代表,生動形象地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勞動人民的生產、生活、思想、感情,是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的深厚積淀,更是保存巴楚古音的優良載體。隨著社會的進步、科學的發達和勞動方式的轉變,土家族薅草鑼鼓必然走向社會性的自然消亡,搶救和保護薅草鑼鼓傳統藝術形式也就成為文化多樣性的必然要求和傳統文化發展的重點。
土家族;薅草鑼鼓;黍作文化;傳統音樂;秭歸
引 言
長期以來,薅草鑼鼓與山區農民生活息息相關,是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在土家族勞動人民中產生和流傳的藝術形式。在生產方面,薅草是保證苞谷豐產的一種必不可少的農耕勞作。薅草鑼鼓是人們在薅草時邊打鑼鼓邊唱歌的勞動方式,俗稱“打鑼鼓”。打鑼鼓者稱為“鑼鼓師傅”,是勞動的指揮者,歇涼(休息)、吃午飯、放工、調場(調整薅草進度)、轟場(催進度)等都由鑼鼓師傅指揮。薅草打鑼鼓,具有提神解乏的作用,特別是晚歇鑼鼓時(放工之前),經過一天的勞作,勞動者又累又乏,鑼鼓師傅就唱些“葷歌子”(又稱“花歌子”),或是插科打諢,或是即興將薅草的、過路的婦女編詞打趣,引起陣陣歡笑,從而調劑精神。同時,在歌聲與鑼鼓聲中,薅草人不能相互交談,只能一心專注于薅草,從而大大地提高勞動效率,故有“一鼓催三工”之說。在精神生活方面,薅草鑼鼓在田中演唱著人間百態和一些民間故事、傳說等,使人們精神愉悅,自然就把薅草鑼鼓昵稱為“農戲”。薅草鑼鼓除主要用于苞谷薅草外,還延伸到集體勞動,如開荒、種地、修水庫等,甚至延伸到水稻田的除草。
2008年秭歸土家族薅草鑼鼓被列入湖北省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它作為傳統音樂文化的一種形式,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勞動人民的生產、生活、思想、感情等風貌,是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的深厚積淀。通過查閱文獻資料發現,秭歸土家族薅草鑼鼓研究尚無人涉足,遂于2015年10月2日至5日對此進行了實地調查。筆者通過采訪當地的民間藝人和查閱《秭歸民間音樂集成》等資料,試圖對秭歸土家族薅草鑼鼓的基本特點和表演形式等進行初步研究。
一、地理環境和歷史淵源
秭歸縣是湖北省宜昌市所屬縣,位于湖北省西部,長江西陵峽兩岸,東與宜昌市夷陵區交界,南與夷陵區、長陽縣接壤,西鄰恩施自治州巴東縣,北接興山縣,是舉世聞名的三峽工程庫區第一縣。秭歸縣為渝東褶皺及鄂西八面山坳交會地帶,境內山脈縱橫,地形起伏,層巒疊嶂;同時也是荊楚文化、巴蜀文化及西南諸夷文化最集中的交匯地。
土家族薅草鑼鼓主要分布在九畹溪鎮、楊林橋鎮、磨坪鄉、沙鎮溪鎮、屈原鎮等鄉鎮。這些鄉鎮海拔高,落差大,多為山地旱田,主產苞谷,其次是小麥、土豆、紅薯和極少的水稻。
薅草鑼鼓歷史悠久,在民間普遍有兩種傳說,一說源于秦始皇修長城,由十二大學士作詞,配上鑼鼓,以解夫役們的勞累,以后被引入農田中;二說源于唐太宗,來自秭歸土家人民的口頭語“唐王游地府,制下鑼和鼓,拿到田中催農夫”。這些傳說尚不足據,但我們不必急于肯定或否定,有待進一步探究。
從文獻資料和出土樂器來看,《寰宇記案·甲乙存稿》云:“揚歌,郢中田歌也。其別為三聲子、五聲子,一曰噍聲,通謂之揚歌,一人唱,和者以百數,音節極悲。”此書于明景泰七年(1456)刊印面世,距今已有550年的歷史。時至今日,秭歸土家族薅草鑼鼓中的腔調名、唱和方式以及“極悲”的音節依然如故。宋代《東坡集》中載:“余來黃州,聞黃人二三月皆群聚謳歌,其詞固不可解,而其音亦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往返高下如雞唱爾,與廟堂中所聞雞人傳漏微似……土人謂之山歌。”音調的“不準”和“雞鳴歌”的唱法,現在仍生動地保留在薅草鑼鼓中,由此可推知至少已有900多年的歷史。另據湖北省《來鳳縣志》記載:“四五月耘草,數家共趨一家,多至三四十人,一家耘畢復趨一家。一人擊鼓以作氣力,一人鳴鉦以節勞逸,隨耘隨歌。”這是早期土家族薅草鑼鼓的真實寫照,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用的是鉦,還沒有鑼,那么,薅草鑼鼓的歷史可從鑼的出現來推斷。據考古資料可知,鑼最早見于廣西貴縣(秦漢時稱布山縣)羅泊灣一號墓出土的西漢初期的百越銅鑼,直到唐初方傳至中原。北宋陳旸在《樂書》中提及銅鑼在中原出現時說:“后魏自宣武以后,始好胡音。…… 打沙鑼。”據此推斷,薅草鑼鼓至少應有1500年以上的歷史,更毋論它在此前流傳多久了。
二、典型特征
秭歸土家族薅草鑼的鼓演唱內容極其廣泛,唱腔眾多,體裁不同,風格各異,鑼鼓牌子十分豐富。其看似一個紛繁而雜亂的大雜燴,但被智慧的勞動人民安排得井井有條,組成了一個有規律的、嚴密的有機整體。
(一)題材特點
秭歸土家族薅草鑼鼓的演唱內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人間百態、宗教信仰、花鳥魚蟲、飛禽走獸無所不唱。鑼鼓師傅們深諳此道:“只要能唱的就可打鑼鼓!”可謂是一幅生動的民族風情畫卷,一部反映秭歸土家族音樂及風土人情的百科全書。
其題材的特點是“聚歌成族”,鑼鼓師傅們精巧地將一些題材或比興手法相同的歌曲匯聚成一“族”,如以曉星、露水起興的許多歌曲,統稱為“曉星”“露水”;把不同形式的花或各種采茶為內容的歌,統稱為“花名”或“采茶”,既對唱腔進行簡便明了地分類,又極大地方便了演唱。每個歌“族”中有歌曲數首或數十首不等。秭歸薅草鑼鼓中的歌“族”主要有“曉星”“露水”“太陽”“陽雀”“花名”“采茶”“午時中”“五更”“送郎”“望郎”“探妹”“逢春”“月歌子”“懷胎歌”“交情歌”“十字歌”(包括《十愛》 《十勸》 《十寫》 《十夢》 《十送》等)。
在其唱腔中,僅同名、同“族”的歌曲就號稱有“48個拐聲”“48個陽雀”“48個午時中”“48個花名”“48個南京城的三姐”及“72個采茶”等。按曲調來計算,鑼鼓師傅少者能掌握百余首,多者三百余首唱腔。號子和揚歌是薅草鑼鼓的基本唱腔(或稱骨干唱腔),以“四聲號子”為例,其歌詞有數十首之多,根據不同的時段,不同的歌詞內容,又演繹出許多唱腔,再加上眾多的“散歌子”(又稱“雜歌子”),唱腔的數量就可想而知了,正如鑼鼓師傅所唱:“太陽過了河,陰涼上了坡,打不盡的鑼鼓,唱不盡的歌。”
(二)體裁特點
秭歸土家族薅草鑼鼓唱腔的體裁,基本上有板腔體的號子、揚歌和歌謠體的“散歌子”二種。號子和揚歌是其固有的主要唱腔,“散歌子”是大量吸收了當地的小調、燈歌、風俗歌以及花鼓戲的唱腔。這里主要論述號子和揚歌的特點。
號子又稱為“聲子”,它只能用高腔演唱,發聲高亢激越,有較強的節奏。號子的形態特征主要有三:一是反復演唱,二是具有“號子回頭”,三是必有“吆吙”(或“吆喝”“吆吙一呀吙”一類的襯詞)。如“四遍子鑼鼓”的號子就必須反復演唱4遍,每遍速度不同,從慢到快,第二遍后面插入“號子回頭我來接,我換歌師歇一歇”等小插句,俗稱“號子回頭”。“號子”的本義就是呼喊,“吆吙”是必不可少的。號子在薅草鑼鼓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主導地位,起著“主題”的作用。其唱腔眾多,形態、風格各異,全憑號子將各種唱腔串聯在一起,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使其既有變化又有統一,足見勞動人民的智慧和薅草鑼鼓非凡的藝術魅力。
號子數量較多,依據形態和功能,可分為主要號子(又稱“當家號子”或“打門槌”)、一般號子和偽號子。各種薅草鑼鼓的主要號子不盡相同,一般有4首,如四遍子鑼鼓的《四聲號子》 《獨腳號子》 《拐聲號子》和《大翻身號子》。一般號子不能代替主要號子在各歇鑼鼓開始時演唱,但能和主要號子唱其他唱腔時一起穿插演唱。偽號子數量極少,如《三聲號子》,它不反復演唱,更沒有號子回頭,不具有號子特征,實屬“歌子”,老藝人介紹:“只是把它借來當號子打而已。”除此之外,號子還具有指揮的作用,如唱了歇涼號子(煙號子、茶號子)、中飯號子或收工號子,大家就知道要歇涼、吃中飯或是收工了。
揚歌有三大特點,一是唱腔極其豐富;二是連帶其他唱腔演唱;三是結構龐大,形成套曲。揚歌也是高腔歌唱,音調高亢悠揚,節奏自由,在薅草鑼鼓中別具特色。全天只能在上午頭歇鑼鼓和下午頭歇鑼鼓時演唱,上午唱的稱“早揚歌”。
歌謠體的“散歌子”數量龐大,是號子、揚歌以外的諸多唱腔的總稱。其中以情歌為最多,花鑼鼓因此而得名,它的唱腔也被謔稱“無郎無姐不成歌”,如《交情》 《望郎》 《送郎》 《懷胎》《五更》 《十想》 《十愛》 《十寫》 《十繡》 《雪花飄》 《虞美人》等。如果把號子、揚歌比喻成薅草鑼鼓的骨骼,那么散歌子就是血肉了。
(三)曲體結構特點
秭歸土家族薅草鑼鼓唱腔的曲體結構多種多樣,既有單曲體,也有聯曲體的形式。號子和揚歌是薅草鑼鼓的主腔,其曲體結構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號子的單曲體,主要有單句子、上下句、三句子、四句子、五句子、穿五句、八句子等。在這些結構中值得一說的是穿五句,通常被稱為“穿號子”,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和巧妙的構思。它由“叫”和“穿”兩個獨立的唱腔組成,所以又稱“叫號子”“鴛鴦號子”。“叫”的部分是五言四句的號子(或“歌子”),被形象地稱為“梗子”,反復穿唱時其詞固定不變,比喻為樹的枝干;“穿”的部分是七言五句的“歌子”,被形象地稱為“葉子”,反復穿唱時隨詞而歌,猶如樹的葉子,更新速度很快。兩部分的歌詞既相對獨立,又存在有機的聯系,曲調、調式、節奏、風格等方面并存著共同的因素,它們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種新的曲體結構,可謂匠心獨具,意味深長,深受人們的喜愛。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穿五句一般被稱為“穿號子”,其實,五言四句的“梗子”是號子,才是穿號子;如果不是號子而是“歌子”,就不能叫穿號子而是穿歌子了。
號子的聯曲體,最經典的莫過于《幺姑娘沒蓄頭》,由號子和歌子連綴而成,全曲歌詞有80句,含有鼓里藏聲、五更、喇叭調等唱腔,曲體結構包括了四句子、三句子、五句子、二句子等,并且調式變化頻繁,由本調(E調)向上方小三度轉調,然后回到本調,再向下方小三度轉調,再回到本調,生動地表現了一個小姑娘的成長和出嫁的過程。由于號子的特性,使薅草鑼鼓形成了一個復雜的“回旋曲式”。在全天的演唱中,以號子為主干,猶如交響樂中的主題,首先演唱《當家號子》作呈示部分,以后將各種號子不時地穿插、貫穿在全天的演唱中。其結構圖示如下:
A(當家號子) →B(如太陽歌) →A1(當家號子或其他號子) →C(送郎歌) →A2(當家號子或其他號子) →D(如花名)→A3(當家號子或其他號子) →E(如午時中) →A4(歇涼或中飯或收工號子)
揚歌是聯曲體形式,只有五句子和二句子兩種,一旦和其他唱腔連綴,就形成聯曲體和套曲,變得異常復雜了。單唱揚歌必然有頭有尾,由三個唱腔組成:揚歌頭→揚歌→揚歌尾(或稱收揚歌)。揚歌具有連綴其他唱腔演唱的特性,這是其他唱腔不具備的特殊功能。例如,“揚歌帶板”,后面連帶號子演唱的叫“揚歌帶號”,連帶采茶歌演唱的叫“揚歌帶采”,連帶贊歌演唱的叫“揚歌帶贊”,連帶花鼓戲演唱的叫“揚歌帶戲”,還曾帶《黑暗傳》 (20世紀80年代民間文藝工作者的重大發現,《黑暗傳》結束了此前學術界漢族無創世紀歌謠傳世的論說)內容演唱等等。揚歌還和其他多個唱腔聯結演唱形成套曲,甚至是套中有套的大套曲,這樣結構就非常精彩了,這在我國民歌中是極其罕見的。例如,揚歌與“逢春”(也是個有頭有尾的小套曲)、“家雞公”“南京城的三姐”等其他唱腔聯結,其結構圖示如下:
揚歌頭→揚歌→逢春頭→逢春(十二月逢春)→家雞公(可作逢春尾)→揚歌→揚歌尾。
或者是套著陰、陽、搖、贊唱腔演唱,結構示意如下:
揚歌頭→陽歌→贊歌→提歌→陰歌→搖歌→揚歌尾。
(以上兩例皆可在頭尾之間任意反復演唱。)
(四) 音調特點
秭歸土家族薅草鑼鼓的唱腔有兩種音調體系,一種是叫人感到“怪異”,不識音高、不辨調式、不好記譜、不易歌唱、不見經傳,給人以“悲”感的“巴楚古音”體系[1],另一種是現在普遍流傳的一般音調。經考證,“巴楚古音”體系的唱腔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是巴楚古音的遺存,被譽為“巴楚古音活化石”。其突出的特點是在音階中含有一個介于大、小三度之間的音程,并有2-3個“不準”的音(所謂的不準,只是相對于純律、五度律和十二平均律而言),這種音調體系,尚保存在秭歸縣、興山縣等地。秭歸縣與興山縣山水相連,原為一縣,吳景帝三年才拆北界立興山。至今兩地民風民俗相同,唱腔一樣,且兩地只有兩種“三音歌”。 這種音階的音律結構,不是建立在固定的、整體音階關系之上,而是建立在相鄰音級進行的關系之上。
(五) 旋律特點
當地人們習慣于“以腔從詞”和 “以詞配曲”這兩種歌唱方法,所以形成了秭歸土家族薅草鑼鼓以下四種不同的旋律特點:
1.語調旋律:當地人們用自己的方言聲調念歌詞而產生的字調就是語調旋律。它是人們唱民歌時習慣于使原唱腔曲調服從于自己方言的聲調的必然產物。
2.韻調旋律:人們用念白方式唱歌叫韻調旋律,韻調旋律的樂音音韻單純,韻味爽朗,節奏緊湊,這種旋律人們又稱為“趕句子”。它接近于語調旋律,其區別在于:語調是“念”歌詞產生的字調;韻調是口語化的“唱詞”。
3.歌調旋律:又叫歌曲旋律,就是歌曲或者絲弦小曲的旋律。
4.唱腔旋律:以節拍自由、拖腔長、高亢悠揚為特點,在曲式結構上有較為明顯的戲曲聲腔特征。
上述4種不同特點的旋律可以分為單一形式和交替組合兩種結構。“語調”“韻調”和“唱腔”3種旋律,在薅草鑼鼓中以交替組合的結構形式出現,尤其是唱腔旋律與“語調”或“韻調”的交替組合,既便于抒情敘事,又使薅草鑼鼓情趣生輝。
(六)演唱特點
秭歸土家族薅草鑼鼓有一定的演唱程式,包括程序性和時序性兩方面,特別是演唱的程序性是判斷薅草鑼鼓原始性的重要標志。無論早晨、中午或歇涼后下田,都要首先按順序演唱“當家號子”(歇涼后可不必唱全),并且在全天的演唱中,必要插入一首至數首號子唱腔(包括“當家號子”和其他號子),造成“整天不離號子聲”的藝術氛圍。嚴謹的演唱程式,使其形成了一個封閉的、牢不可破的保護外殼,從而保持了秭歸土家族薅草鑼鼓的原始面貌。
秭歸土家族薅草鑼鼓同時具有嚴格的時序性。演唱內容依天時而定。如早晨唱“曉星”“露水”“太陽”等,中午唱“午時中”“吃了中飯”等,傍晚唱“太陽下山”等與之發生關聯事項的歌,如果唱錯了時序,會遭責罵、嘲笑:“不知天日”“公雞打鳴不識時”。
秭歸土家族薅草鑼鼓多用高腔演唱,這種唱法一人無法唱完一曲,而每句唱完后,必要其他人來“搭氣”(接腔),故采用疊唱的方式。由于高腔演唱,往往出現“雞鳴歌”(模仿公雞的打鳴聲)的效果,“雞鳴歌”至今仍鮮活地保留在秭歸高腔薅草鑼鼓中。
薅草鑼鼓中的演唱都是以鑼鼓師傅為主,“四遍子鑼鼓”全天都由鑼鼓師傅演唱,而“三遍子鑼鼓”和“五遍子鑼鼓”唱揚歌時,薅草人便與鑼鼓師傅對歌。鑼鼓師傅“陰”一個歌,帶一個“搖”的答唱,然后鑼鼓師傅再“陽”一個歌,帶一個“贊”,再“提”一個歌題,讓薅草人來對。
秭歸薅草鑼鼓歌唱的發聲方法大致有三種:一是假聲高八度的歌唱,俗稱“大放聲”,或稱“窄音”“高腔”“鬼音”“尖音”“天堂音”和“頂音”;二是真聲高八度的歌唱,俗稱“小放聲”,或稱“禿音”和“滿口音”;三是用真聲低八度歌唱,稱為“二黃”。“尖音”和“禿音”是基本唱法,“二黃”只有鑼鼓師傅唱累了才用此法。因此也就有高腔(唱尖音)鑼鼓和平腔(唱禿音)鑼鼓之分,如秭歸楊林橋鎮、磨坪鄉的高腔鑼鼓。
(七)伴奏樂器特點
秭歸土家族薅草鑼鼓的基本伴奏樂器是大鑼和小鼓兩種。鑼較大,直徑42厘米以上,鑼邊較寬,約3.3厘米,鑼板較厚,發音低沉曠遠。大鑼較重,為了長時間在田中演唱,都是用一根曲尺形的樹棍作鑼桿,杵于地面,鑼掛其上。鼓的高度一般在16.5厘米左右,鼓面直徑約23厘米,發音焦脆。鼓都是農村扎鼓匠制作,鼓盆用整段核桃木,按尺寸畫線后將其挖空,然后蒙上牛皮。鼓皮選用4歲以上的水牛皮,以肩胛骨部位的為最好。薅草時,鑼鼓聲在山間回蕩,傳得很遠,焦鼓沉鑼的音色別有一番情趣。大鑼和小鼓圖片如下:

鑼桿上的大鑼

鼓
挎鼓方式有兩種,一是鼓繩斜背在右肩上,左手從鼓繩中穿出,左腿微屈,腰稍前傾,小鼓靠在大腿上,鼓面向上。鑼鼓師傅對其姿勢有極好的寫照:“鼓兒七寸高,凳在膝蓋垉,雖說不打緊,榨得弓起個腰。”一種是鼓繩較長,擊鼓發出“叭啷”之聲,故又稱“叭啷鼓”。
鼓可以發出多種音色,如敲擊鼓心發出“嚨、咚”之聲,敲擊鼓旁發出“噹”聲,敲擊鼓邊發出“噠”聲,一槌按鼓心一槌輕擊鼓面發出“噗”聲,還可鼓槌互擊,發出“替”的聲響。大鑼用二面時,一般選用兩種不同的音色,以便演奏“抱子鑼”(二面鑼相間演奏地結合在一起),還可由打鼓者敲擊鑼邊,稱“帶鬧子”。雖然只有兩種樂器,但多種音色的組合,其效果耐人尋味。有的地方除了鑼鼓外,還增添了其他一些樂器,如郭家壩等地加上了鈸;歸州加上了鈸、馬鑼,稱為四樣鑼鼓(或打四件);茅坪、沙鎮溪等一些地方加上了勾鑼、馬鑼、笛子等樂器;屈原鎮加上了1至2支嗩吶(稱吹鑼鼓),嗩吶選用中音嗩吶或海笛,只用6個音孔(俗稱“六音子”),運用循環換氣法吹奏,還有的地方加上了二胡、镲子等樂器。
鑼鼓的配置視薅草人的多少而定。配置最小的是單鑼鼓(一鑼一鼓),從小到大依次是夾鑼鼓(一鑼二鼓)、雙鑼鼓(二鑼二鼓,又稱對子鑼鼓)、夾心單(二鑼三鼓)、夾心夾(三鑼三鼓)等。“鑼鼓半臺戲”,薅草鑼鼓同樣如此。其作用:一是歇氣(嗓子休息),二是烘托氣氛,三是豐富唱腔。薅草鑼鼓的鑼鼓牌子非常豐富,約有七八十種之多,各個唱腔都有各自的鑼鼓牌子,即唱什么歌打什么鑼鼓。其中有一些趣味性的擊鼓動作,如“黃楊樹栽跟頭”,擊鼓中按節奏將鼓槌高高地拋起,并使其翻轉數周后接著繼續打;又如“狗刨騷”(龍現爪),擊鼓時鼓槌在鼓面上由前至后的劃動,學狗子刨地狀;還有鑼鼓經似的“斗打鐵”等。
“腔落板,板落腔,停腔落板把歌唱。”鑼鼓與歌聲的配合,有三種形式:“鼓里藏聲”(又叫連鼓連聲),邊演唱邊打鑼鼓,歌聲與鑼鼓交融在一起,氣氛熱烈,多用于號子;“住鼓聽聲”(又叫歇鼓接聲),演唱時不打鑼鼓,鑼鼓只作過門用,氣氛清新,多用于散歌子;“鼓里岔聲”(又叫鼓里切聲),歌聲的局部配以鑼鼓,多用于揚歌。
三、研究價值和搶救保護
秭歸土家族薅草鑼鼓在整個民間音樂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的研究價值主要在于:
1.學術研究價值。薅草鑼鼓是在巴楚文化融匯的大環境下形成的具有自身獨特個性的民間藝術品種,也是巴楚古音傳承的優良載體,一旦消亡,眾多的傳統民歌,特別是巴楚古音體系的民歌也將隨之絕響。薅草鑼鼓的保存,為研究本地民風民俗、語言文學和民間藝術提供大量材料。此外,土家族薅草鑼鼓包含有一定的古文化信息,其中不少的謎團還有待解開。
2.文化傳播價值。薅草鑼鼓保留了我國古代音樂文化的傳統基因,對于我國傳統音樂和歷史文學具有很高的文化傳播價值。
從現場調查來看,土家族薅草鑼鼓已經很少有人演唱了。秭歸縣已經不足30個班子,會唱鑼鼓歌的人,所占比例不到人口的10%,并且多為50歲以上的老年人,約占70%左右。究其原因如下:
1.傳承后繼乏人。受現代文明的沖擊,薅草鑼鼓藝人年事已高,老藝人相繼謝世,青年人的審美觀念和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已經發生了改變,不愿意學習薅草鑼鼓,傳承面臨后繼乏人的困境。
2.生存環境受限。隨著改革開放和農村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形成了單家獨戶的勞作,每戶土地面積都不大,使薅草鑼鼓失去了生存空間。
3.勞動方式改變。現在農村中除草,已普遍使用了“草甘膦”等除草劑。農業科技的進步,導致薅草鑼鼓不得不退出歷史舞臺。
4.經濟利益驅使。現在種田的收入,一畝田年收入最多不過一千多元,而外出打工,人均一個月就是二、三千元,農村青年紛紛外出打工。
這種現象的產生,一方面反映出現代化的農業和機械化的操作時代已經到來,另一方面卻讓人們不得不面對薅草鑼鼓社會性的自然消亡,因此搶救和保護薅草鑼鼓傳統藝術形式也就成為文化多樣性的必然要求和社會傳統文化發展的重點。針對上述情況,筆者提出幾點建議,以期這種現狀能得到一定的改善:
1.成立搶救保護專班。建立專班、專人負責。建立薅草鑼鼓傳承人的檔案,搜集、整理薅草鑼鼓原始曲譜、歌詞作品等,并制作成系統的電子文本、數碼資料。
2.搜集資料整理出版。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秭歸縣宣傳文化部門組織力量進行了4次大規模的普查,先后整理了《秭歸民間音樂集成》 《秭歸民間文藝選粹》。還需要進一步廣泛開展民間文化普查工作。
3.每年開展秭歸全縣民間大型文藝匯演、鄉鎮民間文藝調演和薅草鑼鼓的圖片展覽等活動,促進薅草鑼鼓的傳承。
4.將薅草鑼鼓唱腔或者曲目編入秭歸縣中小學的鄉土教材。
5.在各大媒體中廣泛進行宣傳,擴大薅草鑼鼓的知名度和社會影響。
6.切實保護薅草鑼鼓傳承人,為他們提供必要的醫療和生活補貼,使其能夠薪火相傳。
結 語
秭歸土家族薅草鑼鼓是勞動人民在薅草勞動過程中展示和表演的民間傳統音樂活動,它既是一種生產習俗,也是在巴楚文化融匯的環境下形成的具有自身獨特個性的民間藝術品種。秭歸土家族薅草鑼鼓原始質樸,是巴楚古代音樂文化傳承的載體,保留有較多的巴楚古代音樂文化信息,為進一步研究我國古代音樂及其發展、演變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本文的寫作承蒙王慶沅老師提供的資料并予以幫助,特致感謝!)
[1]王慶沅,盧天生.荊楚古音考[J].音樂研究,1988(4).
A REPRESENTATIVE OF MILLET CULTURE:A STUDY ON TUJIA WEEDING GONGS AND DRUMS IN ZIGUI
Yuan Yue
As a representative of millet culture,playing weeding gongs and drums,reflects the production,life,thoughts and feelings of laboring peopl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It is the deep accumulation of ethnic culture and spirit,and an excellent media to preserve Bachu's ancient music.With the change of social progress,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labor patterns,this culture will disappear naturally and inevitably.Consequently,the rescue and protection of this traditional art form has become a vital task to keep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uJia culture;weeding gongs and drums;millet culture;traditional music;Zigui society
袁麗紅﹞
【作 者】袁玥,中國地質大學(武漢)藝術與傳媒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武漢,430074
C955【文獻識別碼】A
1004-454X(2017) 06-0039-007
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三峽庫區秭歸民間音樂的調查與保護傳承研究”(15YJC760122)。
———評《土家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