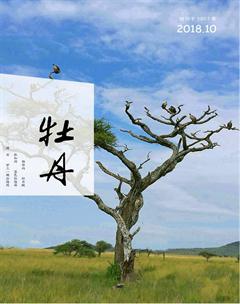與亡靈同柩
王思維 吳堯
本文運用文本細讀手法,從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對比分析《聊齋志異》和《佩德羅·巴拉莫》中的亡靈世界及生死轉化的歷程,隨即從文本上升到文化層面,結合作者生平經歷與中墨兩國思想文化傳統,揭示兩部作品所蘊含的死亡觀念在內在生成機制上的差異。
未知的死亡世界帶給世人恐懼與無盡的想象。作為生命體的必經階段,死亡也成為不同文明難以逃避的話題。蒲松齡《聊齋志異》和胡安·魯爾福《佩德羅·巴拉莫》兩部時代與文化背景不同的作品卻呈現出相似的論調——生死無界,這不禁令人遐想。
而傳統的比較研究中,主體的“先驗圖式”對他者文化進行過濾,比較研究最終淪為自我言說以及對特定意識形態的建構。在中國與歐美主流文學的對比中,研究者或是服從西方思想范式,或是進行帶有話語權爭奪意味的本土化探索,處于來回搖擺的位置。而中國由于近代以來與西方長時間二元對立的微妙關系,對于拉美的認識往往基于對傳統歐美國家的想象。本文在探討兩部文學作品的共同話題——死亡觀時,對“中心化”的自我認同模式進行反思,力圖進行不設主客的平等比較,挖掘兩部作品及其文化內涵的獨特性。
一、死亡觀之差異表現
死亡觀即人對死亡以及死亡價值的根本態度與看法。通過文本細讀對《聊齋志異》和《佩德羅·巴拉莫》中的亡靈界環境與情節設置進行梳理可以發現,兩部作品背后均潛藏著“生死無界”的觀念。下面擬從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對小說文本中的死亡觀念進行探討和對比。
(一)死亡觀的空間依托
1.與現世對立的亡靈世界
《佩德羅·巴拉莫》和《聊齋志異》都描摹了結構完備的亡靈世界,但兩部作品中亡靈界具體架構差異明顯。
《佩德羅·巴拉莫》中,胡安·普雷西亞多死后被多尼斯、多羅脫阿埋進地下,胡安的活動范圍遭到局限,僅能依靠聽覺獲知周邊環境,情節發展主要依靠對話、內心獨白推動。在地上、地下世界之外,更有“煉獄”“地獄”的存在,地下世界是人通往煉獄乃至地獄的過渡地帶,地下世界埋葬的是人的肉體,而未經救贖的靈魂則在地上飄蕩。
《聊齋志異》中,陰間的鬼魂可以到陽間與人交往。人鬼相戀相守的情節在書中屢見不鮮,鬼魂在人間生活如常,但也有一些禁忌不能觸碰;有時,鬼魂甚至還能將人帶回陰曹地府;鬼卒到陽間捉拿罪人,罪人直面閻王審判,隨后留在陰間遭受折磨或者返回陽間贖罪,這也是《聊齋志異》中較具代表性的情節模式。陰曹地府和陽間官府暗含對應關系,皆為社會秩序的捍衛機構,均承擔行政、司法等職能,也呈現出類似的貪污腐敗問題(《席方平》一篇中,由于城隍收受賄賂,席方平父親之冤久久不得伸張,直到二郎神出面解決問題)。陰陽官府有時甚至能夠相互干預,例如《潞令》中,陰曹官員兼理陽間事務,對暴虐的官吏進行了懲罰。陰陽兩界的相互應和,還體現在陰間科舉選拔上——《于去惡》中冥界也有參加入闈考試的士子,而且科場和陽間一樣骯臟迂腐。從以上的一系列對比可以看出,《聊齋志異》中的亡靈界并非天馬行空的思想產物,蒲松齡懷著現實的憤懣,幾乎將陰間描繪成了人間的“平行世界”——陰陽兩界同樣有強者對弱者的傾軋,但也同樣遵循因果報應的法則。
如前所述,兩部作品展現的死亡世界既有相似之處,又有本質上的差異性。共同點在于,兩本書中都存在死后的地下世界,但也并不妨礙陰間鬼魂在人間飄蕩。不同點首先在于亡靈界的內部構造:《佩德羅·巴拉莫》中所謂的“地下世界”只是死者肉體停留的中間站,靈魂接受上天審判后會面臨上天堂、下煉獄、下地獄三種結果;《聊齋志異》中的冥界與人間構成平行對照關系,靈魂接受閻王判決后依據罪行輕重在十八層地獄中接受相應刑罰,然后通過還魂、投胎、附身等方式返回陽間。從根本上講,二者植根于迥異的文化土壤,前者是天主教教義、阿斯特克生死觀、革命歷史碰撞結合的產物,后者則立足于我國上古“靈魂不滅”的觀念以及儒、釋、道三家交融的文化環境。
2.生死在空間上的可跨越性
《佩德羅·巴拉莫》一書以胡安·普雷西亞多的死為分界。胡安去世之前,他以活人身份誤入“死人村”,而在胡安去世之后,作者則描寫了一個地下死人場。
胡安·魯爾福在小說中構建出的地下、地上世界,看似是生與死的分割,但死后的人們仍舊可以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之間穿梭、游蕩。半月村民死后身體被埋藏在地下,靈魂則在世間游蕩,尋找活人來為他們祈禱。于是,當胡安·普雷西亞多來到半月莊時,看到多年來唯一到訪此地的活人,村民們自然“要熱鬧一陣了”,不斷有亡靈從地下世界來到地上世界,請求胡安來替他們向上帝祈禱,從而擺脫這樣日夜游蕩的日子。
《聊齋志異》一書中,魂魄滯留人間的故事比比皆是,但其滯留的原因各有不同。《葉生》一章中,葉生因對知遇之恩的感懷而不知自己已死留在人間;《牛成章》一篇中,逝去的父親因擔憂遺留的孩兒而繼續在人間生活多年……此外,《聊齋志異》中同樣不乏活人到陰間的故事,如《考弊司》一篇中,聞人受邀前往陰間考弊司替鬼向司主求情,辦完一切事務后返回陽間時發現自己已死去三日,后重回身體方才蘇醒過來。
在蒲松齡的筆下,死人魂魄可因生前羈絆而在人間游蕩,也可通過附身、投胎等方式重回陽間;而活人的魂魄同樣可以暫時前往陰間,只是當其魂魄離身時,肉體便已呈現死態。
(二)死亡觀的時間形態
在生死轉化的路徑層面,《佩德羅·巴拉莫》和《聊齋志異》展現出線性生死觀和循環生死觀的差異。《佩德羅·巴拉莫》中,活著是一個短暫的階段,而死亡卻是永恒的狀態,呈現出“生→死”的線性結構。盡管存在“地獄—煉獄—人間—天堂”的層級設置,但事實上小說中沒有任何人獲得拯救升入天堂,絕大多數靈魂因罪孽得不到寬恕而游蕩于世,游蕩最終也會變成一片沉寂。平生作惡最為多端的佩德羅和米蓋爾甚至直接跳過了靈魂游蕩的環節,徹底湮滅了蹤跡(小說對這兩位人物的行為描寫在他們生命結束后戛然而止,或是暗示二人的靈魂走向死滅的終極)。死者寄希望于活人的禱告,但正如小說所反映的,胡安進入科馬拉這個“死人村”后,不僅無力應對“替我們求求上帝吧”的嗡嗡聲響,而且反倒宿命般地被這些“輕聲細語”殺死。正如埋在地下的多羅脫阿所說,科馬拉村民的生命具有單向性——“我這邊的門已給關死,另一邊的門雖開著,卻通向地獄……天堂對我來說,就是我現在所在的這個地方”。
而《聊齋志異》中,死亡只是過渡階段,再度還陽的可能得以保留,呈現出“生→死→生……”的循環結構。贖罪的渠道未受阻塞,罪人在閻王處接受審判,經歷刑罰后即可轉世,人間官府的律令(《酆都御史》)、死者親屬的求情(《鬼作筵》),甚至能加快死者重返人間的過程。
《佩德羅·巴拉莫》中有“死期”一說,生者可加快速度趨近死的終點(例如,愛杜威海斯所言,“你愿意死,只要告訴一下上帝就行了;若是不愿意,那上帝可得強迫了。再說,你若愿意的話,還可以請上帝早點安排……我將在某一條走向永恒的大道上趕上你母親”),但不可倒退返生。而《聊齋志異》中,“生期”“死期”仿佛四季節令,人之生死循環如自然流轉,規律不可撼動。
二、死亡觀之差異原因
(一)作者際遇及表現形式
蒲松齡出身敗落的書香門第,科舉屢試不中,落魄書生的身份使他對炎涼世態感同身受。清初,統治者為了鞏固統治,對主張“反清復明”的人士嚴酷鎮壓。在風聲鶴唳的氛圍下,讀書人稍有不慎則命不保矣,這使得知識分子普遍不敢議論現實,只能埋頭書齋做考究學者。封建社會末期,官僚制度極其腐朽,黑暗的社會現實無法在作品中直白表現,蒲松齡只好以鬼寫人,以冥官寫真官,并通過善人死后被封為神仙,惡人死后投胎做牲畜的描寫警
喻世人。
胡安·魯爾福在墨西哥革命期間出生,六歲時其父在農民暴動中慘遭殺害,戰亂和死亡構成他人生的最初記憶,革命狀況和農民的苦難是貫穿他創作生涯的關鍵詞。魯爾福的第一本小說集《燃燒的原野》集中描繪了農民起義軍遭遇追趕、鎮壓的殘酷場景;《佩德羅·巴拉莫》中,革命軍進入半月村,實施血腥掃蕩——“軍隊把留在村里的那少數幾個人都消滅了”。作家在小說中構建的“死人村”,極有可能并非想象和夸張,而是對駭人現實的忠實描摹。
同樣是混亂社會環境對個體的沖擊,兩部作品卻采用了各異的表現形式,這與不同文學傳統對個體思考表達方式的規范與塑造不無關系。中國古典小說在文體結構和敘事手法方面深受史傳文學影響,《聊齋志異》篇末“異史氏曰”直接取法乎司馬遷《史記》“太史公曰”,篇末議論成為蒲松齡泄憤及針砭時弊的出口,借亡靈鬼事諷現實陰暗、著孤憤之書的意圖較為明顯。《佩德羅·巴拉莫》這部中篇小說則并無作者議論干預的空間,相較于前作《燃燒的原野》對墨西哥革命后農民的悲慘遭遇進行偽紀錄片式的現實主義書寫,胡安·魯爾福在《佩德羅·巴拉莫》中進行了大量文體創新,如意識流和蒙太奇式場景轉換,作者的生死觀念在作品中發生折射變形,掩藏于紛繁復雜的文本脈絡及其營造的魔幻氛圍之中。胡安·魯爾福在這兩部作品中所呈現出的轉變,受益于其豐富多變的人生經歷——胡安·魯爾福多年從事攝影和電影制作的經歷極大地影響了他的創作風格,無論是攝影式的靜物描寫還是電影分鏡式的小說架構,在一定程度上都可追溯于此。此外,福克納和拉克斯內斯對《佩德羅·巴拉莫》作品風格的影響也不容忽視,或者說,胡安·魯爾福意識流的創作方式和對于時空的破碎性刻畫是福克納寫作風格影響的結果。
(二)中墨思想文化傳統的差異
《聊齋志異》中的亡靈世界是我國古代靈魂不滅觀念和佛教因果報應思想澆筑的產物,同時又與儒道精神緊密相連。一方面,據出土材料,中國早在舊石器時代就有靈魂不死之說,而殷人更是以鬼神信仰著稱。三國之后,佛教地獄概念開始傳入,并出現了“十八層地獄”等表述。“十八層地獄”層級區分不在空間高低,而在刑罰輕重長短,《聊齋志異》中便存在對各式酷刑的生動描寫,比如《續黃粱》中,曾孝廉因犯“欺君誤國之罪”,遭受油鍋刑、刀山獄,而在《席方平》中,席方平為冤死的父親“代伸冤氣”,觸怒冥王,被處以火床刑、刀鋸獄。另一方面,儒家向來有重生輕死的世俗傾向,即便刻畫鬼神,也終究難舍現實世界,因此地獄成為人間的摹本,消逝的生命試圖以循環方式重歸現世。盡管城隍一貫被道家奉為俗神,但城隍廟的建造從明太祖開始便得到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政府的大力支持,城隍廟采用行政機構的名稱和層級,主要起警示教化、維護秩序等作用,這在《聊齋志異》陰陽兩地的二元對照結構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佩德羅·巴拉莫》地獄、煉獄、人間、天堂的劃分與但丁《神曲》有異曲同工之妙——罪大惡極者下地獄,有罪但可獲寬恕者進煉獄,唯有無罪的靈魂方能進入天堂。《現代性的神學起源》一書指出,中世紀基督教思想家認為“世界有特定的開端、發展和終結”,“時間并非永無休止地循環下去,而是始于失樂園,終于復樂園”,一種具備“現代性”之嶄新和變動意味的線性時間觀早有端倪。
天主教思想在墨西哥的本土化體現在墨西哥人對“死亡圣靈”的崇拜。墨西哥文化中,“死亡圣靈”往往以盛裝打扮的骷髏形象出現,而這具不再體現種族、性別等等級差異的骷髏則成為了與特權階級的對話者,它總是同其他的天主教圣徒,如基督、圣裘德等一同生活在祭壇中心,直接面對上帝。墨西哥人在天主教中注入本土文明的特殊之處,從而令天主教更好地成為墨西哥人的慰藉,同時展現了自己虔誠的信仰。“死亡圣靈”成為墨西哥特有的神靈形象,但此形象出現的目的是撫平墨西哥人的種族差異,從而成為與上帝對話的“中介”。
胡安·魯爾福筆下,“升上天堂”是所有人最終的追求,若不能“升入天堂”則靈魂只能終日在人間游蕩,于是他們需要找到“活人為他們祈禱”,從而幫助他們化解世俗中的罪孽,實現最終的目標。而在小說所描繪的這個場景中,為亡靈祈禱的活人實際成為亡靈與“上帝”對話的中介,從而表達了墨西哥人在信仰面前的虔誠,面對曾經過錯而內心不安時,努力尋求精神慰藉。
除了天主教的影響,《佩德羅·巴拉莫》亡靈世界的構建還與阿茲特克文化傳統有關。一方面,阿茲特克人將宇宙視作橫分、豎分的兩個世界,豎分的世界包括十三層天堂和九層地獄。“阿茲特克人沒有進地獄贖罪之說,因為除了戰死者、犧牲者、分娩而死者或淹死者之外,其他所有的人死后都要到地獄里去”,在走完地獄的艱險旅途后,“死者之主”將會安排死者的歸宿。如若再考慮到阿茲特克人對大自然周而復始運行規律的敬畏,以及犧牲個體從而成全整個種族生存未來的傾向,他們應該是將個體死亡視作自然及人類社會發展周期的一環,亡靈世界是個人必經的歷練。
三、結語
本文對《聊齋志異》和《佩德羅·巴拉莫》的共同問題域——死亡觀進行了平行比較。空間方面,兩部作品呈現出內部結構差異明顯的亡靈世界,但魂魄都有在死界和人間穿梭的自由。時間方面,《佩德羅·巴拉莫》的主要人物面臨由生到死的單向歷程,《聊齋志異》生與死兩個因素則保持著四季節令般的交替循環。
文本分析之后,本文試對兩部作品死亡觀差異進行根源探究。在創作個體方面,相似的艱難時世一定程度上將二位作者導向對于死亡觀的書寫,但文學滋養源流的不同則深刻影響了他們對死亡觀這一題材的反映形式。在思想傳統方面,兩個文學文本背后各有諸多因素密切交織,《聊齋志異》的死亡觀念是上古靈魂不滅思想和儒釋道精神混雜的產物,天主教時空意識以及天主教在墨西哥的本土轉化影響了《佩德羅·巴拉莫》的死亡觀呈現,阿茲特克文明構建世界與面對死亡的方式亦在作品中留下痕跡。
(1.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2.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