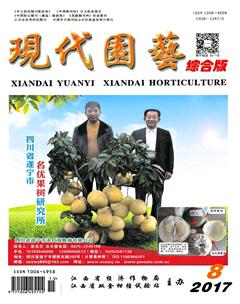當代視覺藝術如何走向自律
摘要:過去三十年是充滿變故的時代,視覺藝術也在上個世紀逐步獨立起來,不再是形象的附屬。從視覺藝術本體來看,它逐漸擺脫文學性,進而逐步擺脫音樂性,視覺藝術逐漸成為一個自律的學科。語言學和符號學又從內在、外在等各個方面促進了視覺藝術的蛻變與發展,將它看作一個特定的運作系統,以滿足視覺規律。科學的進步使我們觀察和認識世界同過去有著本質的區別。藝術家們懷揣著形形色色的策略來思考視覺藝術在新的理解力中應該作何呈現。文章通過對當代藝術外在語言形式和內在精神現象的探討,來分析視覺藝術是擺脫怎樣的束縛而實現自律的。
關鍵詞:語言;文學性;科學;精神性;自律
當代視覺藝術融合了豐富的形式、多樣的主題和獨特的審美,是十分復雜、不一而足的。現代以后的視覺藝術的定義、目的和形式發生了新的轉向。藝術家的創作意圖很復雜,一者是許多藝術家第一職業或者曾經的職業都是與藝術不大相關的行業,另外科技與信息的發展使學科之間聯系更為緊密,使得他們重視創造與藝術圈之外的世界有密切聯系的作品,正是在這樣的環境框架內,視覺藝術自律的發生出現了切入點。
“自從藝術被公認為是一個自律的學科以來,其面臨的主要難題就是話語對視覺的統治。”視覺藝術在久遠的歷史中積淀、創造了自己特殊的表達體系,這可以看做是作品的內在語言,對于這部分語言,往往是藝術家們在自己的藝術宣言(文字語言)中寫下的原則和目標,目的是給自己的作品的闡釋提供背景,供人們在作品中尋找內在矛盾、隱含意義和暗示性的意識形態。但這種語言也使得作品面臨一個問題:人的一種表達方式需要另一種表達來闡釋,這對視覺像是一種諷刺——承認文字語言是凌駕于視覺語言之上。意識到這個問題,二十世紀中期誕生的具象詩啟發了當代視覺藝術家制作出就詞語如何能從傳統文本的線性排列中解放出來進行了實驗,這些具有革新性的實驗讓視覺藝術“反叛”地使語言成為一種表征,我們試圖去理解文字的含義或許就“中計了”。這類藝術家橫跨文學和視覺兩個領域,使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視覺屬性的種類和范圍被擴展了,隨著這種擴展,文學和視覺藝術之間的區分或許不再有效,我們或許不可能杜絕文字對視覺強加的意志,但模糊的邊界已經在起作用了。
一定程度上由于符號學和語言學廣泛地應用在視覺分析上,視覺被看做是語言的一類。語言學為破譯交流提供了系統的方法,當代藝術家參考于此認為,語言發生了實質性的轉變,語言就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掌握規律就可以參與的游戲,學會語言并不足以學會如何說話,語言不再被看作是思想的傳達工具,它只是結構性的系統性的網絡,它形成了一個場,思維在這個場里得到具體化的體現。換而言之,視覺不再是對他者的解釋,而是對其本身的解釋。所以視覺作為語言的一種,它有自己的場域,在人類思維過程中與其他語言居于平等地位。通過對文學性的剝離與語言概念的介入解決了視覺藝術面對文本的被動,這也促使視覺藝術獨立的價值體現出來。
20世紀以來,科學的介入與精神的改造也在不斷影響著視覺藝術走向自律。科學的技術進步、范式轉變和意識形態的變化對文化的影響從古至今都存在,在形式上,藝術家吸收科學工具材料和概念,通常以七拼八湊的挪用方式融入到他們的藝術中,他們的標準只是文化標準,不用科學計量;從創作的動機上來看,科學提供了“因為伴隨著技術進步而來的全新研究領域和經驗性觀察的新機遇”。科學對藝術的影響不僅是本身創造了新的視覺內容,還有科學進步對我們精神世界的改造。當代人與前幾個世紀的人理解世界的區別不是認識的量的區別,而是質的區別,這使得我們在認識宗教、神學、意識、精神等方面有著新的基礎。同時因為藝術從古典時期之后走下神壇,人們不再對某一張畫“頂禮膜拜”,視覺藝術自然出現了快消品的特性,接著面對架上繪畫已死的“叫囂”其必須向著比情感之類的更深層的含義走去,任何時候藝術作品都是藝術家的另一種存在形式,藝術家對自我、意識、精神的探尋都反映在作品中,這種探尋具備了視覺藝術獨特的無法被替代的品質,這無疑使視覺藝術通過表層進入了更深層次的精神世界。
科學的進步讓人們在探討藝術里精神的含義時更加靠近我們希望得到的真實,是一種新的知識基礎之上的“上帝視角”所觀察到的結果。但事實是精神無法被量化,我們雖不能否認它的無處不在,可是也不能知曉其全貌,所以也往往把它界定為是不可知的。當我們面對一件抽象作品,經驗和知識都不再在判斷中起作用,直覺的感受是判斷依賴的條件,這種東西是不可解釋的,馬列維奇說:“在至上主義看來,自然物像的表面本身是無意義的;本質的東西是感覺——在本質上完全獨立于產生它的世界。”命名、描述和定義當視覺藝術的語言及方式,都無助于我們理解它的意思,它是視覺的現實,是精神、觀念的直接輸出,不是任何再現,不對他者負責,作品的完成代表著其自身的終止,其之外的他者表述都不可能再現甚至覆蓋它本身。它不像現代主義及之前的作品一樣建立一個通往審美愉快的捷徑,而是直面真正藝術所必須面對的困難——視覺本身。
當然,即便有可能探究自律的成因和途徑,但也不可避免地看見許多當前的藝術潮流正在發展甚至剛剛起步,現已完成的作品可能并非是藝術家的最終訴求,但重要的是雖然當代藝術作品的解讀意義是開放的,但是我們最多只能去客觀地描述它。當代的視覺藝術作品不僅是靠視知覺來感受受,更多的是靠視覺本身來思考,要理解圖像本身而不是圖像的“比喻”,在面對作品之時和之后,其他表述不會再比作品本身更有用了,排除了一切他律條件,視覺藝術的自律就自然的出現了。
【參考文獻】
[1][美]簡·羅伯森,克雷格·邁克丹尼爾.當代藝術的主題:1980年以后的視覺藝術[M].匡驍譯.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13.
[2][美]歐文·帕諾夫斯基.視覺藝術的含義[M].傅志強譯.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3]易英.抽象藝術的理論死亡[J].大藝術,2011(02):9-12.
[4]易英.紐約的沒落[M].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2004.
作者簡介:黃昌劍(1993-),男,魯迅美術學院綜合繪畫系研究生。研究方向:水性材料繪畫表現與研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