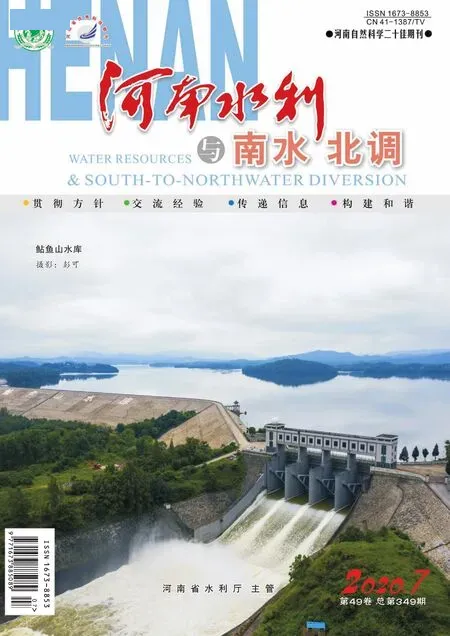灌區信息化建設發展現狀及對策
邵艷楓 姬夏楠 張素艷
(河南省豫東水利工程管理局三義寨分局)
1 引言
灌區發展過程中,對于信息化建設具有了新的要求,也是對灌區服務質量、水平進行提升、降低成本的重要手段,也是今后灌區發展建設的重要方向。近年來,雖然很多灌區在發展中也能夠對該項工作形成重視,但在具體實施上還存在一定的不足。對此,需要灌區管理部門能夠做好存在問題的解決,以科學措施的應用提升灌區信息化建設水平。
2 灌區信息化建設意義
灌區發展中,管理能力存在不足是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在以往灌區管理當中,對于相關的信息、資料還是以手工方式處理,不僅無法實現對資料的維護管理,也無法實現信息共享。在現今水利建設當中,水利信息化是其中的重要標準與基礎,灌區信息化建設也正是整體水利信息化建設的關鍵內容。對于灌區信息化來說,即是對現代信息技術進行充分利用,對灌區管理信息資源進行深入的開發應用,具體包括有信息采集、存儲、傳輸與處理等,以此對信息采集、加工以及傳輸的準確性進行提升,做出準確、及時的預測反饋,以此為灌區管理部門發展提供科學決策,在對灌區管理效能進行提升的基礎上,使整個灌區工作能夠從中獲得健康的發展。
3 發展現狀
3.1 規劃階段
規劃階段,存在的問題有:第一,數據格式不統一,在定義以及分類上存在不規范的情況。作為設計單位,在各自為陣的情況下,存在低水平建設開發的情況。數據庫標準化程度低且模式多樣,數據在存儲上存在難以同化的情況,無法有效的實現信息共享。在信息采集傳輸設備方面,在檔次、種類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第二,規劃同建設脫節。在具體工作開展中,受到編制規劃時期條件與實際情況的差異,在具體規劃編制深度上也存在不足,在技術方案實施的時機上存在不合理的情況,工程量同建設內容間也存在不匹配的情況。在不同地區,信息化建設在重點與規模上存在差異,存在規劃內容同實際建設情況不符的問題。
3.2 建設階段
建設階段,存在的問題有:第一,建設水平低,對數據質量產生了影響。部分區域存在重復建設情況,使指標以及數據源存在重復混亂的情況,很可能因此出現相互間的矛盾。在具體建設中,不同施工單位在技術手段應用上也存在差別,無法對系統建設的整體性進行保證,對于系統的綜合集成、二次開發也具有不利的影響。第二,管理職能分散。對于信息化運行人員來說,其處于基層服務系統當中,沒有參與到項目建設的前期工作當中,對規劃信息的了解存在不足。同時,部分工作人員對于信息化、工作需求存在認識不到位的情況,雖然在水利工程建設方面具有深厚的經驗與技術基礎,但在信息化方面則存在不足,無法對具體信息化建設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及時的發現。
3.3 運行管理階段
運行管理階段,存在的問題有:第一,維護成本高。在灌區當中,雨量、流量與水位相關設備具有較多的種類,在具體性能、品牌上也存在不足。在運行當中,進口設備在運行質量上相對穩定,但具有較高的設備價格,通常為一體化設計,在維修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難。第二,存在資金缺口。信息系統維護是一個難度較大的工作,在管理維護階段中,主要通過管理以及應用者完成。信息化設備在運行當中,具有較高的淘汰率以及更新速度,因此運行維護具有較高的費用。而對于這部分費用來說,通常由使用單位解決,對于水管部門而言則存在一定的缺口。
4 應對策略
4.1 規劃階段
規劃階段,需要把握的重點有:第一,科學規劃。通過科學規劃工作的進行,能夠起到節約工期與工程投資的效果,以此保證工程在建設完成后能夠高效運行。在系統建設規劃當中,需要充分聯系灌區發展實際,緊密聯系效益與應用效果,在灌區管理中充分應用科學技術,保證系統工程具有較高的技術含量。第二,規劃調整。在實際規劃當中,需要做好改造方案的升級工作。對于規劃無法滿足目前需求的情況,即需要能夠充分聯系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以經濟、技術以及效益幾項原則對建設內容進行進一步優化。第三,統一規劃。在系統的輸入輸出接口方面,要做好國家標準的應用,以此為系統的集成提供一定的便利。要對標準統一、科學規范的信息化應用平臺進行建立,對資源共享、網絡互聯目標進行實現,這也正是降低投資、減少后續維護成本的一項重要方式。第四,加強溝通。在水利系統當中,根據具體的職責對應關系,可以由計算機網絡系統同通信系統進行連接,對成果、信息的共享進行實現。具體來說,可以建立云計算、感知層以及網絡層平臺架構,以此為信息化系統的建設提供統一基礎平臺。
4.2 建設階段
建設階段,需要把握的重點有:第一,加強系統建設,做好模塊配置。在現階段灌區發展中,主要的業務系統有配水的調度管理、信息采集管理以及辦公自動化系統等。在具體灌區信息化系統建設當中,需要對相應的技術標準進行嚴格執行,加強關鍵系統技術、主要硬件設備的審查,避免設備多樣化對實際工作帶來困擾,使系統在運行兼容性方面具有更好的表現。在該基礎上,也需要加強業務應用系統的開發,從系統建設經驗角度而言,可以使用微軟控件二次開發,該控件在應用中,具有界面友好、工期短的特點,能夠同管理人員的思維方式、工作習慣進行良好的符合,在經過一定時間培訓后即可以上崗操作。第二,數據庫系統在灌區數據庫建設方面,包括有水情、社會經濟、基礎信息與水利空間等數據庫。在工作當中,要做好網絡資源的充分利用,做好局域網系統的建立,以此對信息的共享、傳輸與處理進行實現。同時,要對灌區管理機構、水利行政部門與計劃用水戶等多級管理的數據共享進行實現,在對行政效能有效提升的情況下,使計劃用水管理具有主動的特點,以此為調度決策工作的進行提供信息支持。第三,建立信息采集體系。在現今公共通信資源當中,能夠滿足對灌區水源地信息傳輸方面的需求。在灌區信息化建設中,需要在現有公共通信網絡的基礎上,建立水利信息通信網絡,為灌區業務發展提供通信服務,在有所需求的情況下,可以對傳輸帶寬進行增加,以此對大數據傳輸能力進行保證。也可以對區域性數據中心進行建立,在基礎信息采集體系當中做好防汛抗旱、應急調度與日常灌溉等資源共享工作。
4.3 運行管理階段
運行管理階段,需要把握的重點內容有:第一,加強制度化建設。在灌區信息化系統當中,具有較多的精密設備,對于技術操作流程具有較高的要求。在具體系統應用管理方面,需要做好責任主體的明確以及管理職責的規范化,做好操作規程的嚴格控制,以此對科學、清晰且嚴謹的系統制度進行制定,保證系統的長效運行。對于很多信息化設備來說,其都是在荒郊野外安裝的,在暴雨天氣當中,很可能因受到雷擊而發生短路損壞問題,且可能出現被人、動物造成破壞的問題。對此,在設備運行當中即需要能夠對防火、防雷以及防盜等方面工作引起重視,以科學措施的應用保證設備安全。第二,加強人才培養。在信息化系統當中,涉及到較多的專業,包括有計算機、水利、自動化通訊等方面。對于管理人員的技術水平、專業素質也具有較高的要求。在實際工作開展中,需要保證管理人員在系統建設階段即能夠積極的參與到其中,對系統建設的技術要求、內容進行充分的了解,并在施工完成后為人員提供充足的培訓機會,在對管理人員不同方面素質不斷提升的情況下,使信息化系統能夠在灌區運行當中有效的發揮作用。
5 結語
通過對灌區信息化建設發展現狀及發展對策的探討,灌區實際發展建設中,需要能夠對信息化系統建設工作引起重視,從規劃、數據庫建設與人才培養等方面入手,切實提升信息化建設水平,以此為灌區未來運行打下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