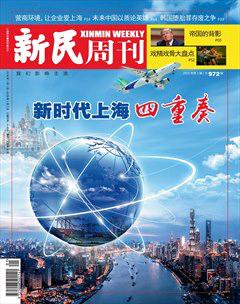神奇!一側大腦指揮兩手中國人開創偏癱治療新路徑
黃祺
手功能是最影響病人生活質量的功能,如果把偏癱一側手臂的神經嫁接到健康一側大腦,是否能重新“喚醒”偏癱的手呢?十年前,華山醫院徐文東教授帶領的手外科團隊在顧玉東院士的科研基礎上,提出了這個大膽的設想,并開始在臨床中不斷探索。
大腦,現代醫學迄今了解得最少的人體器官,它神秘而強大。但如果疾病造成腦損傷,也就是人的中樞神經損傷,帶給人的痛苦也是最大的——中樞神經損傷是致殘率最高的疾病之一,有數據統計,我國約有超過2300萬名中樞神經損傷患者,其中有400多萬腦卒中幸存者,致殘率高達75%,其中40%為嚴重殘疾。
因中風而手腳不便的老年人、腦外傷造成偏癱的青壯年、先天性腦癱而半身不遂的孩子……我們在生活中很容易遇到這樣的病人。過去,治療中樞神經損傷的思路,糾纏于如何恢復受損一側大腦的功能,但無論是傳統的神經康復治療、中醫療法還是后來出現的干細胞治療、機器人輔助康復等,治療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手功能是最影響病人生活質量的功能,如果把偏癱一側手臂的神經嫁接到健康一側大腦,是否能重新“喚醒”偏癱的手呢?十年前,華山醫院徐文東教授帶領的手外科團隊在顧玉東院士的科研基礎上,提出了這個大膽的設想,并開始在臨床中不斷探索。
用了整整十年的時間,這個設想以及它的臨床效果,終于被世界上最權威的醫學期刊刊登,得到了主流醫學科學界的認可。徐文東團隊的論文《健側頸神經移位術治療上肢痙攣癱的臨床試驗》,是《新英格蘭醫學雜志》(NEJM)2017年度唯一刊登的一篇臨床手術類科研論文,體現了國際醫學學術界對中國臨床科研成果的高度認可。
全新的手術理念,為今后中風偏癱、腦外傷偏癱、腦癱偏癱的治療帶來了新的希望。突破固有的定式、創立全新的手術理念和方法——中國臨床醫學研究起步較晚,但徐文東團隊的故事,讓我們看到了中國臨床醫生的巧思和執著追求,正在讓世界醫學同行刮目相看。
突破醫學傳統認識
曉菁,一位21歲的上海女孩,出生在經濟條件較差的一個普通家庭里,不幸的是,出生后不久家人就發現,曉菁不是一個健康的孩子,她很快被診斷為先天性腦癱。
至今,徐文東教授對曉菁當初來找他的情形,還記憶猶新。2008年,曉菁長到12歲,青春期的女孩子需要更加私密的空間,但因為身體左側的手和腿都有痙攣癱瘓的癥狀,曉菁連洗澡還需要家人幫助,這讓她自己和家長陷入了很大的困擾。家人帶著曉菁,找到了華山醫院手外科,希望這個聞名世界的團隊,能夠改善曉菁的殘疾,讓她實現生活自理的夢想。
現在我們看到的曉菁,身體左側仍然有明顯的殘疾,左手的五個手指嚴重變形,但曉菁卻很高興地告訴記者,她的左手在10年前接受徐文東教授的手術后,逐漸康復,現在左手的靈活程度與過去有著天壤之別。曉菁用左手拿起一個小球給我們做示范,雖然五指運動的形態與普通人完全不同,但小球卻牢牢地掌控在她手中,曉菁可以自由地控制小球的位置、旋轉。事實上,盡管看起來有點“丑”,但她的左手功能與右手已經相差無幾,可以完成日常生活所需的所有動作,她曾參加過全國特殊人群手工作業比賽,拿了全國第一名。
在徐文東教授團隊發布科研成果登上《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的新聞會上,他特別感謝了曉菁,當年正是曉菁的康復效果,讓團隊對這個新的技術充滿信心。
要講清楚徐文東教授團隊的這項新技術——“健側頸神經移位術”,不太容易。徐教授說,我們可以把人的神經想象成輸電線路,大腦是起點,神經線路一開始比較粗,從頭頸處開始分流,變成較細的神經,延伸向人體各處。分到手臂方向的神經名為臂叢神經,掌控著手的運動,左腦控制著右臂臂叢神經,右腦控制著左臂臂叢神經。
曉菁的腦癱主要損害了她的右腦,因此左臂的臂叢神經受損嚴重,造成了這一側的痙攣和癱瘓,但曉菁的左腦是健康的。在接診曉菁時,將受損一側臂叢神經嫁接到健康一側大腦的設想在徐文東教授這里已經成熟了,從提出設想到動物實驗,已經有好幾年的時間,醫生們需要做的,是看看這個全新的創想,能不能在病人身上收獲很好的效果。
曉菁之前,徐文東教授已經為一個年紀更小的孩子做過這個手術,證實了手術的安全性,而曉菁,也非常適合做這個嘗試。在與家屬和曉菁充分溝通后,在完成了嚴謹的倫理審查后,曉菁成為這個新技術的第二位病人。
對于華山醫院手外科這個中國手外科最好的團隊來說,將臂叢神經嫁接到健康一側大腦中樞神經這個手術本身,并沒有太大的難度,但徐文東依舊做了最為充分的準備。手術后,曉菁在手外科進行了系統的康復訓練,一年后,曉菁左手的康復水平,完全達到了醫生們的設想,左手的功能大大改善。
曉菁之后,2008年至今的10年中,100多位患者在華山醫院手外科接受了這一創新手術方式。“癱瘓上肢功能都有改善,包括痙攣程度降低,精細功能加強。其中,年輕患者、腦癱患者效果更好。”徐文東教授說。
徐文東團隊先后向《新英格蘭醫學雜志》投稿三次,在進行了巨量的修改和補充后,2016年的第三次投稿,最終被《新英格蘭醫學雜志》接受和刊登。《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以嚴謹著稱,論文刊登說明徐文東團隊以真實的數據證明了新手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這種創新的理念和手術已經得到世界臨床醫學主流學界的認可。
將受損臂叢神經嫁接到健康側大腦的手術創新,有著開創性的價值。“過去我們認為成年后大腦功能就固化了,管左手的只能管左手,管右手的只能管右手。但我們的手術發現,當另一側手臂的神經嫁接到健康一側的大腦后,大腦慢慢‘認識這一只新手,然后通過自我革新將自己分成兩個區域,分別控制兩只手。這說明大腦的潛力遠遠超出我們過去的想象,大腦也可以自己適應新的情況。我們只能贊嘆大腦的神奇。”endprint
兩次被拒甘于寂寞
“這是一個跨界的研究對嗎?”
面對記者的問題,華山醫院副院長、手外科教授徐文東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是跨界,而且跨得很大。”
中國手外科,在世界上享有盛譽,由華山醫院顧玉東院士等老一代學者開創的眾多引領性技術,至今仍是世界手外科界的經典技術。但一般來說,手外科只管手的疾病,“健側頸神經移位術”已經涉及到腦神經外科的領域。
能夠實現跨界創新,與徐文東教授自己的教育經歷有關。徐文東不僅是手外科權威顧玉東院士的得意門生,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后還進行了神經生物學博士后的工作。 “先要有寬度,才能有深度。就像潛水一樣,當你潛得比別人深,才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風景,才能做出自己的創新。” 跨學科的學習塑造了徐文東教授敏銳的發現能力和創新能力,臨床中發現的問題被視若珍寶,變成了科研課題。
然而,中國臨床科研的起步較晚,這讓徐文東不可避免地面臨各種困難和障礙。雖然中國的醫院有大量的病人,但過去臨床科研受到的重視不夠,病人的資料存檔、隨訪都很不健全,開展臨床研究的第一關——找到病人,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過去病人登記的信息很不齊全,2000年后中國人員流動很大,我們按照病人留下的地址找過去,很多人都搬家了,找不到了。我們發出去幾百封信,最后聯系到并且愿意配合的,只有三四十個人。”
除此之外,早期科研經費并不充足,外地患者手術后要定期到上海接受各種檢查,最初的幾年,各種開銷都是“緊巴巴”的。
到了2013年,隨著手術量的增加,病人術后手功能改善明顯,所有的結果都讓徐文東團隊感到振奮。徐文東教授認為,是時候將臨床試驗整理成科研論文向世界上最權威的醫學雜志投稿了。2013年徐文東團隊第一次向《新英格蘭醫學雜志》投稿,當時的他們無法預料到,從第一次投稿到正式刊登,竟然需要4年時間。
《新英格蘭醫學雜志》創刊于1812年,以出版對生物醫學科學和臨床實踐具有重要意義的醫學研究新成果而聞名于世,影響因子位列全球醫學期刊之首。所有的生物、醫學科研工作者和臨床醫生,都以能夠登上這本雜志為榮。這本期刊對臨床科研成果審查嚴格,需要投稿者能夠有力地證明手術或者治療方式的有效性。中國的臨床科研基礎較弱,雜志自然也會對來自中國的論文有更加詳盡的要求。
第一次和第二次投稿后,徐文東團隊都收到了雜志關于補充和完善資料的要求,但經過補充后,還是以被拒稿結束。
2016年,徐文東團隊再次向《新英格蘭醫學雜志》投稿,論文加上附件共43頁。不久后,徐文東收到了雜志的回復,依然提出了各種問題和需要補充的材料要求。團隊逐一回答審稿人提出的問題,光答案就寫了65頁,再加上補充材料,一共回復給雜志140頁。
可以想象,這是一項考驗科研人員毅力與自信心的浩大工程,但徐文東團隊出色地完成了。盡管論文正文按規定只有2700字,但科研團隊為之付出的努力,是難以估算的。
徐文東團隊的論文不僅是2017年《新英格蘭醫學雜志》唯一一篇手術類論文,也是中國幾年來手術類臨床科研成果首次登上這本雜志。NEJM前編委、《NEJM醫學前沿》高級編輯照日格圖教授評價說,NEJM以發表藥物臨床試驗類論文多見,極少發表與外科手術相關的臨床研究,足見此項手術對醫學進步的重大意義,是中國醫學專家為世界做出的貢獻。
中國臨床科研還在探索和起步階段,談起論文成果發表的經驗,徐文東教授說,首先要對自己的研究充滿自信,其次是中國的學者必須嚴格按照權威雜志的規范,做出經得起檢驗的成果。如果從臨床試驗前的各種研究算起,徐文東團隊為這項科研成果的付出,已經超過了“十年磨一劍”,如果不是強大的自信和耐得住寂寞的堅持,恐怕也不會有今天的結果。
兩代人接力轉化醫學
創新的手術理念,絕不可能僅僅來自天馬行空的靈感,徐文東教授一再強調,這一次手術理念的突破,是站在巨人肩上攀登的結果。其中重要的創新依據,來自顧玉東院士創立的“頸7神經根移位術”。
手外科是華山醫院“金字招牌”,早在1966年,華山醫院楊東岳教授、顧玉東教授,完成世界首例“足趾移植再造拇指”術。術后,患者雙手獲得相對良好的外形和功能,一時轟動國內外醫學界。近30年來,華山醫院手外科榮獲7項國家級科技大獎,大幅推動了我國手外科領域的發展。
30多年前,顧玉東教授遇到了一位車禍外傷的29歲病人,車禍外傷讓他的臂叢神經發生了根脫性損傷,與中樞神經徹底分離。這樣的“根性撕脫”造成的上肢癱瘓,過去是不治之癥。車禍給年輕人帶來沉重的打擊,甚至想要放棄生命。
臂叢神經位于人的頸部至腋窩處,由頸5、頸6、頸7、頸8和胸1五根神經組成,分別支配人的背闊肌、胸大肌、胸小肌和手臂上的肌肉。
上世紀70年代,隨著顯微外科逐漸興起,各國手外科醫生開始設想,如果切斷患者身上的一根受影響較小的神經,移植到受損的臂叢神經,是不是能改善患者的殘疾呢?當時,顧玉東教授也在做這方面的探索,在治療了上百例病例之后,他發現了一根可以用來修復臂叢損傷的神經——膈神經。
關于如何萌生用膈神經來修復臂叢損傷的點子,顧玉東教授曾談到,他受到肺結核治療的啟發。“上個世紀30年代,治療肺結核沒有特效藥,病人肺里面一個空洞,醫生把膈神經一阻斷,肺就縮掉了,一縮起來,那個洞癟掉了,就這么治療肺結核。因此我就想了,這個膈神經可以把它剪斷,膈神經剪斷了以后,我可以利用它,把它接到管肌肉,讓它支配肌肉活動。”1970年,顧玉東就已經完成世界上首例膈神經移位手術,有效率達到84.6%。
但眼前的這位患者,膈神經也已受到損傷,膈神經移位手術也不能做了。“好用的神經都不好用了,叫走投無路。”
顧玉東沒有放棄,他翻看過去24年來所做的臂叢手術案例,又有了新的發現——頸7神經也許能夠排上用場。顧玉東發現,人的頸7神經,切斷后不會帶來功能障礙,既然可以切斷這個神經,那么如果從病人健康手臂中取出一根頸7神經借給患病的一側,癱瘓的手臂是不是能重新恢復功能呢?
這是一個破天荒的設想,從未有人嘗試,但顧玉東相信這個方法有用。給車禍患者做了手術后,顧玉東看到了很好的效果,一個全新的手術方式就此誕生。
1989年4月,第八屆國際臂叢學術大會上,顧玉東關于“頸7神經根移位”的報告震驚全場。1993年,顧玉東院士憑借全新突破——《健側頸7神經移位治療臂叢根性撕脫傷》,榮膺國家發明二等獎、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上世紀90年代初成為顧玉東教授的學生時,徐文東也被這一大膽設想所震撼,患者的雙上肢神經被“左右換位”,完全顛覆了傳統的認識。
沿著顧玉東院士的思路,徐文東教授有了更進一步的設想:這種左右換位是否可以應用到一側中樞損傷的病人?將癱瘓的一側上肢的臂叢神經移位到健康的大腦一側呢?就此,徐文東教授帶領著年輕的臨床科研人員,開始了嚴謹而執著的研究。2016年,徐文東教授以《臂叢神經損傷及修復過程中的大腦功能重塑規律及新技術的轉化研發和應用》課題,榮膺第15屆上海醫學科技獎一等獎、上海市科技進步一等獎和中華醫學科技獎一等獎。
徐文東教授說,未來,團隊還會在現有的科研基礎上解開更多的未解之謎,比如,大腦是怎樣“認識”新手的?大腦如何將自己分區并分別控制兩手?新的手術如何在老年患者中收到更好的效果?手功能可以改善,那么這個手術是不是也能改善腿部功能?
從臨床中發現問題并提出創新的解決方案——徐文東教授團隊的故事,正是轉化醫學的生動案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