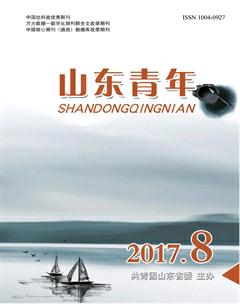論述“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
呂競一+王夢橋+黃婷婷
摘 要:
排除合理懷疑是英美法系國家的證明標準,在刑事訴訟中,對于正確認定犯罪與判處刑罰具有重要作用。我國2012年最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的證明標準中引入了“排除合理懷疑”,與“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形成了主客觀相協調的標準依據。研究“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在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和各國學者提出的解決辦法,有利于提高我國“排除合理懷疑”規則的適用路徑。
關鍵詞: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2013年刑事訴訟法
長久以來,“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一直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作為對證據考量的唯一標準,其所要求達到的證明程度,基本屬于歐美證據學中規定的第一等證明標準[1],被認為是不可能達到的,故學界對此有一定的爭議。而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在理論和實務屆分別被熱烈討論和實際適用,我國便在2012年引入了“排除合理懷疑”的表述,對我國的證明標準進行解釋。
“排除合理懷疑”概念最早可追溯到中世紀羅馬教皇高利一世的告誡:“做出裁判是件嚴重且不體面的事,事存懷疑請務必尋求確信。”[2]主流的觀點認為,其正式運用是在1789年的愛爾蘭法院的一起叛國罪案例中。該案中,法官明確提出了“排除合理懷疑”標準。從此,排除合理懷疑正式作為一種證明標準被廣泛的討論和運用。而美國在成為一個國家之前,1770年的波士頓大屠殺中,便有了這種證明標準的萌
芽。[3]
盡管“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在英美法系國家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但對于其是否需要進行定義或解釋等問題,理論界以及實務界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見。理論界的學者認為,“排除合理懷疑”概念為法律術語,不僅僅拘束于三個詞語日常涵義的簡單結合,要通過對該術語的正確理解,實現控辯雙方公正的當然使命。實務界人士認為,正因為排除合理懷疑標準對事實認定的重要性,陪審團對案件事實認定的決定作用,更應該嘗試做出解釋,以幫助陪審團更好地判斷。至今,此項證明標準有如下解釋。①將排除合理懷疑解釋為一種道德上的確信;②將排除合理懷疑解釋為很高的可能性;③將合理懷疑解釋為“難以決定”;④用量化的比例對排除合理懷疑標準進行解釋;⑤其他解釋。(美國在其基礎上又增加了“擬制第三人”標準、堅定信念、給出理由的懷疑、無需解釋。)[4]全面了解該證明標準是適用的前提。
一、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的實踐
一個合適高度的“欄桿”,才會讓“這場跨欄跑”真實的體現司法的公正。[5]
實踐中的第一個難題便是法官如何對陪審團解釋該證明標準。正如上文所說,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期,不同的法官對排除合理懷疑有不同的解釋。實踐中,是否允許對排除合理懷疑做出解釋也是截然不同的。拿美國來說,第3,6,8,10巡回法院明確要求一審法官為陪審團解釋“排除合理懷疑”的涵義,作為程序的要求之一,如若沒有,二審法院可以據此推翻一審判決。而1,4,7,9以及哥倫比亞的法院明確規定不準對排除合理懷疑進行定義,否則,二審法院同樣可以撤銷一審判決。[6]
其次,陪審團對“合理懷疑”的判斷是主觀的,而且很容易受到非法律因素的影響。例如,輿論對陪審團判斷的影響。著名的辛普森案件,陪審團最終做出了無罪的判決。但是輿論始終相信辛普森確實犯罪了,試想如果陪審團了解這些輿論并且受到這些輿論的譴責,怕是難以做出無罪的判決的。所以在陪審團成立后,除了合法的證據,陪審團不應該受到其他任何因素的影響。這是陪審團制度和“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適用的保障之一。
另外,”排除合理懷疑”可操作性有待提高。法律之所以優于道德和宗教,在于法律的明確性、可操作性與約束力。證明標準作為一項法律制度,也應當具有現實的可操作性。學界認為,該標準應該至少符合兩項要求:一是能夠被一審法院所適當的運用;二是二審法院能夠據此做出對一審法院裁決的處置。而在一審中,法官對于解釋該標準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而二審法院面對一審法院陪審團已經作出的判決,很難從證明標準本身的角度撤銷一審判決。實踐中,二審法院否定一審法官對該證明標準的解釋例子很多,但是很少有二審法院以“未排除合理懷疑”為由推翻一身的判決。
二、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的特點
排除合理懷疑在如此爭議的情況下依然被廣泛適用,在于此標準的優點也十分明顯。
首先,相比于“證據確實充分”證明標準,“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更注重主客觀相結合,強調追求排偽,可操作性更高。完全追求客觀是做不到的,第一由于我們建立的認識論是可知論,但可知論的前提是實踐論,昨日不可重現實踐不可能;第二是收集證據能力的有限性,達不到實現客觀的標準。因此過分強調客觀有失偏頗。而“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給了主觀判斷的空間,不管是對于法官還是陪審團,都有利于他們的判斷。
其次,此證明標準能夠與無罪推定原則更好的結合。第一,無罪推定原則與該標準的出發點一致,都是使判決無辜者有罪的錯誤實現最小化,保障人權。第二,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能夠使無罪推定原則更好地、具體化地落實。“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就是明確了控辯雙方的權利義務,控方承擔去排除合理懷疑的責任與負擔,被控方可以去增加有關于此案件的合理懷疑。由此可見,“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的運用實施既符合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又能夠保障無罪推定這項原則在訴訟過程中得到具體化的落實,而使之不僅僅是一項抽象的原則。第三,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也在1984年通過的關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地一般性意見中指出:“有罪不能被推定,除非指控得到了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由此可見,無罪推定原則與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密不可分,相輔相成。
最后,此標準與我國的“疑點排除”經驗相一致。[7]排除合理懷疑符合中國原有的“疑點排除”經驗,二者結合能夠更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實。在所有的案件處理過程中,如果法官發現收集到的合法證據間不能相互印證,證據鏈有漏洞,讓法官產生了懷疑,那么法官就不能判定有罪。這種因為出現疑點、矛盾而無法作出有罪判決其實就是“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的體現,實質上就是“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的運用。
三、“排除合理懷疑”規則在我國適用的啟示
我國現行證明標準是“證據確實,充分”,2013年后,該法條的第三款引用了“排除合理懷疑”的表述作為解釋我國證明標準的一個輔助規則。為了更好地促進“排除合理懷疑”規則本土化,將英美法系“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與我國“排除合理懷疑”規則進行對比可以得到幾點啟示:
與陪審團相比,法官能夠更好地把握此規則。雖然我國沒有陪審團負責事實判斷,但實踐證明,這并不是我國適用該規則的一個絆腳石,反而是該標規則適用的一個新的突破。由于 “排除合理懷疑”規則的涵義難以界定,普通公民組成陪審團并不能很好的理解并把握此規則。我國“以審判為中心”的庭審制度,由法官運用“排除合理懷疑”規則認定案件事實,法官的專業知識正是促進此規則更充分適用的一個優勢所在。
此規則是針對刑事案件的特有規則。“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僅僅用在刑事審判中,民事審判適用的是更低的“優勢證據”證明標準。對于我國來說,這一點是值得借鑒的。事實上,面向我國部分地區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以及律所的訪問調研結果顯示,目前我國的“排除合理懷疑”規則的適用同樣僅僅體現在刑事案件中。這一點也說明,我國和英美法系適用“排除合理懷疑”的理論基礎的外延是一致的。
完善證據制度有利于更好的適用“排除合理懷疑”規則。英美法系的證據規則和“陪審團制度”與“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構成交相輝映的關系。其中,最為明顯的一個體現便是:違法的證據不予采納,判斷證據違法與否的裁判者是法官,但是進入庭審程序的證據審查者的陪審團成員沒有機會接觸非法證據。而我國證據制度的效果并不能發揮的如此淋漓盡致。原因在于,證據資格和證據能力的判斷者都是法官,非法證據被排除之前已經被法官一覽無余,并且在心中已經形成了判斷。針對這個弊端,我國應該制定更加嚴格的證據制度,或者是相應的審查流程來加以改善。
“排除合理懷疑”規則應在“證據確實,充分”證明標準的指導下適用。這里面主要強調兩個關鍵點。第一,“確實”一詞要求證明案件的證據具有合法性。第二,“充分”一詞,對證據的證明力提出了要求。即在證明力薄弱的情況下,需要其他證據的佐證證明案件。只有充分的證據都指向一個結果的時候,才能判定嫌疑人有罪。所以“排除合理懷疑“規則的適用,一定要在這兩個關鍵的指導下進一步明確案件的事實,形成更加合理的判斷。
[參考文獻]
[1]英美證據學中九等證明程度:“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淵源于英美法系,而英美法系國家將證明標準的程度分為九等:(1)絕對確定。根據人類現有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無法達到絕對確定。(2)排除合理懷疑;(3)清楚和有說服力的證明;(4)優勢證據;(5)合理根據;(6)有理由的相信;(7)有理由的懷疑;(8)根據懷疑可以開始搜查;(9)無線索,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為.
[2]張威. 論排除合理懷疑的動態界定[J]. 中國刑事法雜志,2014,(02):64-71. [2017-09-19].
[3]肖沛權. 排除合理懷疑及其中國適用[J]. 政法論壇,2015,33(06):51-64. [2017-09-23].
[4]楊宇冠,孫軍. “排除合理懷疑”與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完善[J]. 證據科學,2011,19(06):645-656. [2017-09-23].
[5]把“證明標準”比作欄桿是魏曉娜教授在論文《排除合理懷疑是一個更低的標準嗎》中的著名比喻.
[6]陳永生.排除合理懷疑及其在西方面臨的挑戰[J].中國法學. 2003(2):150-160.
[7]肖沛權,論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的司法適用[J]法律適用,2015(9).104-108.
本文屬安徽財經大學大學生科研創新基金項目(項目編號:XSKY1725ZD)階段性研究成果,指導老師:黃瑛琦
(作者單位:安徽財經大學法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