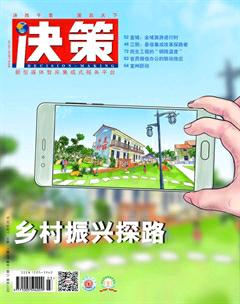鄉村如何振興?
吳明華
“鄉村衰而未亡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公共政策在‘哪些活、‘如何活上有很大操作空間。”
鄉村問題比農業、農民問題更棘手
《決策》:十九大報告把鄉村振興上升到戰略高度,政策思路發生了哪些轉變?
劉守英:有非常大的轉變。首先,原來“三農”問題政策基調是圍繞農業和農民的,對村莊問題是忽略的。實際上,農民、農業和農村應該是三位一體的。下一步,鄉村問題會成為“三農”的首要問題,有可能是比農業和農民問題更棘手的問題。
根據我們了解的情況,農二代基本上是離村不回村,即使回鄉創業,也是流向本省的地區和縣一級城市,沒有回到村莊的。未來農三代基本上跟鄉村聯系隔絕掉了,根本不知道村在哪兒。
我現在最擔心的一件事,就是跟新農村運動一樣,又是砸一大筆錢去刷墻、修路。我覺得必須了解大的趨勢:第一,大部分村的衰敗不可逆,這是趨勢性的;二是要重點研究現在哪些村莊會活,這是未來公共政策的重點。要摸清情況,研究這些村莊怎么活;三是如何可持續的活,人不回村莊就不可持續,鄉村產業成長不起來就不可持續。
第二,城鄉融合。十六大以來提的城鄉統籌和城鄉一體化,解決了城市有農村沒有的問題,養老、社保、醫療等。但同時也把農村的地統到城市去用,另外是城鄉二元體制不是削弱了,而是強化了。所以十九大報告提出城鄉融合,是對原來城鄉統籌的矯正。
過去城鄉在發展權利上不平等,鄉村衰敗肯定是進一步加劇。現在城鄉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已經從原來的單向城市化開始轉向城鄉互動,土地、資本和人等很多要素在往農村走。現在城市對鄉村的需求發生了變化,城里人到鄉村休閑、旅游等,帶來了整個農業功能的拓展。未來城鄉融合非常重要的變化,就是城鄉兩個文明共存共生。
第三,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與現代化。我覺得這是理念上的進步,鄉村是農業和農村的有機體,如果只講農業和農民的現代化,沒有農村現代化,鄉村現代化是不成立的。
第四,農村的地權和農民的地位。把承包權與經營權分離,延長承包期,保證了制度穩定性和制度預期。經營制度方面,過去我們推適度規模流轉,現在整個土地流轉已經達到35%,但公司搞農業都不掙錢,因為地租和勞動力成本上漲。搞農業合作社,農民合不起來,農民成立合作社把政府補貼弄到手,分了就散。所以這次提小農跟現代服務結合起來,主要是服務規模化和區域規模化種植。
五是鄉村治理。原來我們擔心鄉村治理最后變成集體的回歸,但鄉村治理是要重建鄉村秩序和制度,包括自治、法治和德治。
鄉村衰而未亡的背后
《決策》:對于當前鄉村的實際情況,您有怎樣的觀察和思考?
劉守英:過去一年,我從貴州湄潭開始,跑了很多村莊,大部分是西部地區,也有一些發達地區,例如北京郊區、上海、浙江等。從觀察者的角度,我發現鄉村復興還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農民代際特征明顯,正在發生一場我所稱的“結構革命”:離土、出村、不回村。農民不斷離開村莊,而且有一種一去不復返的勢頭。與人口出村相對應的,是村莊數量在減少,而且持續衰敗,我給它的定義是“衰而未亡”。
有一次去河北蔚縣,離北京只有200多公里,偶然機會去了當地村莊,看到一片破敗景象,在村里所能看到活生生的存在只有兩樣,一是老人,另外是狗。離北京這么近的村莊都是這種狀況,讓我非常吃驚。
應該看到,人往外走是符合趨勢的,村莊的慢慢消亡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符合趨勢的,但這一趨勢的背后卻不太正常。整個人類社會的演變,并不是以鄉村衰敗為代價的。也就是說,人的城市化不是以鄉村的衰敗為代價的,村莊的活力還是要靠人來維系。
鄉村如此大面積的、急速的衰敗,來源于中國城鄉不平等的發展理念,鄉村沒有任何發展權利。其次,鄉村衰敗因農業狹窄而起。一般來說,鄉村會“縮”但是不會“敗”。因此,鄉村要活,農業功能必須多,否則鄉村賴以生存的產業就沒辦法和城市競爭。但我們的問題在于,農業發展的路子越來越窄,農村就不可避免地越來越衰敗。
此外,城市過于強大和鄉村過于弱小也是重要原因。在強勢的城市文明下,鄉村文明越來越弱勢。對于一個農民來講,在鄉村是毫無尊嚴的,所以當有機會去城市時,大家便爭先恐后地走向城市。
我們不反對城市化趨勢,但是鄉村如此衰敗,就要反思深層次原因。第一個原因,我覺得可能中國鄉村的現代化是被無視的,我們到現在還是停留在農業和農民增收層面,但是鄉村本身如何現代化,并沒有被提到議事日程上的。
第二個原因,對于農業和鄉村功能的理解有失誤。農業到底是什么?農村到底應該有什么功能?在偏向城市的政策慣性下,鄉村就應該是衰亡的、落后的?
第三個原因是對城市化的認識有偏差,認為城市化就是所有要素都往城市走,只要城市化完成了現代化基本就完成了。雖然一直在強調農業和農村的重要性,但城市文明和鄉村文明到底如何共存,很少有人花功夫去思考。
復興鄉村并非不可能
《決策》:在您的調研中,有沒有發現一些鄉村振興好的做法和經驗?
劉守英:其實,鄉村復興不是不可能的,在我過去一年的調研中,就發現了很多活生生的案例。
貴州湄潭是在鄉村發展基礎上的現代化,它的特點是持續的農村改革、不強勢的政府和城市、鄉村產業的發展。
過去湄潭極度貧困,當時國務院農研室在這里嘗試“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改革,考慮到沒有地的農民如何發展,還啟動了一項非常重要的改革:荒山拍賣。由于嘗到改革的甜頭,歷屆政府也樂于以改革釋放紅利,于是形成一種改革氛圍,用改革撬動發展。
湄潭另外一個發展是茶產業的形成,即規模化+產業+市場。湄潭目前有60萬畝茶山,茶產業和相關連帶產業一年的產值88億元。湄潭一個重要的經驗就是“農業工業化”,農業也是可以工業化的。在鄉村產業起來以后,鄉村旅游和服務業也發展起來。
貴州的安順市起點比湄潭更低,怎樣為更貧窮的地方安上發動機?安順的做法是政府不斷地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是貧困地區發展的前提;另外是持續的扶貧,以產業扶貧為主;然后是改水改灶改廁改圈,提供基本的文化設施和公共服務。
隨著基礎設施完善,外部投資慢慢也來了,鄉村也開始美麗了,產業發展也有機會了。但這些都要落腳到農民的內生動力上,才能把這些資源組合起來,安順在農村產權改革上做了“確權”、“賦權”和“移權”。當所有的生產要素發生變化時,生產關系就開始改變。
安順經驗啟發我們,極貧的地方需要發動機來啟動,需要公共政策引導,需要尋找地方特色應對城市需求。這可能是鄉村現代化的另一條路,即一定的公共投資把貧困的部分障礙掃除,然后再開始換面貌,尋找產業機會,再進行產權改革,慢慢把活力調動起來。
另外一個例子,是浙江松陽縣通過古村活化來引領鄉村復興。松陽在浙江算后發地區,拼工業化拼不過其他地區,但它在歷史傳承上尋找突破口,松陽已有1800年歷史,擁有100多個古村落,71個國家級傳統村落。
目前,一些經過藝術家努力的古村落開始活化,價值顯化與升值,城里的一些元素往鄉村聚,人氣在增加,鄉村呈現生機,圍繞古村復興的投資在增加,旅游在興旺,茶產業的規模化、市場化帶動農民增收和配套產業的發展。
但松陽案例往外走時,也有些問題要思考。首先,其他地方古村改革的資金從哪來?資本來源不解決,還是難以發展。其次,村民得到了什么?這是極為關鍵的一個問題。再次,規劃部門能否控制好局面?鄉村活起來之后往往就面臨著一個問題:規劃控不住。
再來看上海松江區,這里的主要特點是發展家庭農場,做法是將原來一家一戶分到的承包地集中到村集體,然后村里通過一定程序來選出種地的人。一個村的地主要集中在幾個農民手上,一年能有20-30萬元的收入。在松江,農業真正成了一個體面的、可以與其它行業媲美的行業。
鄉村振興的政策重點
《決策》:從地方上來說,如何把鄉村振興戰略落地?政策的著力點在哪?
劉守英:鄉村衰而未亡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公共政策在“哪些活”、“如何活”上有很大操作空間。
對于地方上來說,不要總想著把綠水青山都變成金山銀山。綠水青山在很多地方就是綠水青山,只有部分地方能變成金山銀山,如強行開發可能會帶來諸多問題。美麗鄉村建設并不意味著所有村莊向一個地方大集中,而是嵌在山水中。
在政策制定方面,首先要重新思考城鄉關系。城市文明離不開鄉村文明,城里人在城市待久了,需要去鄉村換空氣、換心情;而鄉村文明也離不開城市文明,農民前往城市是趨勢。未來公共政策應該把鄉村與城市當做平等、共存、共榮的文明來對待。
其次要思考由代際隔離引發的鄉村現代化。這一輪鄉村的現代化一定要考慮代際差異,農二代對鄉村的觀念、與鄉村的關系、與土地的關系可能會決定整個鄉村現代化的走向。
再次是鄉村轉型必須由宅基地改革作為牽引。鄉村的復興需要新的事物來撬動。只靠財政制度、特殊優惠等慣用手段,普通的鄉村難以存活。因此,未來鄉村轉型的重點之一就是宅基地改革必須突破。
當前,宅基地制度基本上是無償分配,以成員權為基礎的,很多村民覺得不要白不要,結果是人不在村莊但地仍舊占據,這使得村莊衰而不亡。而村莊如果想活,宅基地可以起巨大作用。如果宅基地制度不改革,村莊就很難發展。
宅基地改革一個經驗是北京房山區的黃山店村,它展現了外面的資本如何進村。做法先是全村搬遷,搬遷時村里將原來300多戶宅基地有償收回,由集體開發成特色民宿,給農民的補償是每人40平米,每平米400元—800元。剛開始村里自己經營,卻沒有市場,后來引入一家企業做市場運營,公司和村里五五分成。
最后,鄉村的變化跟農業制度改革極為相關。因此,農地權利的設計、經營制度的設計會帶來整個農業的轉型,這應是下一步改革應該考慮的重要內容。鄉村的轉型和農地制度的轉型需配套,核心有二:一是原來農民手上的承包地如何釋放出來;二是誰來種地,這牽涉到未來農業經營制度的主體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