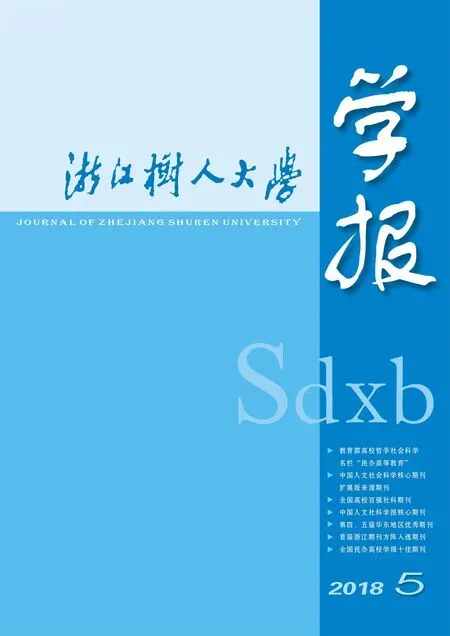白居易紀夢之作探析
王秀妍
(山東師范大學 齊魯文化研究院,山東 濟南 250014)
白居易的詠夢詩是審美人生與現實倫理的結合,體現了詩與夢的共同特點——“空幻”,并使人在“空幻”的心靈世界中,進入一種靈動的審美境界和藝術境界。夢是實現欲望的偽裝形式,更隱蔽地表現人真實的心理活動。在某些方面,文學藝術作品與夢幻相似,也是愿望的一種間接表達,兩者都是一種不同尋常的表達形式。白居易的詠夢詩包含詩人行為中所蘊含的無意識,依據其紀夢之作可探析詩人都不自覺的真實情感,同時觸及詩人心理沖動的最深層面,展現詩人對人生的自我審視,進一步追尋夢境的根源。
依內容而言,白居易的詠夢詩可分為懷人、仕途際遇和人生體悟三大類,分別表達詩人對親朋好友的情深義重、對仕途艱辛的釋懷和對豐富人生歷程的感悟,許多的不可言說、不能言說及不得言說都借助“夢”的形式充分釋放出來。
一、“昨夜三回夢見君”之懷人夢
白居易一生交友甚多,好友以劉敦質、元稹和劉禹錫為主要代表。詩人曾為友人們寫過多首紀夢之作,如“昨夜三回夢見君”*彭定求編,中華書局編輯部校:《全唐詩》,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899頁;第4901頁。,描寫他一夜之間反復夢見好友,表達了對遠在他鄉的友人最真摯的思念之情。
劉敦質,字太白,卒于貞元二十年(804),白居易為其作詩《哭劉敦質》:“愚者多貴壽,賢者獨賤迍。”*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39頁。詩人為“賢者”劉敦質的早逝悲痛惋惜不已。十多年后白居易貶謫江州,無依無靠,夜晚在夢中與敦質再次相遇,與好友同游彰敬寺。“昨夜夢中彰敬寺,死生魂魄暫同游”*彭定求編,中華書局編輯部校:《全唐詩》,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899頁;第4901頁。,詩人在自己最落魄之時做了一個與已故好友同游彰敬寺的美夢,聊以慰藉。在夢中,人能夠自由喚起清醒時所無法觸及的記憶,或喜悅或悲傷。好友早逝,看似已被詩人遺忘,但在詩人的夢中依舊活靈活現,仿佛還在世上,從而實現了現實中無法實現的愿望,重溫兩人之間的美好回憶。
白居易與元稹是生死不渝的摯友,《秋雨中贈元九》一詩所作的時間證實兩人定交于貞元十八年秋。兩人志同道合,素有“元白”之稱,為后人留下諸多情真意切的唱和詩,曾互相以夢詩表達對彼此的思念。如白居易在被貶江州司馬任途中,作“不知憶我因何事,昨夜三回夢見君”(《酬樂天頻夢微之》)[注]彭定求編,中華書局編輯部校:《全唐詩》,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899頁;第52234頁;第4775頁。,用做夢這種間接的方式表達對友人元稹的憶念。詩人夢中的表層含義是“不知遇到什么事情了?友人這樣思念我,不然怎么會三次做夢,頻頻遇見他”,而夢的深層含義是詩人思念友人,因思成夢,一夜三次在夢中與友人相遇,足見彼此感情之深。元稹這樣回復白居易的思念:“我今因病魂顛倒,惟夢閑人不夢君。”夢的表層含義是“我因病纏身,魂魄顛倒,唯獨夢見別人卻夢不見你”,而詩人深層的內心活動是“想要夢見你卻又夢不見你”。“謂吾人所不愿遇見之者,乃至吾人所欲得者,常于夢中實現之”,白居易寫頻夢微之,元稹寫不夢居易,兩首夢詩雖然表面上闡釋不同的意蘊,實際上都是詩人們在無意識狀態下對彼此真情的流露。
白居易與劉禹錫既是文友也是詩敵[注]蹇長春:《白居易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頁。。《舊傳》云:“禹錫晚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詩筆文章,時無在其右者。”[注]劉昫:《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212頁。會昌二年(842),劉禹錫卒時,白居易作詩哭之:“四海齊名白與劉,百年交分兩綢繆。”(《哭劉尚書夢得二首》)劉、白兩人交往許久,相會頻繁,關系密切,但分分合合。自寶歷二年(826)至會昌二年,兩人在輾轉仕途的過程中,相聚時游玩唱和,別離時作詩表思念之情。由于兩人身處相同的政治和文化環境,對彼此的思想有認同感,且可以感知彼此的快樂和憂愁。闊別四年之后,白居易再次身處故人家鄉洛陽時,不禁懷念夢得:“昨夜夢夢得,初覺思踟躕。”(《夢劉二十八因詩問之》)在夢中,詩人“忽忘來汝郡,猶疑在吳都”,夢醒之后才意識到禹錫早已離開吳都,移汝州刺史。“吳都三千里,汝郡二百余”,洛陽與吳都相距三千里,與汝州相距二百余里,迢迢數千里的距離令兩人無法相見,因此詩人分外珍惜與友人相聚的夢。夢醒之后詩人反復思量,長期的分離使夢中短暫的相聚顯得尤為珍貴,看似簡單的夢境道出了現實的艱辛和悲涼。
白居易對兄弟行簡則表達了血濃于水的親情。白居易兩個弟弟早夭,在世的只剩下白行簡,詩人與行簡的感情甚好。兩人為了功名和生計奔波于天涯各處,但那種“本是同根生”的牽掛絲毫未減。白居易時常寫詩表達對弟弟的思念,也時常在夢中與身在遠方任職的弟弟團聚。“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餐。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寄行簡》)[注]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827頁;第1856頁。此詩作于元和十一年,樂天被貶至江州已經一年多,東川是行簡任職的地方,江州與東川相距迢迢數千里,兄弟兩人難以相見,樂天只能將這相思之苦寄予夢境中,一閉上眼就抵達東川,現實中的缺憾在夢境中得到暫時的補償。“天氣妍和水色鮮,閑吟獨步小橋邊。池塘草綠無佳句,虛臥春窗夢阿憐。”(《夢行簡》)“阿憐”是行簡的小字,在日常閑適的生活狀態下無事閑吟,詩人情不自禁地想到阿憐,可見思念之刻骨銘心。“夢到東川”與“臥窗夢阿憐”形式不同,夢境表達的內涵卻相同。俗話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每逢春日到來,天氣妍和,水色鮮麗,在小橋獨步之時,詩人都會將思念弟弟的濃郁之情帶入睡夢之中,在無意識的夢境中享受與兄弟團聚的溫馨和歡樂。
“醒后憶夢,情愈迫而景愈難堪矣。”(《詩筏》)[注]郭紹虞編,富壽蓀校:《清詩話續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頁。夢中歡聚原是一場空歡喜。白居易的詠夢詩超越時空,從夢中寫人,以夢境記人,借夢象懷人,將夢事喻人,解讀其懷人之夢,可以了解詩人真實的心理以及詩人重親情、友情的情感特質。
二、“夢去心不隨”之仕途夢
白居易的仕途充滿顛沛流離和艱辛困苦,但他在立身處世方面始終中立不倚。自踏上仕途之始,至輾轉于被貶之路,詩人做過噩夢亦有過美夢。以江州之貶為界,詩人對人生的思考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其仕途之夢是詩人潛意識活動的積淀,詩人的無奈情緒及悲涼心態借夢境得以調節和開解。“塊然抱愁者,長夜獨先知。悠悠鄉關路,夢去心不隨。”(《思歸》)剛踏上仕途的詩人背井離鄉,心懷滿滿的愁苦,漫長黑夜,獨自度過。夢中詩人邁過鄉關路,回到家鄉,夢醒之后,心靈仍不愿離開家鄉。在詩人的夢中,夢代替真實行動,樂天終于回到他心心念念的家鄉。
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考中進士[注]朱金城:《白居易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頁。;此后二十余年,詩人一直輾轉于被貶的仕途上。詩人在忠州、杭州和蘇州都曾入夢,有噩夢亦有美夢,可見喧囂吵嚷的仕途給詩人的潛意識造成巨大影響。長慶元年(821),結束五年的謫遷生活之后,詩人夢回忠州:“閣下燈前夢,巴南城里游。覓花來渡口,尋寺到山頭。江色分明綠,猿聲依舊愁。禁鐘驚睡覺,唯不上東樓。”(《中書夜直夢忠州》)[注]彭定求編,中華書局編輯部校:《全唐詩》,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933頁;第5036頁;第4655頁。夢中詩人故地重游,聽到猿聲,“猿聲”和“依舊愁”詮釋了詩人在忠州的日子是艱苦難熬的,因而此夜夢回忠州是個噩夢。夢境真實地反映了詩人的情感,即詩人對忠州的厭惡和抵觸。據歷史資料記載,忠州地理環境惡劣,是個“安可施政教?尚不通語言”(《征秋稅畢題郡南樓》)[注]蹇長春:《白居易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頁;第230頁。的蠻荒之地。多年之后詩人仍久久不能忘卻忠州,夢中重游忠州,可見它對詩人造成的心理陰影之大。還有《寶歷二年八月三十日夜夢后作》也描述了詩人所做的噩夢:“塵纓忽解誠堪喜,世網重來未可知。莫忘全吳館中夢,嶺南泥雨步行時。”此處描繪詩人夢見自己被流放至嶺南、在雨中艱難跋涉的場景,反映了詩人遭貶謫之后心有余悸,希望能早日退出官場。
以上兩個噩夢都說明官場生活給白居易留下了太多難以承受的痛苦和失望,詩人不得不設法緩解自己的痛苦。弗洛伊德認為,人生的目的在于追求快樂和幸福,“這種追求有正反兩個目標,一方面它旨在消除一切痛苦和不愉快的經歷;另一方面旨在獲得強烈的快樂感。”[注]弗洛伊德:《文明與缺憾》,中國對外翻譯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3頁。詩人通過作詩反映自己苦悶的夢境,嘗試分散、轉移自己的痛苦,這雖不能使詩人完全抵御現實的苦難,也不能使壓抑的無意識退卻,卻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詩人當下心靈的苦痛。
噩夢之外還有美夢。詩人被貶途中,最愛的地方是蘇州。詩人作《夢蘇州水閣寄馮侍御》:“揚州驛里夢蘇州,夢到花橋水閣頭。覺后不知馮侍御,此中昨夜共誰游?”對于頻繁輾轉在貶謫之路上的白居易來說,在蘇州的幸福時光短暫、易逝,但是這種短暫的幸福給白居易的漫長官路帶來微弱的滿足感。早已離開蘇州的詩人通過做夢又回到良辰美景之中,夢醒后回憶起與好友馮侍御一起游玩于江南的美好時光,可見他對愜意的蘇州生活難以忘懷。由此可知,詩人已掌握開解內心困苦的辦法,以豁達的心態看待人生中的起起伏伏。同時,以才能和天賦為先決條件,詩人將美好的夢境以詩歌的形式塑造出來,使詩人與現實的關系更加微妙。
“思歸”之夢描述詩人剛邁入仕途時內心陷入思鄉和忠君的兩難境地。忠州、嶺南之夢描述詩人在被貶之地艱辛和感傷的生活,但詩人沒有因此消沉,反而對世事的認識更為深入。在現實中,他胸懷“兼濟天下”的抱負;在潛意識中,他重新思考官場生活和人生意義,選擇“從容中道”的路線。蘇州之夢描述詩人在江南與友人馮侍御一起游玩的快樂時光,這段政治生活短暫、愜意,但詩人的內心沒有因此被脫離樊籠的喜悅占滿,而是在潛意識中形成“樂天知命”的世界觀。
三、“一夢誤一生”之人生感悟夢
縱觀白居易一生的行跡,從貧寒子弟通過科舉走上仕途,然后經歷顛沛流離和艱辛困苦的政治生涯,豐富的人生經歷給詩人帶來很多感悟,夢中有悟時尤甚。從詩人的詠夢詩中可以發現,其思想轉變存在一個過程,并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形成自己的生存哲學。
“人有夢仙者,夢身升上清。”“悲哉夢仙人,一夢誤一生。”(《夢仙》)詩中夢的顯義是詩人在夢中看到一個祈求修煉成仙的人,耗費一生的精力,最終也未能成仙。詩人在夢中以旁觀者的視角相信并承認神仙的存在,但是凡夫俗子不可強求成仙,于是對夢仙者“一夢誤一生”表達了同情和感傷。夢境之外,現實中的詩人已在長安永崇里華陽觀寓居,他所處的生存環境無疑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其思維,道家思想不斷刺激和導入詩人的思維,將夢境與現實結合,此夢仙者的夢恰恰是詩人目睹的感官世界中的素材。詩人對夢的思考是夢的隱義,是一種自我認知,通過此夢,詩人將老莊思想中的虛幻人生觀與佛教“苦空”的人生觀結合起來,諷刺現實生活中執著于求仙的人,對道教的核心信仰即神仙信仰持懷疑貶抑的態度,這也是對世人蕩盡妄念、與世無執的警醒。
“拙定于身穩,慵應趁伴難。漸銷名利想,無夢到長安。”(《無夢》)[注]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194頁。詩人擺脫功名利祿的束縛之后,夢中再未出現過“長安”,夢是心境最真實的反映,可見白居易在官場生活的壓抑情緒終于得到徹底地釋放。又如《安穩眠》“眼逢鬧處合,心向閑時用。既得安穩眠,亦無顛倒夢。”[注]彭定求編,中華書局編輯部校:《全唐詩》,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995頁;第527頁;第5221頁;第5221頁。“顛倒”一詞體現在詩人的心靈深處,仍然會在“獨善其身”的中隱觀念與“兼濟天下”的社會責任感之間掙扎,但詩人時刻說服自己堅持“獨善其身”的人生理想,反映在他的夢境中便是“再無顛倒夢”,此時詩人內心的政治波瀾已漸趨平靜,自在安閑,心無掛礙。再如《閑居》“書卷略尋聊取睡,酒杯淺把粗開顏。心靜無妨喧處寂,機忘兼覺夢中閑。是非愛惡消停盡,唯守空身在世間。”放棄“兼濟天下”夢想的詩人,只做自己喜愛的事情,看書把酒,心境平和閑適,“夢中閑”就是詩人現實生活狀態的寫照。
晚年的白居易病魔纏身,《夢上山》就作于這個時期。“獨攜藜杖出”是白居易的真實狀態,已患上足疾的他行動不便,“夢中足不病,健似少年日”描述的卻是夢中的他健朗如少年一般。夢醒后白居易思考“形”(身體)與“神”(精神抑或思想)的關系,“既悟神返初,依然舊形質。始知形神內,形病神無疾。形神兩是幻,夢寐俱非實。”詩人從夢中暢游到醒來時依舊患有足疾,感悟到身體雖染上疾病,精神卻可以保持健康。再如另一首詠夢詩《春眠》“枕低被暖身安穩,日照房門帳未開。還有少年春氣味,時時暫到夢中來。”年老色衰的香山居士在夢中搖身一變,盡顯昔日少年活潑強健之態。此時詩人雖患上嚴重的足疾,但他的精神是健康、樂觀的,正如禪宗所言“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世間諸世相是短暫虛幻的,樂天晚年因為受到佛教禪理的影響,看待事情更加豁達,在“獨善其身”的人生道路上不斷前行。
若將人的心理結構描繪成一座矗立在大海中的巨大冰山,那么人在夢境中的無意識就是沉沒在海水里的那部分冰山,看似影響微乎甚微,卻具有支撐著海水以上冰山的力量。白居易的儒者形象就是海水以上的冰山,后來受到佛道思想潛移默化的影響,逐漸形成沉沒于海水下的冰山。綜觀白居易一生的夢,他首先是作為一個合乎儒家傳統規范的知識分子,余英時說:“隋、唐時代除了佛教徒(特別是禪宗)繼續其拯救眾生的悲愿外,詩人、文士如杜甫、韓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更足以代表當時‘社會的良心’。”[注]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頁。此時的白居易嚴格按照儒家倡導的價值理念和行為準則立身行事,是一個典型的“儒者”。但是,隨著家庭變故、仕途變遷和朋友的離開,白居易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佛道思想的感染,由胸懷“兼濟天下”的政治抱負向“獨善其身”的心性修養轉型。白居易的人生感悟之夢,是他對現實中人生經歷的反觀,亦是他對人生經驗的思考。
解讀白居易的詠夢詩,按夢的內容劃分,每一類夢都是詩人對各階段自我生存境遇的審視,亦是詩人積極適應所處現實生活的體現。探尋白居易的懷人之夢,他是個情感豐富的人,對親人和朋友情真意切;反觀白居易的仕途之夢,他是個經歷豐富的人,對待仕途從容中道而樂天知命;思索白居易的人生感悟之夢,他是個思想豐富的人,漫步于儒釋道的文化叢林中。在解讀白居易詠夢詩的過程中,可以感受到他無意識狀態下“樂天知命”“執中用常”“無過無不及”“無可無不可”及“中和圓融”的心理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