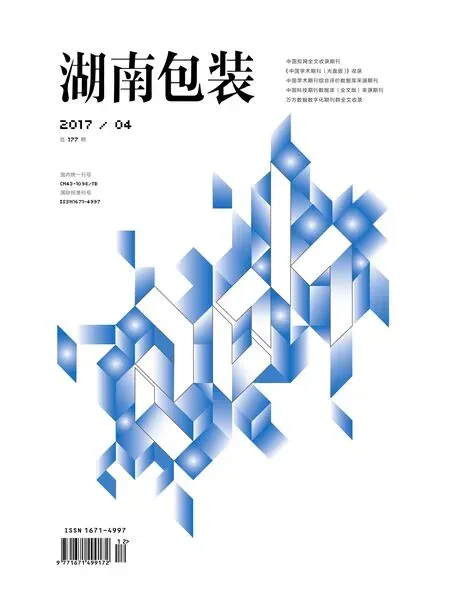湘西傳統服飾工藝在現代服飾設計中的時尚化表現
宋艷輝 丁 晨
(長沙師范學院藝術設計系,湖南 長沙 410100)
湘西地處云貴高原東緣的武陵山脈,世代聚居著土家、苗、侗、瑤等少數民族。偏僻落后、山高路險、窮山惡水阻礙了各民族之間的往來,為了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安逸地生存,各民族人民充分利用大自然中得天獨厚的動植物資源,用勤勞的雙手創造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傳統工藝,形成了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習俗:單純清麗的藍印花布,絢麗典雅的刺繡挑花,五彩斑斕的織錦,熱烈明快的剪紙鑿花,喜慶熱辣的木版年畫,鬼斧神工的木、竹、石雕,精美奇巧的陶瓷器皿和古樸神秘的祭祀繪畫等,構成了一幅五彩繽紛的民俗畫卷。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現代文明文化的傳播,各民族賴以生存的傳統工藝不但受到人們審美觀念變化的沖擊,更重要的是傳統工藝繁瑣的制作過程與現代化工業的高效率、快節奏格格不入,致使相當數量的傳統工藝面臨消亡的危機。因而,提煉這些富有民族底蘊的傳統服飾工藝精髓,結合自身獨到的審美與思維方式,將傳統服飾語言與國際時尚舞臺相締結,是文章研究的重點。
1 湘西傳統服飾工藝特征
1.1 刺繡工藝
刺繡即繡花,又名女紅,是針線在絲、棉、毛等織物上繡制各種裝飾圖案的總稱,具有實用和審美的雙重價值,是苗族服飾主要的裝飾手段。傳統刺繡織物是奢侈品,繁復的工藝、華美的材質,是財富與地位的象征,而苗族刺繡是苗族人們男耕女織的重要經濟特征。刺繡針法主要有平繡、辮繡、結子繡、堆繡、縐繡、破線繡、貼花繡、打籽繡等[1],多以紅、綠、藍等對比強烈的顏色為主,色彩鮮艷明快,使人有爽朗熾熱之感。面料以綢緞或土布為主。紋樣結構主要包括單獨紋樣、連續紋樣、適合紋樣和邊角紋樣,以動植物紋樣變形為基本構成形式,常見于頭帕、繡花鞋、腰帶、肚兜及服裝的袖口、褲腳口、裙邊、門襟等部位,如圖1肚兜,構思奇特、工藝精巧,紋樣造型栩栩如生、變幻莫測,既富裝飾性又耐磨經穿,富有濃郁的民族特色,“成為穿在身上的史書”。
1.2 印染工藝
印染是指將設計的紋樣在胚布上進行染色、印花、整理、洗水等加工處理,從而使織物富有藝術氣息。湘西印染工藝主要包括藍印、扎染、蠟染等。
藍印花布又稱靛藍花布,古時稱“藥斑布”、“澆花布”。按染色后的成品效果可將其分為藍底白花、白底藍花和雙面花3種形式,全憑人工手紡、手織、手染而成。其染織過程是將防染漿劑通過雕版拓印于布面,再浸入植物染料如靛藍染料中,氧化后即可顯出藍白花紋。藍印花布面料多以自制的棉布為主,透氣吸汗;防染漿劑也是采用天然材料,以石灰、豆粉進行調和而成,有利于身體健康,因而深愛苗族人們的喜愛[2]。色彩以藍白兩色為主,紋樣以花鳥植物居多,如圖2花鳥紋樣,通常用來制作服飾、床上用品、門簾、桌布等,目前一些有特色的賓館、酒店用得也較多,那種藍白分明、自然古樸、清新明快的藝術風格,給人一種回歸自然的感覺。

圖1 肚兜
扎染古稱“絞纈”,通常是在織物上將設計的紋樣畫好,根據紋樣或色彩的需要用針和線將織物縫成一定形狀或直接用線捆扎、折疊、抽緊等防染處理后染色,最后拆線、清洗、固色,使織物呈現出各種美麗暈染效果[3]。染料主要采用天然的板藍根植物,層層疊疊、扎線松緊不一形成的藍白斑紋,洋溢著濃郁的鄉土氣息。隨著化學染料的出現,對織物的多次捆扎,不同色彩、不同程度的浸染,使傳統的扎染面料由藍白兩色變成了現代的五彩斑斕,如圖3扎染面料,五顏六色的扎染服裝已成為各大旅游景區一大亮麗的風景。
蠟染古稱“蠟纈”,是一種以蜂蠟為防染手段的印染手工藝。用蠟刀蘸上蜂蠟在白胚布上繪制圖案,在染色與翻動的過程中,利用蠟與水相互排斥的原理,染液不能滲透或細微地侵入而形成色彩差異,冷卻后蠟花自然龜裂而形成“冰裂紋”,再經過加熱去蠟、漂洗,使布面呈現獨特肌理、變化莫測的藝術效果[4]。傳統的蠟染采用當地自然生長的植物作為染液進行浸染,紋樣主要是花、鳥、蟲、蝶和一些幾何圖形,如圖4蠟染面料,主要用于床上用品。為了適應市場發展的需要,蠟染的色彩豐富多彩,紋樣也根據消費者的喜好增加了風土人情,廣泛用于服飾、餐飲、旅游、壁掛等工藝用品。

圖2 花鳥紋樣

圖3 扎染面料
1.3 土家織錦
土家織錦又稱“西蘭卡普”,土語中“卡普”指花,“西蘭”指被面或鋪蓋,因而土家織錦又俗稱“打花鋪蓋”或“土花鋪蓋”。土家織錦是以紅、藍、黑色等棉線為經線,用色彩鮮艷對比強烈的絲、棉、毛線為緯線,在傳統的木制織機上,以通經斷緯手工織造的方法反面挑織而成,是土家族傳統的手工藝術瑰寶。土家織錦圖案排列簡潔有序,基本結構以菱形、方格形、復合形等幾何多邊形為主,常以典型的二方連續或四方連續紋樣形式出現。紋樣題材多以自然花卉、人物場景、生活器皿、民間民俗圖案為主,如圖5織錦紋樣,因其色彩艷麗、紋樣圖案清晰飽滿,廣泛應用于床上用品、壁掛、日常裝飾用品及服裝中,如:蓋毯、壁掛、地毯、圍巾、香袋、提包、服裝、鞋墊等,裝飾性極強。通過二方連續的形式在單元格內填充適合的植物花卉紋樣,形式優美,色彩絢麗奪目,對比強烈,具有鮮明的民族裝飾風格。古樸典雅的土家織錦常用在服裝的領口、袖口、裙邊、門襟等邊緣處,用土家織錦作緣邊裝飾的衣裙常被人們稱為“土布花衣”[5]。
2 傳統服飾時尚化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
2.1 傳統服飾工藝的傳承與創新

圖4 蠟染面料

圖5 織錦紋樣
民間藝術是時代的產物,其內涵與外延隨時代的需要而改變,因此湘西傳統工藝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在內容與形式上也應體現時代的特征,在傳承的基礎上滿足社會的需要,走時尚化發展道路。傳統服飾工藝雖然在一定形式上保留著湘西人民古老的生活意識形態和生命軌跡,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社會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大量的年輕人受到都市文化的影響,對傳統服飾工藝越發冷漠,認為傳統工藝過時、土氣、落后,難以產生經濟效益,不愿子承父業,紛紛外出務工,致使精湛的傳統服飾工藝逐漸被邊緣化,失去生產傳承的土壤。因此,在當今多元文化與現代服飾流行時尚面前,傳統服飾應主動地與時尚化的設計理念接壤,在遵循時代客觀發展規律的前提下,果斷地傳承之精華,摒棄其糟粕,借鑒其他藝術文化形式不斷推陳出新,融合現代先進工藝技術進行時尚化再設計。在保留傳統工藝所創造的文化價值與美學感受的同時,縮短制作周期、降低人工損耗,使傳統服飾文化在傳承與創新的過程中逐步實現時尚化、規范化、統一化,這是傳統服飾時尚化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本土服裝設計師立足民族、放眼世界的根本[6]。

圖6 織錦紋樣在服裝中的運用
2.2 現代消費市場的審美心理需求
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引起的時尚趨同化激發了現代人們的審美意識,使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對傳統服飾的消費,從基本的經濟行為上升為彰顯時尚個性的審美行為,不再滿足于產品的實用性,而是追求更高層次的個性化的精神欲求。湘西傳統服飾工藝作為展示與傳播湖湘傳統文化的窗口,在消費者面前展現出的是其濃郁的民俗文化和自然樸素的民風,消費者多數是被其豐厚的民俗文化底蘊而吸引,但這對于身處現代時尚化語境下的消費者們還不夠激發他們的購買欲望,他們期望這些傳統民俗服飾品不只是傳統的文化紀念品或服飾收藏品,而是能夠在滿足他們時尚個性化消費需求的基礎上,結合現代審美趣味、流行趨勢和生活需求,運用現代的設計理念和手法進行再設計,使其更和諧地融入現代生活中,成為既與現代時尚服飾接軌又能傳承民俗文化的實用性與審美性兼具的服飾品。
3 傳統工藝在服飾設計中的時尚化體現
3.1 傳統工藝在服飾設計中的平面時尚化表現
民族服飾耐以生存的農耕社會在工業化時代的沖擊下已逐漸瓦解,時尚成為民族服飾賴以生存的落腳點。服飾設計中的平面時尚化表現形式主要有數碼印花、印染及手繪等,運用這些技法直接或間接地將傳統服飾紋樣在時尚的包裝下,融入現代設計理念,將紋樣中的色彩、形狀及大小變化、點線面的關系融入現代設計中,以新的設計技法重新載入人們的生活。如圖6織錦紋樣在服裝中的運用,為依坊服飾品牌設計的2015年春夏連衣裙產品,將織錦紋樣的色彩、圖案與構成形式進行解構、重組,創造于服裝的前胸和后背上,營造出局部民族味的奇特效果,使織錦工藝濃郁的民族色彩不僅沒有古樸、土氣的味道,反而達到了一種視覺的和諧,贏得了客戶的好評。

圖7 傳統工藝的運用
3.2 傳統工藝在服飾中的立體時尚化表現
立體時尚化表現方式主要是通過刺繡、褶皺、剪切、撕扯、堆飾(浮雕)、拼貼等傳統技法直接或間接地運用于服裝的整體或局部,改變面料原有的形態特性,但不破壞面料的基本內在結構而獲得,表現形式直觀又富有個性化[7]。立體褶飾沿用扎染“捆扎”技法,將縫線收緊或拉伸在面料的表面形成凹凸紋理和豐富變化的肌理結構;拼貼是指將不同材質、不同形狀、不同風格的面料,按照點、線、面的構成規律運用拼縫的方式塑造出富有立體感的特色服飾,產生絢麗多彩的視覺效果。如圖7傳統工藝的運用,運用立體褶飾技法將面料按照設計的圖形捆扎、抽緊,賦予面料新的生命,與拼貼技法相結合,合理地運用于抱枕設計中。在服飾設計時,以刺繡、鏤空、褶飾等傳統工藝為核心,融入西方時尚元素,面料采用真絲、羊絨、棉、麻等天然面料,以簡潔大氣的款式造型創造出時尚潮流的新中式服飾,受到大量的社會名流、國際友人及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界人士的喜愛,如日本的褶皺大師三宅一生、法國Dior首席設計師約翰·加利亞諾的設計作品,永遠少不了中國傳統服飾文化的身影。
4 結語
湘西傳統服飾工藝古樸典雅,是我國民族文化藝術的寶庫,其豐富多彩的服飾文化資源聚集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但隨著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對傳統文化的沖擊,傳統服飾工藝的全手工制作,生產周期長,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與現代化高效快速的生產方式格格不入,使傳統服飾文化成為一種戲劇化、儀式化、觀賞性的商品文化。把握傳統服飾文化價值“神”的核心,提煉其傳統服飾語言元素,總結其款式特征、色彩要素、結構造型、人文因素等,挖掘其深厚的文化內涵,通過視覺意象的傳達和新的表達方式與現代的設計理念、手法和諧融合,使民族服飾語言走上國際時尚舞臺。按照現代人的審美標準,創造出符合現代時裝市場需求的服裝,使之重新納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完成真正意義上的傳承和創新發展民族服飾文化產業,同時促進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這是我們當前面臨的迫切任務。
[1] 周夢.苗侗女性服飾文化比較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學, 2010,(5):98-102.
[2] 唐帆.湘西藍印花布圖案與藝術形式研究[D].株洲,湖南工業大學,2009,(6):15-20.
[3] 盧玉琪.扎染褶皺結構在服裝設計中的創新性應用[D].北京,北京服裝學院,2016,(12):4-22.
[4] 周成飛.貴州地區蠟染“卍”字紋研究[D].北京,北京服裝學院,2016,(12):10-59.
[5] 冉紅芳.土家織錦文化變遷研究[D].北京,中南民族大學,2007,(5):2-20.
[6] 王莉詩.土家族服飾時尚化研究[D].武漢,武漢紡織大學,2013,(3):21—45.
[7] 周祥.傳統民間藝術對服飾時尚潮流的影響研究[J].湖南包裝,2016,31(3):4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