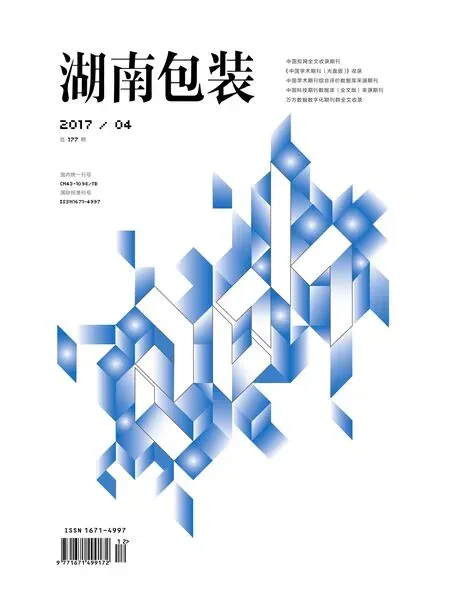地方性知識視角下非遺數字化平臺的構建
——以“新通道”項目為例
謝慧玲 張朵朵 何雨威
(湖南大學設計藝術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2)
1 傳統的非遺數字化平臺的內容建設問題及思考
“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在其名稱中冠以‘非物質’的定語,是以它的存在脫離了物質載體,或其價值遠大于承載它的物質載體”[1],例如:節慶活動、傳統手工藝等。這類以口傳身授為傳承方式的非遺因其傳承方式的局限性及傳承人數量逐漸減少,正面臨逐漸消亡的可能[2]。在非遺保護和傳承中,最傳統的方式是建立線下實體博物館,以物品為媒介還原文化情境,再配以文字、音頻或視頻解說重現文化現場。但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催生各領域產生數字化的轉型。非遺的傳播與保護也從線下博物館的形式向線上數字化平臺擴展。這些真實的傳統文化藝術結合數字化技術不斷地設計開發,并運用互聯網技術進行全面推廣,最終能使非物質文化得到活態傳承[3]。但在當下非遺數字化平臺的建設過程中,普遍存在著如下問題。
1.1 陳舊、單一的展示維度
非遺數字化平臺的建設通常以省為單位,主要記錄的是省內申請成功的國家級和省級非遺名錄和非遺傳承人,大多數平臺僅用文字、音頻、視頻等之類的靜態資源對某項非遺項目進行闡釋說明[4],以一種文化數據庫的形式存在著。對比實體博物館更活態且有互動性(如邀請非遺傳承人開辦講座、與公眾進行交流),線上的數字博物館的知識呈現模式則顯得陳舊、單一。
1.2 缺少對內部受眾的思考
這些平臺在內容組織結構上無外乎分為三大類:與非遺知識切身相關類(如某項非遺項目的介紹和記錄、傳承人)、與非遺資源相關類(如政策法規、新聞報導)以及非遺知識交流類(如學術論壇、保護論壇)。依據平臺內容的分類可以將非遺知識傳播的受眾歸納為:與非遺行業相關的從業人員;行政機構相關人員;與非遺學術研究相關的人員。依據當地非遺知識的文化擁有關系,又可以將平臺的受眾分為“外部受眾”(異文化群體)與“內部受眾”(地方文化持有者——既包括作為非遺知識持有者的非遺傳承人,也包括地方其他知識持有者的非遺社區普通居民)[5](表1)。對于外部受眾的需求,目前所有的非遺數字化平臺照顧得很周到;而對于內部受眾的考慮,卻忽略了非遺項目當地的普通居民,所有知識的描述都是圍繞著“社區精英”——非遺傳承人及“非遺項目”,這易使非遺社區內的普通居民對本是自己地區內的文化產生疏離感。
1.3 非遺知識的呈現缺乏“整體性”
平臺中所有內容組織結構的職能都是讓公眾能多方位地了解非遺項目,但在這之中存在的問題是,在對第一類“與非遺知識切身相關類”作介紹時,非遺項目和非遺傳承人往往從其原生環境中剝離出來,被當作獨立的個體。這易導致公眾在認識非遺時會缺乏“整體性”的認知,不利于公眾對非遺形成“整體保護”的意識[6]。
出現上述問題主要在于技術應用形式不夠創新、對受眾考慮不夠全面以及對于非遺知識的特質的不正確理解。對于前者,可借鑒其他成熟的數字博物館平臺的技術,如使用虛擬現實、三維影像制作等技術,以豐富的展示維度增強公眾對于非遺的認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顯著特征是其文化生態特征,它的產生與發展被認為是與周圍自然、社會環境變化密切相關[7]。因此后兩者則需平臺的設計者、非遺知識的記錄者正確、整體地認識到非遺社區普通民眾和“社區精英”——非遺傳承人一樣是非遺得以傳承和延續的重要力量以及非遺項目的“地方性”、“語境性”特質。非遺來自于特定地區、特定群體,是基于當地社區的生活、生存需要而產生的,不僅要看到它的獨特性,也就是地域特色,還需有整體觀,系統性地將非遺項目的生態環境、人文活動等當地資源考慮進非遺項目敘述中來,將非遺項目的本真還原給公眾,通過對地方的敘述喚起普通民眾對于非遺項目的親密感和歸屬感。

表1 非遺數字化平臺的受眾分類

表2 新舊平臺的對比
2 地方性知識平臺的建設——以“新通道”為例
基于地方性知識的視角,就目前非遺數字化平臺所存在的問題,提出非遺數字化平臺的新形式——地方性知識平臺。重新劃分了“受眾群體”,將同是非遺傳承重要力量的當地普通民眾也包攬在內,并增加了內部受眾與平臺的交互行為,他們作為地方知識的持有者,同時也將變成地方知識重構的深度參與者。此外,將舊平臺內的“內容組織架構”作出調整,從文化生態系統的角度考量非遺知識的重構與呈現,以“風景+人文+物語+社區”的資源整合形式排布非遺項目所在地的生態、人文、物質資源以及非遺項目和當地社區的動態,使之作為一個有序的整體(表2)。下文將以湖南大學設計藝術學院的“新通道”(New Channel)設計與社會創新系列項目的“新通道”地方性知識平臺為例,通過分析“新通道”地方性知識平臺的建設過程,為地方性知識如何獲得及地方性知識在平臺上如何重構提供詳細說明。
2.1 地方性知識平臺:地方性知識視角下的非遺數字化平臺的新形式
“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這一概念原由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茲(Clifford Geertz)在1982年于其論文集《地方性知識》一書中提出,主要應用于人類學中對異文化的研究,它將對異文化的闡釋放置于其本地域的環境中,包括整個地域環境系統中的人、地區以及上下文背景即情境(context),并通過與內部“文化持有者”對話使文化得到確切的詮釋。非遺作為特定區域內的產物,是特定群體共享的地方性傳統,是當地社區所共有的地方性知識。基于非遺知識的“地方性”、“內嵌性”(它無法與當地人及地域剝離開來),針對非遺傳承和知識共享的數字化平臺則更像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平臺”,在其上對非遺項目的闡釋需要更加的整體、系統、保真,以確保外部人士對非遺項目的正確理解,增強非遺社區群眾的地方認同感,更好地促進非遺的傳承和保護。

圖1 “新通道”項目系列地方性知識平臺網站
2.2 “新通道”地方性知識平臺的建設
“新通道”(New Channel)項目組主要在偏遠地區少數民族聚居區針對當地的文化保護傳承、經濟和文化振興與可持續發展開展一系列設計與社會創新實踐活動,目前已在湖南通道、隆回花瑤、四川雅安等地以工作營的形式深入地區進行實踐工作。每次項目組成員都大體上分為兩組:一是設計組,主要通過與非遺手工藝傳承人或普通手藝人協同設計(co-design)將非遺項目轉化成創意產品以及為當地特色農產品做包裝設計;二是研究組,由研究者和影像記錄者合作,重點就非遺項目及當地社區等問題采訪非遺傳承人及當地居民,產出為研究報告、論文等學術成果及文化紀錄片,其成果也支撐設計組做創意產品設計。在“新通道”系列地方性知識平臺(圖1)上,承載的內容以文化研究組的成果為主,首要重點是地域文化知識的推廣傳承。下文將以“新通道”地方性知識平臺為例案,詳細闡述其搭建過程及方法。
(1)地方性知識獲取的新手段:協同創作、參與式影像
研究者對地方性知識的獲得不能是機械地進行記錄,而是要同“文化持有者”也就是當地人展開積極地商談對話,確保以接近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理解文化[8],形成準確的闡釋成果。當地人不僅包括當地文化精英——非遺傳承人,還包括當地普通手工藝人和社區居民。項目組除了使用田野調查的手段對非遺項目、地區物質資源、社區結構、當地生活方式等地方性知識進行獲取外,還采用了更活態的知識獲取方式——協同創作、參與式影像。前者應用于獲取地區內手工技藝類非遺知識,因手工藝知識的隱性(Tacit)特質[9],研究組除了通過有手工藝研究背景的“專家型”研究者與手工藝人的交流、溝通獲得部分隱性知識外,還通過記錄設計人員與手工藝人協同設計過程——手工藝人通過與設計人員產生實踐上的交流,將手工藝知識與設計人員共享,設計人員通過“做中學”理會手工藝的關鍵知識,隱性的手工藝知識得以外顯化——的方式[10],使用影像民族志工具,捕捉實踐活動時的難以察覺的、復雜的部分[11]。后者應用于當地文化的影像記錄,影像記錄者將影像的記錄權和編輯解讀權移交給傳承人和研究者,只作技術的支持,減少被攝物被誤讀的可能性[12]。如在非遺手工藝拍攝時,讓在傳統上作為被攝對象的非遺傳承人掌握主動話語權——掌控影像的拍攝角度,因為他們知道在關鍵時刻需要關注哪個動作、從何種角度進行觀察最佳;他們還能主動指出一些內部文化持有者所共知而外部人士不易觀察到的關鍵細節,使手工藝知識更為客觀、整體。在影像制作后期,傳承人也參與影片的剪輯篩選,有專業知識背景的研究者協同影像設計人員完成影像成品。在此過程中,傳承人的主動參與及研究者的協助使影像資料更好地呈現了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另外,由于深度的參與,傳承人也在行動中加強了自己的主體觀念及對非遺文化的認同感。
(2)地方性知識在平臺上的重構:有序化、系統化整合
非遺知識在數字化平臺上的呈現還需注意的一點就是非遺知識的“重構”。非遺的文化生態特征要求我們注意到非遺在地方的生態關聯[13]。“新通道”地方性知識平臺以地區為單位,根據地區內資源和項目成果的性質最后歸納創造出“風景、人文、物語、社區”4個模塊的資源整合方式,使所有內容的排布更有序。以“新通道”地方性知識平臺的“花瑤花”子平臺為例[14](圖2),“風景”模塊圖文并茂地記錄了當地美不勝收的生態資源;“人文”模塊介紹了花瑤當地的民俗節日、民族手工藝及非遺傳承人故事等文化資源;“物語”模塊詳細記錄了花瑤挑花、灘頭年畫、造紙工藝、竹編工藝這些傳統手工藝以及設計人員和當地人協同設計的創意產品與基于當地物質資源所做的一些創意設計;“社區”模塊則著重于社區互動,包攬有“花瑤花”項目成果在外界所參展的詳細記錄、當地社區新動態及項目組在當地的工作記錄。
將項目組的調研成果和設計成果分門別類地放進4個模塊中,關于一個非遺項目的闡釋,可以在不同的模塊中找到其對應的相關內容。以“花瑤挑花”為例,在“物語”可以深入地了解手工技藝及基于挑花技藝設計的創新產品,設計同行和手工藝人也能通過設計實際案例激發創作的靈感,更有利于非遺的活態傳承;“人文”模塊內你可以了解關于挑花人的故事;在“風景”和“社區”內你可以看到身著挑花筒裙的倩影。對于“花瑤挑花”雖然是以“人文”、“物語”的描述為主,但“風景”、“社區”處的內容與它們相呼應、補充,讓外部人士有更全貌、系統地理解。非遺項目的這種呈現形式加強了它在社區內真切的存在感,對當地居民來說,也增加了與非遺的親密感。
項目組踐行“地方性知識與人、地區、情境是密不可分的”,系統地通過文本與影像相結合的方式對當地文化資源、物質資源、精神資源進行了詳盡的記錄,并在關鍵闡釋中將話語權交給專業的非遺社區人群以保證知識的準確性,這樣一整個資源體系的呈現讓非遺項目和當地地域文化能夠更好地被外部人士理解,當地人也能對其價值產生認同,并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圖2 “花瑤花”平臺的風景、人文、物語、社區版塊
3 結語
從地方性知識的視角出發,依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態文化”特征和“地方性”特質,提出非遺數字化平臺的新形式——構建以非遺項目及傳承人為核心,以其他地方知識作為補充說明的地方性知識平臺,強調在文化生態系統中對非遺知識進行闡釋,注重非遺知識的整體性、本真性。同時還要注意在知識獲取時當地文化持有者的參與狀態,避免機械地記錄,確保非遺知識更好地呈現了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新通道”地方性知識平臺對傳統非遺平臺的“受眾群體”及“內容組織架構”進行重新定位與建設,將非遺知識闡釋的重心轉移到“地方”上來,讓非遺項目當地普通民眾對非遺產生認同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在平臺上交付“地方”以權力,以期望作為當地文化的持有者的本土居民能主動與外界分享當地的文化,成為非遺傳承與知識傳播的內生性力量,這是目前“新通道”平臺所欠缺的。因此如何讓他們加入到平臺中,平臺以何種方式支持地方權力的參與,是“新通道”系列項目所有地方性知識平臺需要進一步探索的方向。
[1] 彭冬梅.面向剪紙藝術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技術研究[D].浙江大學 ,2008.
[2][3]王麗娜.“互聯網+”時代山西面塑藝術的數字化保護與設計開發[J].湖南包裝,2017,32(2):78-81。[4][6]宋麗華,李萬社,董濤.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與知識整合平臺建設[J].圖書館雜志,2015,34(1):73-81.
[5] 王明月.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數字化風險與路徑反思[J].文化遺產,2015(3):32-40.
[7][13]耿波.地方與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方性與當代問題[J].民族藝術,2015(3):59-67.
[8] 王邵勵.“地方性知識”何以可能——對格爾茨闡釋人類學之認識論的分析[J].思想戰線,2008,34(1):1-5.
[9] 張朵朵.隱性知識:傳統手工藝設計創新研究的微觀視角[J].裝飾,2015(6):117-119.
[10] 張朵朵,季鐵.協同設計“觸動”傳統社區復興—以“新通道·花瑤花”項目的非遺研究與創新實踐為例[J].裝飾,2016(12):26-29.
[11] Nicola Wood, Chris Rust, Grace Horne :A Tacit Understanding: The Designer”s Role in Capturing and Passing on the Skilled Knowledge of Master Craftsme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 Vol.3 No.3 2009,65-78.
[12] 徐村,蔣友燏.淺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參與式影像記錄方法[J].《藝術與設計:理論》 ,2014(5):147-149.
[14]“花瑤花”地方性知識平臺網址:http://newchannel.design-engine.org/huayaoh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