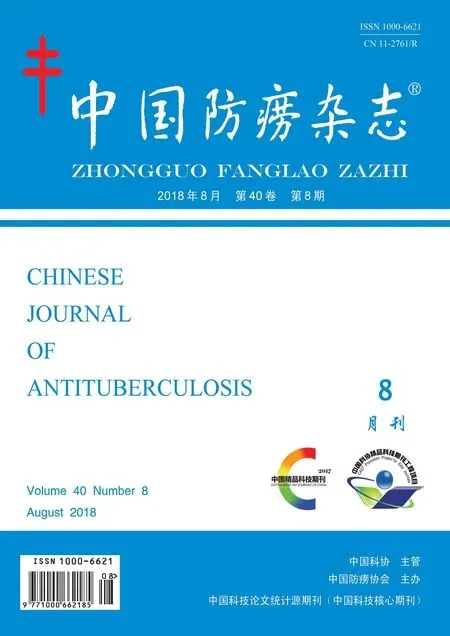做科研型結核病醫生 實現全球結核病戰略目標
沙 巍
世界衛生組織的“2015年后全球結核病戰略”的目標是在2015年和2035年之間將結核病病死率降低95%,將新發病例減少90%,旨在終結全球結核病流行[1]。但是縱觀近年的結核病全球疫情,2016年新發結核病患者1040萬例,死亡167萬例;新發耐多藥結核病患者64萬例,死亡24萬例[2]。所以,全球結核病疫情并沒有顯著下降,耐多藥結核病和死亡患者較2015年還有增加的趨勢。中國是全球30個結核病高負擔國家之一,結核病疫情、耐多藥結核病疫情和結核病并發艾滋病疫情均在全球居高位,不僅對公眾健康具有嚴重的威脅,更是導致相當一部分患者因病返貧和因病致貧的重大傳染病之一。
s1998年英國Sanger中心和法國Paseteur研究所科學家合作完成了結核分枝桿菌 H37Rv株的全基因組測序工作,一度曾認為可以揭示結核病的發病機制并推動新的疫苗研制。然而時至今日,雖然隨著γ干擾素釋放試驗和分子生物學技術的廣泛使用,結核病的診斷技術有了飛速的發展,但在結核病的預防和新的治療方案研究中,仍缺乏具有突破性的進展,結核病患者仍需要經過漫長的治療周期,耐多藥結核病患者的治愈率依舊沒有改善,健康人群和密切接觸人群仍然缺乏有效的預防措施。隨著基礎科研技術的發展,人類可以揭示結核分枝桿菌4000多個蛋白中每一個蛋白的功能,亦可以發現宿主對抗結核分枝桿菌的天然免疫和獲得性免疫的各種效應細胞、分子和通路。亟待解決的是如何將這些基礎研究進展轉化為可以在臨床應用的成果,臨床問題如何追溯到細胞和分子層面,需要在基礎研究和臨床研究之間建立互通的橋梁。在人類與結核病這場戰役中,不僅需要基礎研究科學家,還需要大量的臨床研究科學家,即科研型的臨床醫生。
一、合格的科研型臨床醫生是推動醫學發展的中堅力量
科研型醫生指不僅能承擔臨床工作,同時具備科研思維和能力,并善于在臨床實踐中發現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的醫生。一方面他們應該具備豐富的臨床醫療實踐經驗,扎實的理論基礎,并善于在工作中進行總結并發現臨床中尚待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他們應該具備良好的科研思維和開展臨床科研的能力。王辰院士曾將臨床醫生形象地分為:醫匠、醫師和醫帥三大類,“醫匠”是依靠自己的經驗進行臨床實踐工作;“醫師”按照科學的原則性行醫,但被動地接受指南和專家共識;而“醫帥”為醫學提供創新性的診斷及治療方法,引領醫學發展,是真正的醫學大家[3]。
現代醫學的進步離不開臨床科研的發展,而臨床科研的實施離不開科研型臨床醫生的工作。結核病的化學治療方案從單純使用鏈霉素到短程化學治療方案走過了30余載,初治結核病短程化學治療方案有全球多個國家的臨床研究的數據支持[4-7],凝聚了大量臨床研究者的智慧,使得結核病患者的治療療程從18個月縮短到6個月,顯著提高了結核病患者的治愈率,全球的結核病疫情大幅度下降。該短程方案至今仍作為敏感結核病的標準化療方案在全球推廣。
國內亦涌現了許多著名的醫學科學家。1987年,我國血液病學專家王振義教授通過長期的臨床研究,發現全反式維甲酸可治療帶有早幼粒白血病基因(PML)-維甲酸受體基因(RARα)融合基因的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然而全反式維甲酸大規模運用以后,醫生們發現,10%~15%的患者表現出原發性耐藥。在翻閱了大量資料以后,王振義和陳竺聯合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團隊開展了全反式維甲酸聯合三氧化二砷治療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的臨床研究并取得了成功,挽救了成千上萬例患者的生命,并已成為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的標準療法[8]。這是一位兢兢業業從事臨床科研的醫學科學家對人類健康所做的貢獻。這項研究獲得多項國際腫瘤研究獎。2010年,王振義教授獲得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實至名歸。
二、科研型醫生是提出臨床問題并解決臨床問題的核心力量
臨床醫生在診治病患的第一線,是以發現病因并提供適宜治療措施為己任的健康守護者,對疾病的病因、發展和預后的認識很多都是從診療過程中分析總結患者的臨床表現而得來的。因此,臨床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和需求是臨床科學問題的一個重要來源;善于提出問題,積極去追溯問題,是科研型醫生最重要的潛質。
結核分枝桿菌的發現者羅伯特·科赫是結核界乃至微生物界臨床科研型醫生的典范。他1866年從醫學院畢業后,先是在軍隊中當隨軍醫生,普法戰爭后在東普魯士一個小鎮當鄉村醫生。當時結核病在全球猖獗蔓延,導致了1/7的人口死亡,科赫提出了“人類為何會得結核病”的臨床問題和“結核病是由特殊病原導致”的科研假說。他研究了98例人體結核病、 34 例動物結核病,接種了496頭實驗動物,取得了43份純培養,并在 200 頭動物中進行細菌毒性試驗,并不斷改變染色方法,在第271份標本中發現了結核分枝桿菌。繼而,他提出了“科赫法則”,為病原微生物學系統研究方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并創建了近50種診治人和動物感染性疾病的方法。他從一名鄉村醫生成為了現代微生物學和感染病學的奠基者,依靠的是臨床的實踐及自身敏銳的觀察力和縝密的思維能力。
結核病這個亙古已有的傳染病迄今尚未被消滅。在臨床診治的過程中,醫生會面臨各種困難和困惑,此時所需要的是善于刨根問底地挖掘問題,更善于將這些問題凝練成為科學問題,并與基礎或轉化醫學科學家合作攻關解決問題的科研型結核病醫生。
三、臨床醫生從事臨床科研是職責所在
現代醫學對臨床醫生的要求不再是機械地重復診療行為,埋頭看病者充其量只是一個“平俗”的臨床經驗的積累者[3]。進行臨床科學研究是醫生的職責和義務。醫生天然就是研究者,臨床和研究是渾然一體、高度統一的,一名成功的臨床醫生面對任何一例患者的診治程序本身就是科學研究的成果。世界上也不可能有一組不直接從事醫療工作的研究人員代替醫生從事有關診斷和治療的相關研究工作。因此,醫療和科研工作不但不沖突、不對立,反而相得益彰。臨床科研工作的開展有助于培養臨床醫生自身科學的思維方式和嚴密的邏輯論證能力,有助于其用創新的思維和方法來解決問題,改善自身的診療行為。
國內肺科的締造者之一吳紹青教授深以控制結核病疫情為己任,放棄美國的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奔赴嘉興研制國產異煙肼,繼而在國內多家醫院對活動性肺結核患者進行臨床研究,證實國產異煙肼療效高、不良反應小、價格低廉,使國產異煙肼在全國推廣,眾多肺結核患者獲得了及時的治療[9]。之后,吳紹青教授繼續與上海第一醫學院病理教研組和微生物教研組協作,進行結核分枝桿菌對異煙肼的耐藥性與致病力關系的研究,為當時給予結核病患者長期合理的接受抗結核藥物治療提供了科學依據[10]。吳老是國內結核病臨床科研的開拓者,他濃厚的家國情懷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值得每一名結核人效仿和傳承。
四、加強自身科學研究潛質的挖掘,促進結核病領域臨床研究的發展
現代的醫學教育體系已經為臨床輸送了大量具有臨床科研復合型潛質的醫生,但是并不意味著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能成為優秀的科研型醫生。結核領域亦不例外,需要醫生從以下方面進行自我培養,提升科研能力。
1. 閱讀大量文獻:通過對國內和國外的文獻學習,可以了解學科前沿的最新動態,厘清關注問題的發展脈絡,探尋學科的研究熱點和發展趨勢。一名優秀的結核病科研型醫生必定有非常卓越的文獻搜索、整理和總結能力,不僅關注結核領域的文獻,也關注感染領域乃至于關注與結核相關的邊緣學科的文獻。
2. 積累科研知識:結核病的臨床科研不僅限于結核學科,還要求臨床醫生必須學習系統的科研方法及流行病學、統計學等相關學科的基本理論知識,掌握先進的科研方法原理,如分子生物學、分子病理學和各種組學的理論和應用。此外,必須掌握高質量的臨床研究設計原則和要素,熟悉結核病診療臨床試驗的特殊要求,才能避免在研究中出現偏差,確保得出科學的結論。
3. 培養團隊精神:現代醫學研究早已不是個人的單打獨斗,科研型醫生要具有良好的溝通能力及相互協作的團隊意識,善于與基礎學科、轉化學科和其他臨床學科合作。團隊的構成可以以項目為核心組建,也可以以學科建設組建,同時要注意形成學科間的有機結合,每名成員有自己的發展目標、工作計劃,有數據和成果的定期交流和分享,共同討論解決臨床研究中的各類問題。
4. 具備科研誠信和“以人為本”的職業道德:科學研究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很可能會出現研究結果不盡如人意的情況。科研的目的是解決臨床科學問題,而不是單純為了課題申請、文章撰寫和職稱晉升。科研允許失敗或出錯,但是絕對不能有偽造、篡改、剽竊等行為。臨床科研的研究對象是疾病患者,因此,所有的診療手段必須符合倫理要求,堅持依法行醫和確保患者安全。
2017年發布的《“十三五”全國結核病防治規劃》明確提出了應加強結核病科研與國際合作,開展多層次多形式的學術交流和醫學教育,培養結核病防治人才,提升防治人員工作能力和研究水平。 “功以才成,業由才廣。”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學技術是人類的偉大創造性活動。一切科技創新活動都是人做出來的。”每一名結核醫生必須以高度的責任感和強烈的使命感,不斷學習、加強創新科研的思維和理念的培育、推動臨床科研的開展,成為實現全球結核病戰略目標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