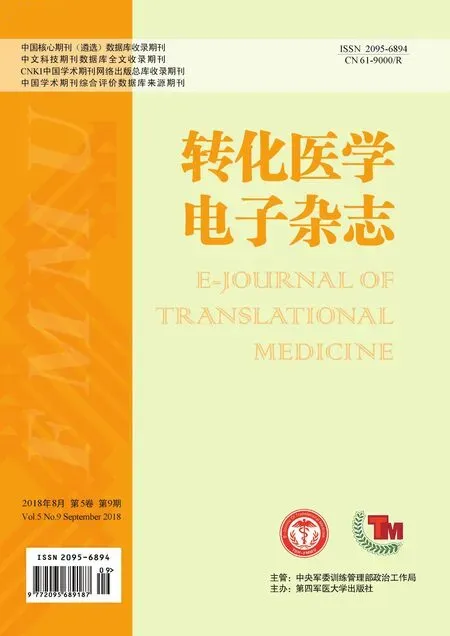計算機輔助藥物設計的研究進展
劉 軻,陳 曦,蔡如意,應沂岑,郭雪媛,趙清璇,初 明 (北京大學醫學部基礎醫學院,北京100191)
0 引言
藥物上市是一個耗資巨大并且漫長的過程。在過去的十年中,開發和推向市場的藥物成本增加了近150%。但是進入臨床試驗的藥物有90%最終未能獲得FDA批準,其主要原因是合理藥物設計(rational drug design)中所遇到的各種問題[1]。隨著生物信息學和計算機技術的飛速發展,計算機輔助藥物設計(computer aided drug design,CADD)取得了巨大的進展。目前,CADD可以實現對成千上萬個分子進行快速篩選,不僅降低了藥物研發的成本,而且大大縮短了藥物上市的時間,在藥物研發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正因為如此,如何提高CADD的準確性和靈敏性也成為研究的熱點。根據計算機藥物篩選原理的不同,人們提出了基于結構的藥物設計(structure?based drug design,SBDD)、基于片段的藥物設計(fragment?based drug discovery, FBDD)和基于配體的藥物設計(ligand?based drug design, LBDD)。 本文對這3種CADD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
1 基于配體的藥物設計
在合理藥物設計中,在藥物靶點的蛋白質結構不明確的情況下,LBDD是目前最合理的藥物設計方法。LBDD是通過分析已知的與受體結合的配體結構來進行藥物設計,又稱為間接藥物設計,包括藥效團模型、定量結構?活性關系模型 (quantitative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 QSAR)[2]。 藥效團是藥效特征元素的集合,保持化合物活性所需的結構特征,可以反映這些化合物在三維結構上的一些共同原子、基因或化學功能結構及空間取向,這些往往決定著配體的活性,以此分析已知的與受體結合的配體的共同藥效特征來篩選藥物[3]。QSAR是通過以配體和靶點的三維結構為基礎,根據分子內能變化和分子間相互作用的能量變化,將已知的一系列藥理的理化性質和三維結構參數擬合出定量關系,再進行優化改造,因此QSAR不僅可以模擬結合受體的配體的結構特征,還可以預測藥物的活性,自從Corwin Hansch建立了QSAR的方法以來[4],QSAR經過不斷的改進和優化,已經演化為可分析包含成千上萬種不同分子結構的超大型數據集統計和機器學習技術。人們采用LB?DD的方法成功篩選獲得了大量的臨床藥物,如諾氟沙星、氯沙坦[5]、佐米曲普坦[6]等。 LBDD 為合理藥物設計奠定了基礎。
然而,LBDD只分析了配體的結構特點,忽略了受體結構對藥物和靶點相互作用的影響,因此經常出現假陽性[2]。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受體和配體的空間構像需要不斷變化以促進相互之間的結合[7-8]。蛋白質并不是靜止不動的,其功能受其內部動力學的控制,了解其動態特性也是非常重要的[9]。雖然目前已經建立了多種模型,但是沒有一種可以適用于所有的配體結構,因此,LBDD仍存在很多未解決的問題,在未來的發展中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2 基于結構的藥物設計
在藥物設計與開發中,如何改善設計方案是長期以來困擾著研究人員的問題。例如在1991年至2000年這十年時間里,因為吸收不良或代謝過度而未通過審查的候選藥物就高達90%[10],所以如何保障藥物的效力與安全成為了研究者最大的挑戰。研究人員急需尋找一種具有更短的開發時間與更高的效力、功效和口服生物利用度的藥物設計方式,也因此基于結構的藥物設計得到了眾多的關注與青睞。
自從蛋白質晶體結構被成功解析以來,人們開始不斷構建蛋白質的三維結構信息。隨著結構生物信息學的飛速發展,SBDD方法也取得了巨大進展。SBDD可用于任何能夠測定結構的藥靶蛋白質,但必須分離得到足夠數量和純度的藥靶蛋白質,以便進行結晶,并用X線衍射法測定結構,將蛋白質的三維結構信息與計算方法相結合,使我們可以在原子水平上分析配體與受體的相互作用模式。而且基于蛋白質的結構信息,計算機能夠更快地篩選出合適的候選藥物,根據以前的經驗加以考慮,并得到一系列漸進的導向設計物,再經實驗證實這些化合物的預期性質。SBDD不僅創新性地推動了藥物設計過程,更重要的是這樣設計出的藥物更加安全有效,比如最近的黃連素多靶點藥物的發現[11],而且目前已經篩選獲得30多種臨床候選藥物,其中3種已經被FDA批準[12]。
但是SBDD也面臨著許多技術上的問題。其一就是公共數據庫中蛋白質結構信息的準確性,這是保證SBDD結果準確的首要條件。盡管在結構研究中,研究者擁有高端的晶體學硬件、數據處理和結構優化軟件,仍然可能出現誤報和不一致的數據[12-13]。 其二是SBDD方法依賴于蛋白質結構,而解析蛋白質結構的方法是主要通過X射線晶體學、NMR光譜學(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NMR)、核磁共振及冷凍電鏡。這些實驗受成本與時間的限制,并且有一定的實驗難度,只有蛋白質可以結晶時,X射線晶體法才可以分析蛋白質結構。然而,大部分蛋白是難以結晶的,占目前批準藥物的60%[14]。核磁共振也只適用于小分子蛋白[15]。因此,SBDD面臨著重重挑戰。
3 基于片段的藥物設計
FBDD正逐漸成為一種熱門的藥物設計新方法,主要是利用檢測與靶點結合的小分子片段來進行藥物的篩選,最早于1981年被 Jencks[16]所提出。FB?DD將藥物視為由兩種及以上的片段組成,通過篩選得出針對靶點并能與靶點弱結合的低分子量小分子化合物一般結合為mM級,再確定片段與藥靶結合的結構信息,考察結合區域與如何相互作用,最后根據片段與藥靶相互作用的結構信息來指導對片段進行優化或衍生,或將不同片段連接加工成較大的配體。方法設計出的配體對于靶點擁有更高的親和性、結合率以及更好的優化能力[17]。近年來,FBDD發展迅速并逐漸被人們接受。FBDD通過分析靶點的空間特點,所設計藥物的活性和選擇性也更高[18]。近年來,很多FBDD藥物已經開始進行臨床實驗,甚至已經 上 市, 如 GKAs[19]、 HJC0123[20]、 HJC0416[21]、STAT3 小 分 子 抑 制 劑[22]、 Zelboraf(vemurafenib,PLX4032)[23]等。
FBDD在藥物設計上也存在著很多問題。首先是FBDD篩選出的藥物多數是小片段,即使是最佳互補的片段,其與靶蛋白的相互作用面積也比較小,親和力也比較低。其次,通過連接或增長片段來設計藥物十分復雜,依賴于藥物化學方法的進步。雖然FB?DD對藥物的設計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通過FBDD方法設計的藥物還需要不斷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