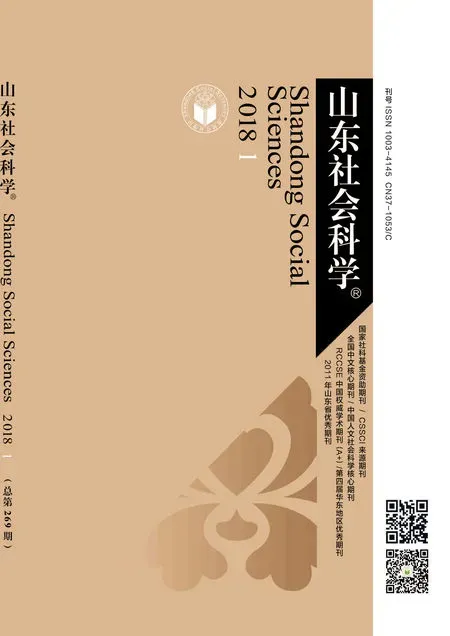論國際援助功能的變化和全球發展
王 微 周 弘
(浙江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58;中國社會科學院 歐洲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一、導言:國際援助與全球發展
作為一項國際事業,國際援助的發展已經有半個多世紀了。它采取財政援助、技術援助、促貿援助和債務減免等方式來緩解全球貧困,幫助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經濟、應對全球問題和挑戰。由于在新世紀中各國的社會發展基礎和政治經濟環境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國際援助這一社會事業的發展也會面臨著新的條件。這些條件包括發展中國家的成長和新興援助國的興起對舊有的國際援助秩序形成了沖擊,援助生態從兩級化向多極化發展,以及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民族國家治理的難度在增加。此外,當代通訊和大數據技術的發展也為實現全球發展目標提供了新的技術條件,但同時它也會形成了新的社會風險。
因此,在這些新的條件下討論全球發展援助事務時,我們要在國家層面和全球層面上同時考慮相關的問題,在國際援助中把基于民族國家利益的需要與全球發展目標相契合。在事實上,在新世紀以來,國際援助的驅動力已從冷戰時期的跨國競爭到實現千年發展目標(MDGs)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SDGs),國際援助的機制也從以往OECD/DAC國家的官方援助占絕對主導地位轉變到援助私有化趨勢不斷增強。各種國際組織、多國公共基金、新興經濟體的多元發展的態勢引起了國際援助功能的因應改變,使國際援助從一種單純的發展手段發展成為全球治理新機制。討論這些變化對于我們認識國際援助的實然和應然,理解全球發展和我們所處的時代具有重要意義,也有助于推進全球治理和全球發展政策的研究。
在展開對于研究議題的討論前,我們首先需要對于國際援助的幾個基本概念進行界定。從概念上說,國際發展援助(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IDA)是一國或國家集團以及國際組織向他國或國家集團無償或優惠的提供貨物或資金,以便幫助這些國家應對其所面臨的困境和挑戰的手段*黃梅波、王璐、李菲瑜:《當前國際援助體系的特點及發展趨勢》,《國際經濟合作》2007年第4期。。這些援助包括財政援助、技術援助、糧食援助和債務減免等多種形式*劉貞曄: 《國際多邊組織與非政府組織:合法性的缺陷與補充》,《教學與研究》2007年第8期。,采取官方或非官方的手段。官方國際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指發達國家及其所屬機構(或國際組織)以資金、物資、設備、技術等各種形式對于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援助*李小云等: 《國際發展援助概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年版,第2頁。;而非官方援助則指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s)基于人道主義的義務所進行的發展援助。
在對于國際援助項目執行主體的界定中,我們需要辨析官方和非官方的援助主體的不同屬性,因為它們在援助活動中具有不同的行為特點和價值導向。在以往的(和現有的)國際援助體系中,官方援助通常居于主導地位。許多國際援助是通過各國政府采取雙邊援助項目的形式運作的。這些雙邊援助項目主要來自發展援助委員會(DAC,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的23個OECD國家,據2015年4月8日發表的經合組織報告,2014年DAC成員國提供了高達1352億美元的官方發展援助*經合組織網站,2015年4月8日。。這些由各國政府提供的官方發展援助不可避免的會具有一定的功利目的(如提升國家影響力、輸出意識形態、獲取戰略資源等)。與此相比較,另一類官方援助主體——國際組織提供的援助則具有較強的人道主義或為價值導向所驅動的含義。譬如聯合國系統大多采取無償贈款援助的形式提供食品和衛生醫療救助服務,而世界銀行集團和區域性開發銀行則常常采取低息貸款的形式提供援助。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非政府組織和非官方組織的作用。一些具有特殊援助目的的專項基金和各種全球性基金在扶貧、環保、衛生、教育、技術合作、人道主義援助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這些國際非政府組織包括英國樂施會、蓋茨基金會、全球疫苗免疫聯盟和全球環境基金等。到20世紀末,國際NGO已接近4.5萬家*高飏、付濤: 《發展援助, NGO和公民社會: 矛盾中的探尋》,《中國發展簡報》2011年11月30日。。2008年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無償援助資金高達236.55億美元,并以其專業性和深入基層使援助項目取得顯著成效*楊文兵、王曉雙: 《全球治理語境下非政府組織角色定位新探》,《學術論壇》2008年第4期。。隨著對外援助的私有化趨勢不斷增強,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非政府部門參與國際援助活動。這些國際NGO常常以自己的專業知識影響著外援的分配和走向,在對外援助中主要扮演項目執行者、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同時近年來也在日益強化其政策倡導、項目決策和評估監督等方面的作用。
在本世紀頭十年,國際發展援助的數額保持在相對穩定的狀態。根據相關資料,從凈官方發展援助額來看,主要受援地區是非洲(特別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其次是亞洲,而最少的是美洲、歐洲和大洋洲*王妍蕾、劉晴:《OECD十年發展援助情況演變》,《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在資金流向上,由于發展伴隨的地區差異持續增大,國際援助的減貧功能被進一步強化,因而援助資金流向中高收入國家(如東歐)的比例相應下降,流向其他低收入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的比例持續增長*http://www.oecd.org/dac/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development-finance-data/aid-at-a-glance,登錄時間:2017年4月9日14:58.。當然,在分析國際援助狀況表現出來的這些變化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在這些援助項目的活動之后援助的機制和驅動力的變化,這些方面的變化引起了國際援助功能的因應改變。
本文將探索在這些變化中援助國與受援國在國際援助事務方面的利益和實踐經驗,揭示在此過程中國際發展援助功能的演變與拓展,展開對提升國際援助功能的政策討論,說明國際發展框架如何在現在框架基礎上作出調整和改變,從而檢驗國際援助作為全球發展工具所具有的成效。我們將首先介紹國際援助從國家利益功能到社會發展和人道主義功能的演變與拓展,剖析國際援助功能變化的原因,然后就提升國際援助功能的政策展開討論,論證國際發展框架如何在現在框架基礎上作出調整和改變,以發揮新時期的國際援助“超越援助”的功能。
二、國際援助的國家利益功能
對國際援助所具有的作用和各方面的功能,人們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闡釋。國家利益理論強調對外援助的本質是政治性的,即援助國為了保護其國家自身利益而對他國提供援助*鄧紅英: 《國外對外援助理論研究述評》,《國外社會科學》2009年第9期。。例如漢斯·摩根索( Hans Morgenthau)指出對外援助本質上都是政治性的,是為了促進和維護包括塑造民族形象、提高國家聲望、宣揚社會價值以及傳播生活方式等國家利益*Hans Morgenthau, 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6,No.2,1962, p.301.;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 Waltz)強調對外援助是為了爭取盟友,與行賄沒有本質差異*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asley Publisher Corporation, 1979, p.200.。他們認為對外援助是外交的組成部分,而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在此意義上,國際援助行動可以被看成是國家內部因素的外化,是援助國內部的社會經濟政治變化的反映。因而各國所特定的歷史經驗、政治文化背景和社會發展模式都會影響他們的外援行動。
也有些學者強調國際援助的意識形態功能。斯多克提出“條件論”來解釋跨國援助的這種功能*Olav Stokke, Aid and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EADI Book Series 16,1995, p.12.。斯多克強調,盡管我們在分析中不能排除援助國的“利他主義”和“人道主義”動機,但援助國進行援助的直接目的大都是通過援助促使受援國進行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改革,并以這種方式輸出本國價值觀和治理理念*Olav Stokke, Western Middle Powers and Global Poverty, The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Uppsala, 1989.。在援助國輸出“硬資源”進行援助的同時,受援國“軟力量”會受到援助國的影響,這種影響在受援國觀念、方法和制度等環境建設方面都會發生作用。因此,他認為國際援助的動機大致可分為三類,即人道主義的動機、現實的國際主義(為本國現實利益)和激進的國際主義(輸出意識形態)*Olav Stokke. Aid and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 Routledge, May 19th 2014.。
在20世紀發展起來的國際援助活動中,我們看到早期的國際援助主要是基于現實利益的各國官方援助。發達國家通過國際援助來爭取盟友、培育各自的勢力范圍。例如1945年英國議會通過的《殖民地發展與福利法案》、1946年法國設立的“法蘭西戰后殖民地開發計劃”項目,都是殖民地宗主國在這些殖民地獨立后力圖通過發展援助來展示其道義上的責任,并繼續維持其對于這些地區的影響力。這些發展援助具有很強的功利導向,主要服務于主權國家的安全戰略,從《馬歇爾計劃》到《東南歐穩定公約》都體現了以國家安全為出發點而提供的援助*周弘: 《對外援助與現代國際關系》,《歐洲》2002年第6期。。即使在本世紀,我們也常常看到這種基于國家利益所提供的援助項目,特別是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9·11事件都刺激了世紀之交國際援助項目的增長。
這種基于現實的國家利益的考量與發展援助意識形態的考慮相結合,催生了國際援助的社會交換論。社會交換論從援助國與受援國雙方互動關系出發闡釋對外援助,例如鮑德溫(David .A. Baldwin)認為,國際政治中所有的關系都是圍繞國家權力進行的交換關系*David .A.Baldwin, “Power and Social Exchange”, p.1229.,拉爾遜(DeborahW. Larson)也強調國際關系是一系列資源和利益的交換活動*DeborahW. Larson, “Exchange and 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Vol.3, No.2, Feb.1998, p.134.。例如在東歐,西方發達國家對于轉型國家提供的國際援助常常就伴隨著市場化,民主化和私有化等社會政治要求。這充分體現了斯多克的分析所指出的援助國通過內部整合來達成對于受援國的整體戰略并改變與受援國間的關系*Olav Stokke. Aid and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Routledge, May 19th 2014.。
當然,這種國際援助所導致的效應會在援助國和受援國之間造成矛盾和沖突,使如何接受國際援助并保持國家主權的獨立性成為爭論中的焦點問題。援助國對于受援國附加援助的條件(包括進行市場化改革和多黨制政體)影響當地的經濟發展和政治體系的建設。不過一些學者也指出,這些干預對于受援國的發展來說,既是進行現代化和社會改造的驅動力,也在社會穩定和民族自立等多方面承受著壓力和挑戰。這使許多受援國強調國際援助的“國家所有權”原則的確立。人們批評一些國際援助行動所附帶的政治經濟條件是基于援助國自身的利益,是援助國對于受援國的內政的干預。這種“激進的國際主義(通過外援輸出意識形態)”促使許多研究者強調國際援助應削弱意識形態的功能而增進社會發展和人道主義的功能,加強援助協調和受援方的項目運作自主性。
三、國際援助的社會發展和人道主義功能
隨著國際援助的發展,一些學者也強調國際發展援助是為了社會發展和人道主義的目的和宗旨而進行的,利益超越國家界限。例如當世界各地發生人道主義災難后,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以及民間團體都有責任進行國際援助。這種國際援助的人道主義功能在九十年代以來被不斷的強化,并逐漸替代國際政治利益而成為國際援助的價值基礎和合法性基礎。特別是在進入21世紀之后,聯合國倡導的“千年目標”進一步強化了國際發展援助的基礎,促使國際援助的主體增多、規模增大、領域擴展、形式更加多樣化。這導致國際援助項目從強調“援助”走向“發展”的目標,從關注援助“過程”走向更注重援助“結果”,從而催生了國際援助合法性基礎的演化。
國際援助的社會和人道主義功能的強化,造成國際援助的重點領域發生變化。在以下表格中,表1反映了主要援助國家(或組織)的援助聚焦在社會基礎設施和服務領域,使受援國的社會福利和生活條件的改善成為國際援助的關注重點。表2則反映了DAC國家在不同部門的官方發展援助占全部雙邊援助的比例的變化。根據這個表格,從1984年2013年近三十年中,經濟基礎設施、工農業和其他產業、物資和項目援助的比例都有較大幅度的下降,而在社會公共設施和人道主義援助方面的投入在不斷增加。
導致這種變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半個多世紀以來,國際援助采取了多種方式促進受援國的經濟成長,例如注入資本、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等,但援助成效并不明顯。以前集中于經濟部門的援助并沒有帶來預期的發展效果,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發展不平衡日益凸顯*See Wolfgang Fengler and Homi Kharads.,Delivering Aid Differently:Lessons from the Field,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Washington.DC,2010,p.1.。這是因為這些途徑對于經濟增長的積極成效也要通過社會改造和社會轉型的努力才能夠達成。但國際援助在有效帶動當地內生力量增長方面一直收效甚微,導致其在改善人們生活和社會進步方面的成效十分有限。援助實踐經驗使發達國家意識到,國際援助要取得長久的發展效應,主要在于這些援助項目的運行需要能夠強化當地社會所具有的發展功能,改善當地人民的生活質量并提高社會質量。
另一方面,正如表3所示,從2010年至2015年,DAC國家的官方發展援助中的人道主義援助穩步增長,援助總額從2010年的100.33億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132.62億美元,已經成為繼社會和經濟基礎設施之后的第三大援助領域*Data extracted on 16 Apr 2017 01:32 UTC (GMT) from OECD.Stat.。當前包括恐怖襲擊、自然災害、地區沖突和統治暴政等常常會引發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人道主義救援與減貧、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等議題相互交織,就成為國際發展援助的重要領域。這種情況表明,在當前人道主義危機頻發、全球減貧壓力持續增大、環境氣候問題日益嚴重的背景下,人道主義救援和長期發展援助之間需要更大的一致性和互補性,需要加強人道主義需求與長期發展援助優先舉措如扶貧、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等之間的平衡。

表1 主要援助國家或組織援助重點領域(2010)
資料來源:劉方平:《中國援外的歷史進程與現時拓展》,《暨南學報》(哲社版)2016年第2期。

表2 DAC國家在不同部門的官方發展援助占全部雙邊援助的比例(%)
資料來源:黃梅波、王璐、李菲瑜:《當前國際援助體系的特點及發展趨勢》,《國際經濟合作》2007年第4期。

表3 DAC國家官方發展援助中的人道主義援助概況(2010—2015) 貨幣:美元;單位:百萬
資料來源:Data extracted on 16 Apr 2017 01:32 UTC (GMT) from OECD.Stat
四、國際援助功能變化的原因分析
基于國際援助所具有的社會基礎和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我們看到當前全球發展呈現出復雜的狀況。一方面,以經濟成長為中心的發展導向已經走向多元發展的狀態,使環境/可持續發展、社會質量和全人類福祉這些理念逐漸地被納入發展維度中;另一方面,巨大的減貧壓力、弱勢群體的社會融入,國際移民和歐洲難民問題,新興工業化國家嚴重的氣候和環境問題等,構成各國發展可持續性的挑戰。社會控制和民族國家的治理更加艱巨,社會風險和發展的代價在不斷增大。發展援助可以通過項目運作的途徑對這些挑戰進行回應,并且把跨國援助的功能從傳統的服務國家安全、輸出意識形態、建立地區霸權轉向促進社會發展、增進受援國福利、人道主義救援、促進貿易和投資、環境保護和氣候治理等變化拓展。這些變化的原因是國際援助的價值基礎和行動邏輯的改變。從目前的國際援助變化情況看,我們可以把這些變化歸納如下。
一是國際援助的政治功能的弱化。隨著冷戰的結束,以往基于兩大陣營抗爭的政治目的而強化的國際援助在下降。在柏林墻倒塌之后,曾經有大量的援助資金從西方國家涌入東歐,但很快西方國家看到這些援助資金并沒有通過民主化和私有化的改革給他們帶來所期待的利益。同時,其通過援助條件促進東歐受援國實施政治經濟改革并得到紅利的意圖也未真正實現。因此在1990年代后期,由于國際援助意識形態功能的弱化,國際發展援助總額在短期內急劇下降。到1997年,全球官方發展援助(ODA)的數額降到了約600億美元,OECD23個援助國官方援助占其國民總收入的比重也從1990年的0.33%下降到了2000年的0.22%*賀光輝: 《第三世界發展理論與援助功能的演進(1950-2000)》,《世界經濟研究》2003年第1期。。與此相反,一些學者發現,國際援助在改善社會福利水平方面起到更為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在公共衛生、教育、農業基礎設施方面,國際援助對福利指數的影響很大,這種效應在福利水平較低的國家表現得最為顯著*ensen, T.M.(2008), “(How)does aid work? literaturere-view of aid effectiveness and welfare studies”, DIISWorking Paper, No.2008/29.。因此,作為政治競爭手段的國際援助正日益失去其價值基礎,而作為福利增進提供的援助則具有廣泛而持久的發展動力。
二是逐漸形成新的國際援助理念。隨著國際援助的基礎正由國家利益轉向促進全球福祉,社會進步逐步成為被廣泛認可的國際援助的普世價值。隨著千年計劃綱領的形成,國際援助的目標已經超越了民族國家的局限,與人類發展目標相結合,人道主義功能逐步強化。人類安全理論和人類發展理論的成長以及埃斯蒂斯(Richared J Esters)的社會進步指數(ISP)和開發計劃署提出的人類發展指數(HDI)的影響,都強化了社會進步的意識。《千年計劃》強化了可持續發展理念,《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還關注發展自主性、參與性、包容與共享等,議程提出了建設更具包容性的全球伙伴關系的動議,不僅指援助國與受援國之間,也指DAC援助國和新興援助國之間。參與各方在援助領域可以發揮各自的優勢和長處,形成國別、地區、行業、援助方式上的良好分工和布局,共同提高國際發展援助的整體效率和效果*王國慶:《國際官方發展援助分配及協調趨勢》,《國際經濟合作》2012年第8期。。在此,三方合作是一種把二者聯系起來并發揮各自優勢的有效機制。2014年發布的《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戰略規劃(2014—2017年)》正式將三方合作形式作為南南合作的核心模式。在未來十五年中,國際發展援助將要在議程指導下通過項目運作大力推進這些目標的實現,使跨國援助成為實現人類發展的政策工具。
三是對于受援國自主性的肯定。新世紀以來,國際援助的受援國自主性受到了廣泛關注。2005年《巴黎宣言》正式提出了受援國的“國家所有權”原則;2008年的《阿克拉行動議程》再次肯定“國家所有權是關鍵”,強調新時期的援助雙方應是更具包容性的伙伴關系;2011年《釜山宣言》提出要加強和擴大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提出了“全球伙伴關系”的概念,確立了評估發展有效性的框架*曹黎:《從千年發展目標到釜山合作宣言》,《經濟研究導刊》2013年第9期。;2015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要求將來自國內和國際層次上的公共部門和私有部門資金整合進國際發展框架*聯合國文件:《秘書長的說明:可持續發展籌資和 2015年后發展議程方面的一致性、協調與合作》,E/2015/52,2015年3月25日,第6頁。,強調國際援助社會應該努力支持各國政府提高國內資源利用效率,提高國際合作和集體行動的能力。這些協議都匯聚成一種共識:強調受援國自主性,要求援助國避免過度干涉受援國的國內政策,要充分保護受援國對于其發展過程的領導權和決定權,使受援國有充分的政策空間來發展適合國情的援助機制并滿足自身需求。
四是在不斷加深的全球化進程中增強國際組織的作用。目前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糧食計劃劃署等國際組織已成為國際援助的中堅力量。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的成員國(DAC)也通過三方合作方式在援助國與受援助國之間發揮協調作用。同時,各種非官方的國際援助組織也在積極的發揮作用。此外,不同于傳統的雙邊和多邊援助,新世紀以來出現了一種多國公共基金的援助方式,如美國、英國、澳大利亞、荷蘭、丹麥等九個國家共同出資成立的“多方援助信托基金”(Livelihoods and Food Security Trust Fund,LIFT),以及英國國際發展署、澳大利亞國際發展署、歐盟等成立的“三種疾病基金”(Three Diseases Fund,3DF),通過國際援助機構之間的合作,減少了援助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和資源浪費,提高援助的一致性和協調性*楊義鳳、鄧國勝: 《國際NGO參與對外援助的變遷及對中國的啟示》,《中國行政管理》2014年第3期。。
第五,我們也要看到東亞地區和新興工業化地區的影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后,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迅速崛起,成為國際發展援助的突出力量。中國、韓國、巴西、印度等傳統的受援國開始成為援助國,其援助額在2009年為170億美元,其在全部發展合作中的份額從2006年的6.7%增至2011年的10%,增加了近50%*黃超: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框架下官方發展援助的變革》,《國際展望》2016第3期。。與傳統DAC國家援助通常附加各種政治條件,重視受援國的政治進步、民主進程和社會發展不同,這些新興援助國(NODDs)提供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尊重伙伴國自主權,重視經濟增長、技術進步和減貧,援助促進經濟效應明顯。傳統DAC國家面臨援助領導權挑戰,新興援助國(NODDs)不僅以南南合作的方式為國際發展援助提供了新的源泉,也促使國際援助的理念發生了變化。如中國在2005年世界銀行年會上就提出“重視國家能力建設”(building state capacity)的主張,并被寫進了會議公報。這些發展都對世界外援的走向帶來重要影響*周弘、張浚、張敏: 《外援與發展:以中國的受援經驗為例》,《歐洲研究》2007年第4期。,使2015后議程增添了經濟發展和能力建設的目標。
五、提升國際援助功能的政策討論
在全球化的今天,民族國家的發展問題也是全體人類社會的問題。國際援助項目可以做為推進全球發展的手段和催化劑,同時也能夠幫助受援國提升國家治理能力、保障人權和支持民族事業的發展。為了實現這些功能,我們需要強化國際援助項目的社會發展和人道主義功用,弱化其政治利益和提升經濟效益手段的功用。因此,我們需要辯證看待國際援助項目的多重目標定位,合理確定援助的中心目標。我們不能忽視國家安全,國際貿易,戰略資源、地區影響等國家利益目標,也要關注減少貧困、民生增進,環境改造,基礎設施建設等社會發展目標。在這些目標中,我們要以反貧困,緩解社會不平等和社會排斥、增進包容性作為援助的中心目標,全面評估國際援助對于社會發展的積極效應,通過各種政策途徑(進行社會投資,重視扶貧開發,培養專業隊伍,建立監測評價體系、創新援助機制等等)來促進全球集體行動,提高生活質量并增加社會質量。在此,發展和增能賦權是各種國際援助項目的關鍵理念。按照這些理念,我們的國際援助要關注邊緣群體和社會排斥現象,推進技術成長和增進國民教育,兼顧可持續發展和環境改善,進而推進全球發展。
同時,我們也要強化對援助項目的監管。強化監管,防止項目失控和貪腐現象,是使項目能夠落實到幫助目標群體的基本保障。一些評估專家批評說,國際援助項目的運作可能創造更多的權力尋租和腐敗的機會*Dalgaard, Hansen& Tarp(2004), “ On the emprics of foreign aid and growth”, Economic Journal114:F191-216.;Doucouliagos&Paldam(2008), “Aid effectiveness on growth:Ametastud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4:1-24.;也有人強調,在缺乏有效監管的條件下,國際援助項目的運作常常面臨政府問責的缺失、導致援助依賴并破壞稅收刺激等,這使援助項目導致更多的是損害而不是獲益*Dambisa Moyo,Dead Aid: Why Aid is Nos e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 Better Way for Afri-ca,Farrar,Straus and Giroux,NewYork,2009,p.48.。所以,如果缺乏制約和監督,貪腐現象將使人們對于項目運作的公共性和合法性產生質疑。為此,有關各國需要建立暢通有效的信息通報機制,增加援助項目的透明度;要進一步完善項目管理條例并有效的執行,加強項目評估,加強問責制度建設,形成國家水平上的獨立監控機構。UNDP、DAC、EU、WB等國際援助主要組織要通過同行評估及相關會議機制加強對成員國的督促等*毛小菁:《DAC發展援助改革最新動向及對我國影響》,商務部網站,2015年11月4日。。不過,由于缺乏政治互信或與當地的制度文化相沖突(或與當地的利益集團發生沖突),這種監管的要求也常常會被認為是外來的干預,是援助方力圖對于項目運作附加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條款,從而導致援助雙方的矛盾和沖突。因此,如何淡化項目運作監管過程的政治色彩,強化項目管理的透明性和專業性,改善對項目的管理成效,就成為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
此外,評估各國社會制度的異同對于援助項目運作造成的影響。完善項目評估,設立科學的評估指標體系是進行有效監管的必要條件。在進行國際援助項目評估中,不僅要考察經濟效益指標和社會效益指標,也要考察生態效益指標、生活福利指標以構建全方位的發展評估體系。這一指標體系要能夠反映出發展援助是否有效的達成了目的,是否公平和透明,是否有公眾參與。比如美國的對外援助評估就包括了績效監測、績效評估和影響評估等*王新影: 《美國對外援助評估機制及啟示研究》,《亞非縱橫》2014年第6期。。基于這些原則,援助機構必須超越項目評估本身,更廣泛地考慮到受援國的總體發展模式,發散的、主題的、國家層面的評估都應該被越來越多地用到*Taylor & Francis. Foreign aid and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 Issues of effectiveness and consistency.Democratization,1997,4(3):69-108.,這些指標既要包括生活水平、健康以及教育和人的發展等生活質量方面的指標,也要包括社會保障、社會包容、社會賦權、社會凝聚等社會質量方面的指標。要測量國際發展援助項目的成效,我們不僅要確立項目運作的多邊機構之間建立起可持續運作的機制,更要注重這些計劃對于受援國社區發展和全球倡導行動兩方面的影響。從社會發展、環境發展、人的發展的角度出發測量國際發展援助項目的社會成效、環境成效和人文成效。同時,評估結果必須做好信息傳播,以便所有想獲得評估信息的潛在用戶都能根據各自的需要獲得信息。決策人員必須能獲得一個綜合性的結果而不僅僅是詳細的項目評估結果本身*R.Rameezdeen & YuzoAkatsuka ,A Policy Oriented Approach for Evaluating overall Performance of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Journal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1999)。強化這些工作對于提升發展項目的有效性至關重要。
另外,民眾的參與。在此,僅僅關注援助項目的評估指標建設和項目監管技術是遠遠不夠的。國際援助計劃要真正有效就要發動群眾參與,尋求各類社會主體的合作機制,使國際援助項目能夠帶來受援國長久的社會進步。受援國的市民社會組織需要積極參與到發展援助中并與援助國進行多維度對話,國際組織也要通過共同推進項目、舉辦援助論壇、開辦學習培訓班等方式與當地的合作伙伴有效合作和共同行動*高飏: 《發展援助,NGO和公民社會: 矛盾中的探尋》,《中國發展簡報》(輯刊),2011年11月。,這樣才能推進受援國的社會改造和社會進步進程,更好地支持受援國本土內生力量的發展。新時期需要強化援助方和受援方的政治信任和文化寬容,不發達國家要消除貧窮就必須進行社會體制的改革,學習先進的的發展理念和管理方法,培養公眾的發展意識,增進社會包容和賦權,否則所有的援助都會無濟于事。
再者,社會體系的改革。 就工具性意義而言,一些DAC國家在提供經濟援助的過程中,往往要求受援國進行民主改革、實行多黨制,發展市場經濟,企業私有化等,把國際援助作為影響受援國政治和經濟改革的工具。這些援助條件要么不適應受援國的實際情況,要么遭遇受援國的各種抵制,影響援助功能的正常發揮,也極大的影響援助效率和效果。當然,國際援助的目標旨在促進受援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和國民福利增進,而這一目標是否能夠達成與援助計劃的設立與當地國情的適應程度相關。這就要求項目設立時要對受援國社會背景進行深入的制度分析,使國際援助項目能夠適合當地的國情和民眾的需要。把當地的文化和制度的特點與援助項目所帶有的人道主義價值進行融合,減少援助實施過程中因受援國當地的政治宗教制度和社會習俗差異而產生的排斥和抵制*蔣華杰: 《中國援非醫療隊歷史的再考察(1963—1983)——兼議國際援助的效果與可持續性問題》,《外交評論》2015年第4期。。同時,發達國家必須遵守受援國的勞動分工制度,認識到發展的實質是發展中國家加強發展能力,達到自己的治理目的,不是通過削弱所有權的方式實施援助。如果單向度的基于西方援助國的價值觀來提出要求,其項目運作所具有的許多目標可能并不現實,從而無疑會影響援助的效益。
最后,強化國際援助的發展導向。國際援助項目不僅僅要關注自主權問題,更要關注全球發展問題。在國際援助項目的設計中,要兼顧受援國項目運作的自主性和全球發展的總體需要。要把國際援助計劃納入當地社會發展的整體規劃中,充分發揮在地方層面和全球層面上各類發展主體的能動性。要遵循聯合國發展委員會于1991年制定的《發展援助評估原則》要求,即發展援助評估要重視在整個項目執行的過程中各方所起的作用、責任和地位,并確保項目評估的公平性,透明性,民眾的可獲得性,以及項目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Stokke O. Evaluating development assistance : policies and performance. Frank Cass, 1991.。基于這些原則,我們需要從社會發展的角度出發來測量國際發展援助項目的成效,確立項目運作的多邊機構之間建立起可持續運作的機制,提升項目的可持續性并有效的回應實踐的需要。為此,我們需要處理好援助項目的人道主義和社會發展的功能與項目所含有的政治經濟利益方面功能之間的關系,處理好項目所內含的普世價值與項目執行雙方所具有的特定的歷史社會文化追求的關系,倡導援助的有效性、協調性、發展性、新型伙伴關系,共同推進人類社會進步和實現社會發展議程。
六、小結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國際援助已經成為全球治理的一種基本制度。它在推進全球發展和緩解地區沖突和緊張方面獲得了很大的成果。從服務于冷戰的援助競爭到冷戰之后促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再到新世紀之后追求全球福祉的“發展有效性”,國際援助正從國家間競爭工具轉為全球治理的新機制。特別是隨著聯合國千年計劃的實施、《巴黎宣言》的簽署和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的設立,人們對國際援助的功能和有效性標準的反思也在不斷深入。隨著規范化和制度化進程的推進,國際援助工作環境得到優化,國際減貧、包容性增長成為援助項目的核心目標。
當然,在目前國際援助項目的運作中也存在著種種矛盾和問題。受到援助國政府的經濟發展情況以及對外發展戰略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援助金額的提供具有很強的不穩定性。援助資金的巨大缺口,給援助依賴程度較高的國家帶來極具破壞性的影響。因此2002年蒙特雷國際發展籌資會議提出要尋找創新籌資渠道,之后出現了機票統一稅、綠色債券、疫苗債券、三角貸款、貨幣交易稅和碳交易稅等一系列新籌資機制*黃超:《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框架下官方發展援助的變革》,《國際展望》2016年第3期。。這些新型融資渠道,開辟了新的資金來源,可以對發展援助起到支持補充作用。對于不發達地區,尤其是對于重債窮國(如安哥拉、中非、科特迪瓦、剛果、馬拉維、尼日利亞等國),債務減免是消除這些國家沉重債務負擔的重要手段。在新時期,啟動重債窮國計劃和多邊減債動議以提升籌資機制的可持續性;協調這些新型融資與ODA的一致性等,都是國際援助新框架的重大議題。
在操作層面上,國際援助項目的運作可以作為平臺促使援助國和受援國之間的經濟互動、知識交流和技術合作,從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能力等多方面推進區域發展。在此,政治互信和文化寬容是影響項目運行成效的價值基礎。這種政治互信可以減緩在項目管理中援助國之間的摩擦和沖突,也避免形成一種把國際援助項目僅僅看成是帝國主義控制不發達國家的工具的偏見,然而,在項目執行過程中,援助方會要求加強監管和評估以化解由腐敗和經費濫用帶來的管理風險,受援方則會要求具有更大的國家所有權和自主空間。要處理好這些矛盾,需要援助項目的各方在文化寬容的基礎上誠信合作。同時,援助項目也要重視地方治理和社區建設,把國際援助作為地區發展的重要手段來促進當地社會的進步。
在國際援助領域,各種發展主體(包括非傳統援助國、全球基金、私營部門、民間社會組織)貢獻他們的寶貴經驗和資源,同時在管理和協調方面也形成了一定的挑戰。半個多世紀的援助實踐證明,發展項目的成效主要取決于社會建設的成果。國際援助從兩極化態勢向多極化態勢的改變,將使發展中國家有更多的選擇和自主性,通過國際援助項目的執行來達成社會改革成效的可能性大大增強,以項目執行為契機增進社會的均衡和協調發展日益成為現實。同時,傳統DAC國家如何面對援助領導權受到的沖擊、新興援助國如何克服西方國家“權力邏輯”制造的障礙,國際援助新框架開辟什么渠道提供什么平臺讓新興國家適當而有效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如何面對援助一致性協調性難度加大的現實,都是新時期的國際援助框架需要考慮的問題。因此,強化社會援助機制的建設、加強援助協調和構建援助治理新秩序,是確保援助效果長期持續性的關鍵。
最后,實施“廣泛參與”的原則。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倡導國際援助體系的改革,要求擴大國際援助計劃的公眾參與基礎。然而,過去許多援助項目的運作是通過“自上而下”的路徑執行的,缺乏“自下而上”的通道,這種狀況常使項目執行產生“精英捕獲”而很少能夠惠及窮人。特別是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社會分化和社會不平等現象嚴重,大眾對于全球發展過程的參與往往會遭遇體制性障礙。各種國際援助項目可以在降低生活風險(如疾病、衰老、自然災害等)、強化社會保護和緩解社會不平等狀況方面起到一些作用,但如果缺乏廣泛的民眾參與,這些項目的運作在社會改造方面將難以取得實質性的效果。只有推行援助體制的改革,使國際援助項目能夠影響更為廣泛的群體,才能使這些項目的運作在引導社會變化方面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新時期,發展中國家需要深化地方政府,公民社會組織和議會各方的能力建設,確保發展中它們的所有權以及需求,因為未來更多的援助將通過受援國的體制和機構來開展,因而受援國完善的政治、經濟體制以及良好的政策和公共治理能力將受到更多重視,并可能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影響援助決策特別是援助分配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