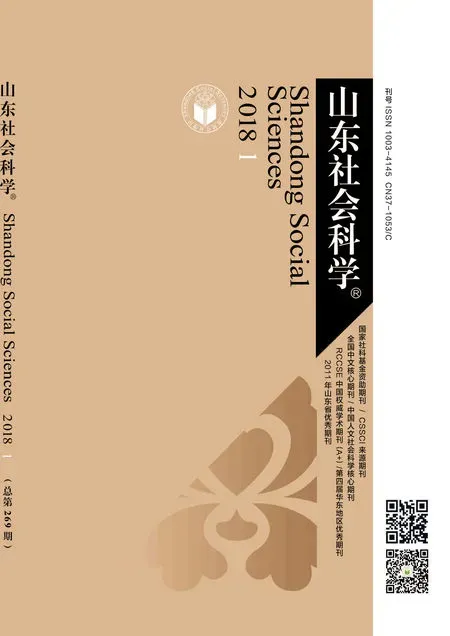全球發展與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國際經驗及其討論
艾 莎 李 驊 方 珂
(浙江大學 光華法學院,浙江 杭州 310008;浙江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08)
一、導言:在國際背景中談論非政府組織
由于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發展領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研究國際發展和全球治理必須考察各國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全球發展與地方發展是同一個進程的兩個方面*林卡:《國際經驗和中國社會福利體系的發展》,《浙江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非政府組織通過增進地方福利來推進全球發展進程,但在另一方面,不斷強化的全球化進程又不斷重塑非政府組織活動的社會環境和工作目標。正如Korten反映的,非政府組織在20世紀初主要從事救濟和福利工作,隨后轉向追求區域發展的目標,而目前其關注點放在可持續性發展的相關社會運動上。*Korten, D.C. (1990) Getting to the 21st Century: Voluntary Action and the Global Agenda. West Hartford, CT: Kumarian Press.Clark也有類似的看法,認為非政府組織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專注于發展援助和社會福利方面的功能,到90年代擴展為強化民眾參與和賦權方面的作用。到了21世紀,這些非政府組織力圖將它們的地方性行動與全球發展的活動結合起來。*Clarke G.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and politic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Political studies, 1998, 46(1): 36-52.
這一發展進程也反映在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成長中。據聯合國經濟社會委員會的統計,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數量從1948年的40個發展到2010年的3382個*馬方方等:《國際非政府組織與聯合國聯系機制研究》,中國社會組織網。,而國際協會聯盟的統計數據表明,2011年全球各類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數量達到5.77萬個*楊麗等:《國際型社會組織發展研究報告》,中國社會組織網。。這些組織與國內外機構合作,在亞洲、非洲、拉美等欠發達地區積極進行反貧困慈善、人權、健康、農業發展、社會福利和環境保護活動。一些國際非政府組織諸如照顧國際(CARE International)、大赦國際(Amnesty International)和樂施會(Oxfam International)也對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包括減貧、救助、增能以及婦女權益保護等方面的發展援助項目。因此,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對于非政府組織作用的研究不僅要放在國內社會環境中進行,也要在國際發展的語境下展開討論。
在已有的研究中,學者們對于亞洲、非洲和拉美國家中非政府組織的許多相關議題進行過研究和討論,強調非政府組織對于全球發展所起的關鍵作用。*林卡:《收入差距和社會公正:拉美國家社會保障體系的發展及其經驗》,《社會科學》2011年第10期。舉例來說,Collier強調非政府組織在國際事務活動中的價值與道德問題*Collier, P. (2007) The Bottom Billion: 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Shrestha、Farrington以及Mercer批評國際發展機構忽視非政府組織諸如尼泊爾和坦桑尼亞等發展中國家對于在當地發展中的貢獻。*Shrestha, N.K. and Farrington, J. 1993: NGOgovernment interaction in Nepal - overview. In Farrington, J. and Lewis, D.J., editor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state in Asia: rethinking roles in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189-99;Mercer, C. 1999: Reconceptualizing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Tanzania: are NGOs ‘making a difference’? Area 31.為此,我們要高度評價國際組織與當地非政府組織的積極配合對于形成和推進全球發展目標所做的努力。本研究將對相關研究進行回顧和討論,它涉及對于非政府組織的地位、作用及其面臨的問題的界定,也要對非政府組織所起作用進行討論。
二、非政府組織的界定和功能
要在全球背景中展開非政府組織作用的討論,就要對“非政府組織”這一概念進行界定。根據Sunkin等人的定義,非政府組織(簡稱NGO)可以指私人組織、公司、小業主和慈善團體,其性質可以是營利的或非營利的*Sunkin, M., Bridges, L. and Meszaros, G. (1993) Judicial Review in Perspective. London: The Public Law Project:108.。與這一界定不同,Najam則關注其所具有的社會職能,把非政府組織定義為包括社區組織、民眾組織以及社會組織在內的組織*Najam, A. (1996). NGO accountability: A conceptual framework.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14(4), 339-354.。此外,Vakil把非政府組織界定為自治的、私人的、非營利的組織,其宗旨是提高弱勢群體的生活質量。這些組織可以具有多種形式,包括未正式登記注冊的草根組織(GSOs)*Vakil, A. (1997) ‘Confronting the classification problem: toward a taxonomy of NGOs’. World Development 25, 12.、當地的非政府組織和國際非政府組織等。其中,國際非政府組織指由3個國家以上組成的組織或參與者開展自主活動的非營利性自治組織*Anheier, Helmut K., Mary Kaldor, and Marlies Glasius, eds. Global civil society 2005/6. Sage, 2005.,而國際非政府組織可以進一步劃分為北方非政府組織(NNGO)、南方非政府組織(SNGO)以及轉型國家中的非政府組織*Najam, A. (1996). NGO accountability: A conceptual framework.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14(4), 339-354.。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們對于非政府組織推進國際發展活動的作用主要從以下幾方面來闡發:首先是它們起到連接政府與市場、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的作用。非政府組織既不以追求利益或營利為目標,也無法履行政府的公共責任,但它承擔著廣泛的社會責任。這些組織具有非營利屬性、自愿性、自治性的特點,可以跨越政府(公共)部門與市場(私營)部門而處在社會(第三)部門中。這種特點使非政府組織可以起到培育社會關系、社會資本和社會信任的作用。正如Lewis說的,非政府組織可以調動社會資源為需要的人提供物品和服務,在衛生保健、小額信貸、農業推廣、緊急救濟和人權等多個領域開展廣泛的活動。*林卡:《收入差距和社會公正:拉美國家社會保障體系的發展及其經驗》,《社會科學》2011年第10期。Ulleberg也強調非政府組織可以通過強化教育幫助、福利服務、組織宣傳和改革的公共活動向福利需求群體提供服務*Ulleberg I. The role and impact of NGOs in capacity development. From replacing the state to reinvigorating education. Pari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 UNESCO, 2009.。
顯然,非政府組織的這些活動不是履行政府的公共責任,而是以社會的力量依托,為推進人道主義的理念而采取的行動,也為慈善事業的發展提供地方的驅動力。許多地方非政府組織通過與國際援助組織密切合作,為當地民眾進行糧食援助和其他各種社會服務,成為國際援助的地方承接者。正如Lewis提到的,在過去二十年中隨著政府支持和捐助者的增加,非政府組織“承接”了許多社會治理工作,并以招投標的方式運作了許多社會項目。*Lewis, D. (2007) The Management of Non-Government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2nd edn. London: Routledge.這些活動固然屬于當地的社區活動和民間活動,但當這些活動與全球發展的目標和國際組織相關聯后就成為全球發展的一部分。
再者,從全球發展的視角看,非政府組織也積極推行各種社會項目來強化公民的創新能力,通過賦權來增進他們社會參與的能力。對此,Lewis用公民行動主義的概念來指稱那些鼓勵公民參與的社會規范和做法,認為非政府組織是社會創新的實驗場,并為發展提供導向*Lewis D, Kanji 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09.;Davis則把非政府組織看作是“知識生產者”的俱樂部和協會以增加社區群體的參與*Davis, Gloria. A History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Network in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Social Development, Paper No.56, March 2004.;Frank也強調這些非政府組織是社會變化的催化劑,有助于推進社會變革采取改造思想的行動以促進變革*Frank D J, Longhofer W, Schofer E. World society, NGO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reform in A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2007, 48(4): 275-295.。為了說明這些作用,我們可以從發展中國家選取一些案例來展開討論以反映不同社會中NGO的作用。
三、非政府組織在推進國際發展中的案例
在發展研究中,學者們對于非政府組織在增進地方發展的作用上進行過許多案例研究,提供了各種經驗。這些經驗具有地方的特殊性,但也能夠從獨特的背景中展示NGO組織在這些不同社會中的影響。在此,我們可以舉一些來自于非洲和南亞的案例來體現。這些案例有的是在社區層面的,也有的是在區域、國家和全球層面的。
案例一:肯尼亞發展機構(KCDF)。KCDF組織成立于1997年,致力于改善家庭福利(特別是孤兒和單親家庭)以提高婦女和女童的地位和安全,促進預防性保健支持的創新。KCDF通過與當地民間社會組織進行合作,提出“減輕貧困,加強聲音,改善居住在內羅畢基貝拉和其他貧民窟的弱勢群體的健康”項目。例如KCDF城市的生計計劃通過資產建設以可持續的方式提升自己,也與政府、非營利組織、商業部門和個人等進行長期合作以實現社會公正,KCDF利用電視和娛樂的力量為生活在具有生態問題的地區(特別是在非洲)的生活環境改善作貢獻,并獲迪拜國際最佳實踐獎。
案例二:Shri Kshethra Dharmasthala農村發展項目(SKDRDP)。該項目組建以聯合責任小組(JLGs)為單位的自助小組(SHGs),通過小額信貸增強人們的經濟發展能力,尤其是提升農村婦女的經濟能力。該組織以實施“食品換工作”的項目進行土地開發,使居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其家庭可獲得大米作為補償。這一項目采取自助模式來提升人們的經濟能力,也通過組織自助小組(SHGs)或者聯合責任小組(JLGs)的方式來確保可持續性的脫貧成效。為了給有時間和有工作意愿的農村家庭主婦和失業青年提供工作機會,項目的婦女發展委員會設置了“業余社工”(Sevaprathinidhi)的崗位,使志愿者可以使用業余時間支持社區工作。
案例三:印度Sarva Seva農場協會(ASSEFA)。在印度種姓不平等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它通過甘地的“土地贈予”運動,支持高地家庭向無地低地農戶捐贈土地并保持可持續發展*ASSEFA, http://www.assefawr.org/.。其進程是由田野調查員進行社會調查,在此基礎上,設立小規模的試點項目,建立農戶合作并提高信任度。如果能夠成功運作,再擴大項目并提供技能培訓。當項目成熟了,ASSEFA在幾年后將逐漸撤銷其支持。這一發展項目的立腳點是農戶利用當地資源進行集體努力,而不是從外部輸入資源。該協會的支持活動使農戶可以從土地上獲得收入并鞏固土地使用權的安排,這種安排使各戶既能夠增加收入,開展信貸和培訓工作,也使被支持的低階層家庭并沒有在社區中丟失體面。*Thomas,1992 73. Thomas, A. (1992) ‘NGOs and the limits to empowerment’. In M. Wuyts, M. Mackintosh and T. Hewitt (eds), Development Action and Public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從以上三個范例看出,這些當地的非政府組織通過采取相關的社會項目來推進當地社會的發展。其社會改造的行動并不是在政府的要求下進行的,而是由當地的市民社會內生的,通過賦權增能強化民眾的行動能力。在社區的發展模式上,這三個個案都是通過社會試驗、模式擴展和社會流行的過程不斷發展,通過引起廣泛的社會影響和民眾的積極參與來獲得社會改造的成效。這些非政府組織的活動與當地社會的民生問題密切相關,帶有很強的發展效用。這些項目十分強調宣傳教育、培訓等因素,也注重增進人力資源的提升,并且維護這些活動的可持續性,反映出非政府組織在推進當地社會發展進程上具有優勢。
除了這些基于地方NGO進行努力的成功個案外,我們也看到在國家和區域層面上非政府組織所作的貢獻。在此我們同樣給予三個案例來展示。
案例一:發源于南非的貧民窟居民國際(SDI)。這一國際非政府組織旨在將無家可歸的人和非政府組織聯系起來,建設基礎設施提高居住權保障的程度,為城市貧困人口提供基本居住條件。它在32個發展中國家面對200多萬貧民窟居民,加強對無家可歸者的幫助以確保他們的生存能力。它定期組織窮人與該組織之友建立起支持關系,到2007年為止,有超過25萬個家庭獲得了該組織提供的安居服務。*SDI (Slum Dwellers International). Who is SDI?, http://knowyourcity.info/who-is-sdi/about-us/.
案例二:津巴布韋的教會組織。在非洲,非政府的衛生服務組織對當地社會提供各種直接服務和自助活動。特別是以教會為基礎的非政府組織在提供醫療服務方面尤為突出。這些教會組織在津巴布韋提供了農村地區所有醫院病床的68%,而在贊比亞,教堂組織在農村地區提供40%的醫療服務。在烏干達,很多農村學校和地方醫療診所由這些組織所支持。這些行動促使其社區成員組織快速增加,從而使非洲各種自助組織的增長構成了全球發展的組成部分。
案例三:國際非政府組織反販賣婦女聯盟(CATW)。該組織成立于1988年,在菲律賓、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泰國、委內瑞拉、波多黎各、智利、加拿大、挪威、法國、希臘和澳大利亞等國家都設有分支機構,也擴展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島嶼。該組織致力于打擊販賣婦女行為,尤其是與賣淫相關的人口販賣活動。在菲律賓,這一聯盟組織對男女青年做了大量性別、性行為和反對賣淫等知識訓練。它設立訓練營,每個營地大約有50名男孩參加,出營需要通過畢業考試。營會還在賣淫興旺的社區教育青年,鼓勵他們把受到的知識訓練傳播給別的年輕人以打擊強奸和賣淫活動,也通過漫畫書教育女孩和男孩有關性剝削的現實和風險的知識。
以上三個案例從不同的視角反映出跨區域的社會組織和國際組織在增進社區發展和回應民眾需求方面所起的作用。這些組織所提供的社會服務大多依靠傳統的社會安全網絡來進行工作,例如通過教會、村莊和婦女兒童團體等組織來發揮作用,從而在社區中起到很強的協調、組織和區域發展方面的效用。同時,作為地方性聯盟或跨國組織,它們也與公共部門和國際組織保持一定的聯系,形成專業群體進行游說,扮演著公共部門與民間部門溝通的橋梁。
四、對于非政府組織在全球發展所起作用的研究
基于對非政府組織所起作用的調查研究,學者們從各種視角對這些經驗資料進行分析和闡釋。這些分析常常回應各種發展理論,包括現代化理論、依附理論、制度分析理論和新自由主義理論、替代發展理論以及后發展主義理論。在現代化理論中,人們常常強調生產方式的變化和人的發展對于走向現代化社會的影響(包括羅斯托、托夫勒和英格爾特等),但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很少被提及。依附理論則擴展了世界體系理論的分析,強調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成長過程中所面對的矛盾,并強調國際資本的影響和在社會領域中民族獨立的運動所產生的社會效應*Gunder Frank A.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HOWEL, N. etal. Catalyst, 1969: 58.。但這一分析主要聚焦于國際資本和國內經濟結構的二元區隔,而對于這一演化過程對非政府組織的影響這類問題則很少討論。
與此形成對照,制度主義的分析強調發展進程帶來的社會關系的變化,強調第三部門的成長和社會關系的重構,以及非政府組織在其中所起的作用。*Brett, E.A. Theorising crisis and reform: Institutional theories and social change in Uganda. Sussex: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Sussex, 1993.新自由主義理論則強調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與非政府組織的作用相關性,把非政府組織看作是市民社會中積極活動的社會主體。*Sachs, J., McArthur J W, Schmidt-Traub G, et al. Ending Africa's poverty trap.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04, 2004(1): 117-240.替代發展的理論則注重性別平等、公民賦權和公眾參與對可持續發展的意義*Clark J. Democratizing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Kumarian, 1991.,強調非政府組織在其中所能夠起到的作用。后發展主義理論則注重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發展中所作的積極貢獻。如Escobar強調發展的理念不應僅僅是運用西方經濟發展經驗的結果,發展中國家也作出重要貢獻。*Escobar A. Imagining a post-development era. Power of development, 1995: 211-227.在此,非政府組織在維護當地社會所具有的特點,推進社會改造方面都起到積極作用。這些理論和對于非政府組織作用的觀點可以通過下頁的表格反映出來。
基于這些理論立腳點來討論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如何強化社會基層組織建設、提升第三部門的作用、增進社會資本和培育具有活力的市民社會的作用,是人們關注的核心問題。盡管各學者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各不相同,但這些組織在推進社會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則是被普遍確認的。非政府組織的工作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也關注政治經濟變革,把互助救濟這些工作目標導向“發展”的理念*Social movements in development: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pringer, 2016.。由此,William與Young強調,非政府組織是變革發展的主要參與者,是推進增能賦權的現實政治力量*Williams, D. and Young, T. 1994: Governance, the World Bank and liberal theory. Political Studies XLII, 84-100)和Hearn, J. (2007) ‘African NGOs: The new comprador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8, 6.。Mercer也認為,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社會組織被視為發展中國家向自由和現代社會轉變的制度性手段*Mercer C. NGOs,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z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2002, 2(1): 5-22.。

理論、代表人物和年代主要觀點非政府組織的作用現代化理論W.W.Rostow(1960)由資本主義向當代資本主義轉化的過程和變革很少提及非政府組織依附理論A.GunderFrank(1969)殖民地國家遭受西方“核心國家”的剝奪所造成的從屬地位和欠發達狀態。很少提及非政府組織,但把“社會運動”視為促進自由與變革的積極力量制度主義發展理論E.A.Brett(1993)只有通過改善社會體系的結構性關系與獲得經濟活力才能取得發展的良好條件非政府組織被視為三大部門之一;在合適的規則和激勵機制的作用下并具有合適的背景和條件,非政府組織在提供服務方面可以比其他兩個部門更具有比較優勢新自由主義發展理論J.Sachs(2004)使全球化進程有利于窮人階層:市場機制是開發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潛力的核心動力非政府組織是民主化、私營化和在服務投遞中提高成本效益的社會行動者替代發展理論J.Clark(1991)著眼于市民社會,把性別平等、賦權和自下而上的參與作為可持續與公平發展的核心內容非政府組織與社會底層人群具有密切的關聯,它具有挑戰那些自上而下傳播的發展教條的能力后發展主義理論A.Escobar(1995)發展理念本身是西方國家強加給他人的不受歡迎因而需要被拋棄的理念非政府組織是推進現代化的行動者,也是本土經濟文化轉型的推進者;只有當地的社會運動才能抵制這些變化進程
資料來源:Lewis D. and Kanji N. (2009),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更進一步說,這些組織在實施當地社區建設和社會改造的行動過程中推進了全球治理進程。它們強化了地方和國際組織之間的聯系,推進本地社會與全球發展的導向相融合,建構起社會對話的渠道并使民眾能夠介入到國家社會治理的決策過程中。例如Waltz舉突尼斯為例,非政府組織對該國行政部門施加壓力,實現廢除該國臭名昭著的國家安全法庭和改革審前拘留的做法*Waltz S. Islamist appeal in Tunisia. Middle East Journal, 1986, 40(4): 651-670.。世界銀行的報告也談到非政府組織的積極參與可以促使政府部門權力下放,尤其是在那些地方特性根深蒂固和民族分裂的國家*World Bank 2000: World develoment report 1999/2000: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因此,非政府組織基于全球發展理念而進行的社會努力可以影響各國的政策制定理念、模式和方向,并制約政府組織的行為。
與此同時,非政府組織所進行的地方社會實踐也為國際組織豐富它們的發展理念提供了經驗基礎。非政府組織進行的地方實踐可以成為成功的案例來進行推廣,從而啟發國際組織對于全球發展的新的理念與新的視角。通過對于這些社會試驗的經驗進行理論概括和抽象,國際機構可以從而總結新的發展模式并進行推廣。同時,這些非政府組織所進行的地方性的實踐活動也可以充分展示全球發展的多樣性。全球發展的理念作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導向是抽象和一般的理念,它在各地會有各種表現方式。結合各地不同的社會歷史文化條件,同樣的理念可以形成不同的展示形式或實踐模式*林卡:《社會福利、全球發展與全球社會政策》,《社會保障評論》2017年第2期。。因而,地方實踐的豐富性可以給全球發展提供豐富的思想養料,形成具有多樣性色彩的全球發展前景。這就要求把全球發展的一般的目標和各種發展的可能性模式相結合,從而形成統一性和多樣性的有效結合。這就有利于培育統一的全球發展目標并達成發展目標的共識,避免了在全球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目標的沖突*林卡:《社會質量:理論方法與國際比較》, 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五、非政府組織發展的困境
在推進全球發展的歷程中,非政府組織在社會協調、構建政府組織與公民群體之間的聯系、建立社會共識等方面貢獻卓著;但其發展也存在著許多問題,面臨著各種困難。在與國家機構和國際組織關系的構建問題上,一些非政府組織受到民眾的批評,被認為過于依賴政府組織,或者成為國際勢力的新買辦。例如Tandon等左翼批評者指出,非政府組織幫助和維護(甚至擴大)了非洲新殖民主義體系;Hearn更直接批評非洲的一些非政府組織是“新買辦”*Tandon, Y. (1996) ‘An African perspective’. In D. Sogge, K. Biekart and J. Saxby (eds), Compassion and Calculation: the Business of Private foreign Aid London: Pluto press.,它們依靠國際機構來管理西方援助資金鞏固他們的政治和經濟權力。Kaldor也認為這些組織已經成為“馴化”激進的社會運動的工具*Kaldor, M. (2003) Global Civil Society: An Answer to War. Cambridge: Polity Press.,并進而指出,非政府組織可能會削弱來自社會運動的草根行動*Kaldor, M. (2003) Global Civil Society: An Answer to War. Cambridge: Polity Press.。他們質疑增加對非政府組織的財政支持可能實際上損害了具有代表性和參與性的民間社會*Mercer C. NGOs,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z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2002, 2(1): 5-22.。
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指出,在發展中國家,許多地方的非政府組織的發展面臨著威權主義政權所形成的壓力,這成為發展非政府組織的瓶頸問題。*Cleary S. The role of NGOs under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systems. Springer, 1997.例如在Okafor關于尼日利亞非政府組織的研究中強調,這些組織在增進當地社會的人權和影響該國立法的民主化建設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也幫助行政部門強化軍事統治的合法性,但在威權主義秩序下,它們的發展程度目前仍然十分有限。*Okafor, O. C. (2004). Modest Harvests: On the Significant (But Limited) Impact of Human Rights NGOs on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Behaviour in Nigeria. Journal of African Law , Vol. 48, No. 1 (2004), 23-49.在亞洲,Gray在對越南案例的研究中指出,威權主義的政體限制了越南非政府組織的發展規模和數量,因而如何推廣越南的民間社會發展和支持農村社會組織成長是尚未解決的問題。在拉美國家,Bebbington強調許多非政府組織在進行轉型后面臨著身份的重新定位問題。這些討論都涉及到非政府組織的自主性建設問題*Gray, M.L. 1999: Creating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NGOs in Vietnam.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0, 693-713.。
在與民間社會的關系問題上,一些人批評非政府組織的運作會具有官僚化的傾向*夏道明:《試論我國非政府組織公信力問題及其提升》,《新疆社科論壇》2010年第5期。。這使許多非政府組織的管理往往變得不民主,形成與捐贈者和國家組織合謀的態勢。例如在孟加拉國,Wood對“特許經營國家”的模式提出了關注。由于越來越多的社會服務項目被委托給地方非政府組織,一些非政府組織將工作注意力集中在捐助者的資助和行政采購而不是推進社會政治改革運動的發展。一些學者也談到,雖然非政府組織具有更多的社區實施機會和基層組織參與*Wood, G. 1997: States without citizens: the problem of the franchise state. In Hulme, D. and Edwards, M., editors, NGOs, states and donors: too close for comfort? London: Macmillan, 79-92.,但這些組織在項目管理中所具有的官僚主義色彩和政府對項目管理的低效率常常導致發展項目的執行無效。Mac Abbey批評一些非政府組織缺乏協調,管理機制不善,運作效率低下*Mac Abbey E. Constructive regulation of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8, 48(2): 370-376.。因此,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在2003年6月在其網站發聲,提出“非政府組織的透明度和問責制問題”*Welker M. Enacting the corporation: An American mining firm in post-authoritarian Indonesia.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另外,Oxfam也指出另一個管理問題,雖然在理論上說非政府組織經營應該擁有比私營機構更為有效的管理結構,但缺乏被廣泛接受的績效衡量標準阻礙了非政府組織制定明確的目標和評估工作進展*Oxfam G B. Cash-transfer programming in emergencies. Oxfam, 2006.。
此外,也有批評者指責非政府組織具有私利,并未對廣大民眾服務,而是服務于私利或者機構利益*Tandon, Y. (1996) ‘An African perspective’. In D. Sogge, K. Biekart and J. Saxby (eds), Compassion and Calculation: the Business of Private foreign Aid London: Pluto press.。Hearn批評說,一些非政府組織犧牲他們推進社會發展的理念而成為自利的行為者,按自己的利益來設立議程。因此,非政府組織是代表貧窮的和邊緣化群體的利益還是捐助者的利益,是賦予非政府組織行動的零政治動機只關注具體事務的運作,還是強化非政府組織的社會性、公益性以贏得公眾信任*Hearn, J. (2007) ‘African NGOs: The new comprador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8, 6: 1095-110,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在非政府組織與國際組織的協同關系上,盡管國際組織常常強調非政府組織的作用,但在國際援助資金分配中真正落到非政府組織的資金比重很少。例如在非官方國際援助中,非政府組織獲得的資金只占援助資金總額的15—20%*OECD, DAC1 Official and Private Flows (op. cit.). The calculation is Net Private Grants/ODA.。根據《2015年全球人道主義報告》,在國際人道主義援助總額中,只有0.2%直接投向地方和國家非政府組織,3.1%直接投向受災國政府*Global civil society 2005/6. Sage, 2005.。這一方面是由于國際援助的資金容易被濫用。同時也由于項目管理方面的問題,例如Hancock批評國際援助經費的使用很不透明,常常為城市精英、專家和政府官員所獲得,并未真正為需求人群所獲得*Hancock G. Lords of poverty: The power, prestige, and corrup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aid business.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2.。因此,國際組織與各國政府組織給予非政府組織的支持資金也很少*Assistance G H. 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2015. 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report 2015, 2015.,并且質疑非政府組織的權力資源和管理能力。
六、小結
本研究通過對國外學者對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發展中所起作用的討論,反映了人們在此議題上的各種觀點以及相關的實踐。這一回顧為我們加深理解非政府組織的國際實踐提供了相應的概念背景和經驗基礎。它所涉及的議題十分廣泛,而且不同學者所采用的視角也有很大的差異。但在這些研究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共識。作為活躍在第三部門中的社會主體,非政府組織在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方面積極行動,也在推進公民參與、培育民主制度、保障公民權利、提供社會福利等方面進行努力。這些因素都強化了非政府組織在推進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作用。同時,在推進全球發展方面,非政府組織可以作為國際發展運動的“信息傳達者”“協調者”“思考者”和發展方向的“探索者”。在實踐中,這些非政府組織成為國際組織在進行發展工作和人道主義援助的地方執行者,也是推進全球治理理念和國際發展的積極行動者。本研究在對于這些案例和研究評述中把非政府組織議題放到全球發展的背景中去探討,以期揭示這些組織在全球發展過程中的功能和特點。
當然,我們也要意識到各國的非政府組織結構復雜,并且與當地社會的文化、政治和經濟背景密切相關。要研究這些復雜的關系,就要深入考察非政府組織的行動邏輯,研究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以及市民社會和市場的關系。但是在不同的社會中這些關系很不一樣,而且各地非政府組織生存的環境也很不同,難以充分地反映非政府組織行動的多樣性。因此,本研究聚焦在對于非政府組織行動在推進發展方面的效應。這一研究雖然離不開對非政府組織發展成果和各影響因素間相互聯系的考察,但其研究的焦點是理念原則和政策倡導。基于這一考慮,本研究把非政府組織的議題與全球治理的議題相關聯,撇開了社會背景制度關系的分析,以便為我們理解全球發展的社會基礎和發展主體提供基本的概念原則和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