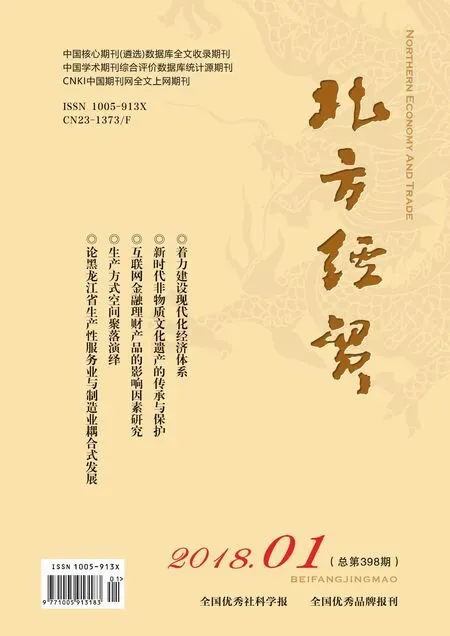商品房價格財富效應的地區差異研究
張志鵬,余海霞,羅 艷
(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經貿學院,鄭州450046)
隨著近年來房價的高速上漲,居民在購房方面的個人居住支出或者是投資保值支出相比過去大大增加,該現象對于居民消費的影響主要歸為兩類:財富效應和擠出效應。一方面,房產價格的上漲會使得擁有住房的消費者在出售房屋時獲得的收益增加,或者預期的收入增加,房地產價格的上升一般也會帶來房租的升高,出租房屋者獲得收益增加,消費水平提高,所以產生了正的財富效應;另一方面,房價上漲會增加有購房需求者的負擔,購房成本提高,他們會降低消費水平增加儲蓄去購置房屋,房租成本增加,因此會產生負的財富效應或擠出效應;此外,對于部分消費者,住房是為了滿足居住需求而不是投資,也無法變現為實際的購買能力,所以對消費不會產生影響顯著的財富效應。由此可見,財富效應有正有負。
二、分析模型與數據來源
(一)理論基礎
1.混合估計模型。如果一個面板數據模型定義為 yit=α+βxit+εit,i=1,2...N;t=1,2...T
α和β相同且不隨i,t的變化而變化,則稱這個模型為混合估計模型。y為被解釋變量,x為解釋變量,α為截距項,ε為誤差項。若選用此模型,則無論還是趨向于無窮,模型參數的OLS估計量均為一致估計量。
2.固定效應模型。固定效應回歸是一種空間面板數據中隨個體變化但不隨時間變化的一類變量方法。固定效應模型分為三種:個體固定效應模型、時刻固定效應模型、個體時刻固定模型。本文選用的是個體固定效應模型:

此時對于不同的個體有截距項不同即隨著的變化而變化。
3.平穩性檢驗。面板數據模型在進行回歸之前,必須檢驗其平穩性,否則可能會影響最終的結果。有些序列本身就是不平穩的,就算回歸之后得出的可決系數很趨近于,也沒有任何意義,這時候的回歸就是偽回歸,是不可取的。所以為了避免虛假回歸,必須對面板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
(二)模型選擇
根據前面所提到的消費函數和為了便于研究房價的財富效應,本文所采取的模型為:lnCit=α+β1lnIPit+β2lnFJit+μit,其中表示城市人均消費支出,表示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房屋平均銷售價格,用房價變動來表示居民資產財富的變化。
(三)數據來源與預處理
本文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鑒和各個城市的統計年鑒以及統計公報。由于我國房地產市場主要集中于城市,本文選取的是全國31個城市2004年~2015年的城市人均消費支出、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房屋平均銷售價格,房價的上漲對于人均消費支出的財富效應。全國31個城市主要包括省會城市以及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重點城市,由于拉薩統計局部分數據缺失,無法準確計算,所以并不在研究范圍之內。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費支出和房價會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所以要剔除價格因素的影響。然而各個地區城市價格存在差異,為了準確體現房地產價格的變化,于是計算各個城市以2004年為基期的CPI平減指數,用這個指數剔除價格因素,通過取對數得到的城鎮人均消費支出、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房價的對數序列。
三、實證分析
(一)面板數據的平穩性檢驗
本文采用的是LLC(Levin-Lin-Chu)檢驗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表明,三個變量均為平穩的,無需進行一階差分進一步探討,所以也無需進行協整檢驗。
(二)F檢驗和豪斯曼檢驗
本文采用面板數據模型,面板數據回歸模型的類型有:混合效應回歸模型固定、效應回歸模型和隨機效應回歸模型,這就需要運用F檢驗以及Hausman檢驗來判斷決定用三者中的哪一模型。
1.F檢驗。假設H0:β1=β2=…=βN(混合效應回歸模型)
H1:α1=α2=…=αN,β1=β2=…=βN(固定效應回歸模型)
其中,T=12,K=2。
如果接受了H1,則為不變參數模型;如果拒絕了H1,則檢驗H0,如果接受了H0,則為變截距模型,如果拒絕了H0,則為變參數模型。根據以上信息,分別計算混合效應、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回歸三種回歸模型的殘差平方和S1,S2,S3和各自的自由度。
通過Eviews8.0檢驗得表1:

表1 面板數據回歸模型F檢驗的殘差平方和與自由度

計算得出F1=30.3361,F2=48.2918,通過公式得到在顯著性水平為5%的Fa1(60,279)=1.367,Fa2(90,279)=1.3117。如果 F1>F[(N-1)k,N(T-k-1)],則拒絕H0,又 F2>F[(N-1)(k+1),N(T-k-1)],則拒絕 H1。由于F2>Fa2,則拒絕 H2,又由于 F1>Fa1,所以本文所用的模型采用變系數模型。
2.Hausman檢驗。通過Hausman檢驗得到的值大于臨界值,所以不拒絕原假設,應該用隨機效應模型,但是由于用隨機效應模型得出的可決系數R2很小,模型的擬合程度不好,又選取了固定效應模型做回歸,得到的可決系數R2=0.987比較大,擬合程度更好一些,根據Wooldridge的一般經驗研究,選擇固定效應模型解釋會更合理些,因此最終選取固定效應模型。
在這里再考慮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變量的固定效應模型在變系數模型情況下的估計系數。
通過變系數模型可以得到不同城市各個變量的收入估計系數房價估計系數如表2。

表2 固定效應模型變系數下的各城市收入系數以及房價系數
從表中可以看出,有些城市的房價系數為正即有財富效應,有些城市的房價系數為負即有擠出效應,有的城市的系數趨近0,財富效應不顯著。財富效應的有:深圳、上海、重慶、長沙、鄭州、太原、西安、福州、石家莊、哈爾濱、呼和浩特、烏魯木齊、廣州、海口、銀川、西寧、蘭州、成都、南寧、南京。擠出效應的有:北京、合肥、武漢、天津、濟南、南昌、長春、杭州、沈陽、昆明、貴陽。但是這樣并看不出區域特性,采用經濟意義,由國務院2015年提出的城市,將這31個城市分為了一線城市、新一線城市、二線城市、三線城市。其中一線城市包括:廣州、上海、深圳、北京。新一線城市包括:成都、杭州、南京、武漢、天津、西安、重慶、沈陽、長沙、福州、濟南。二線城市包括:昆明、鄭州、長春、合肥、南昌、哈爾濱、南寧、石家莊、太原、貴陽、呼和浩特。三線城市包括:烏魯木齊、蘭州、西寧、銀川、海口。假定各線城市中沒有個體差異和時間差異,不存在截距和斜率的變化,因此使用混合效應模型來分析各線城市的財富效應。

表3 全國各城市以及各線城市的消費函數
四、商品房價格財富效應的地區差異分析
綜合來看,這組消費函數的估計效果較好的,可決系數都挺高的,模型擬合程度很好。從全國的消費函數來看,修正后的可決系數為0.8014,模型擬合優度很好,解釋變量均顯著。房價系數為0.0758,表明房價每上漲1%,城鎮人均年消費支出增加0.0758%。說明在總體上看,我國房價總體的財富效應是正的,房價上漲會導致人們消費支出增加。
(一)一線城市表現為擠出效應
一線城市的財富效應為-0.1126,體現為擠出效應。現行的土地供給制度和城市化建設,導致了地少人多。房地產生產周期長導致供給曲線陡峭,供給彈性小,房屋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取代,所以對于一線城市來說,人口集聚性比較強,土地資源稀缺,人們普遍對房地產的價格持有增長預期。實際情況看,我國北京、上海、深圳和天津等一線城市,房價收入比遠高于二線和三線城市,對城市居民造成了較大的負擔,所以他們一般只能減少消費來支付房屋的費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房子即為家,并且現在的人結婚的前提是必須有房有車,這就使得買房不僅是年輕人的事情,還是他們的父母所要一起承擔的壓力,于是伴隨著房價的不斷上漲,它們對消費的擠占作用也以倍數效應擴大。
(二)新一線城市表現為較弱的財富效應
新一線城市的財富效應為0.0188,體現出較弱的財富效應。新一線城市的房價沒有一線城市的房價上漲程度那么大,再加上新一線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近幾年也上漲的很快,房價收入比相比于一線城市較低,擁有住房者消費水平會有微小的提高,消費擠壓現象不明顯,所以房價上漲也并沒有產生較為明顯的財富效應,對消費也并沒有產生明顯的促進作用。盡管新一線城市房地產的財富效應并不顯著,仍有重蹈一線城市覆轍的可能性,所以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也會產生擠出效應。
(三)二線城市表現為財富效應
二線城市的財富效應為0.1082,體現為財富效應。由于二線城市的人口變動相對較少,而且那些房屋大多都是居民用來自住的,房價和上漲的幅度都比經濟發達的城市要低,同時人們認為房價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會覺得自己的財產在無形中增多,所以會提高消費,因此對消費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四)三線城市的財富效應不顯著
三線城市的財富效應0.066,體現為不顯著的財富效應。三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相比于一二線城市來說比較落后,房地產信息不完善,所以限制了房地產的流動性,并且這些城市的居民買房只是為了居住,投機成分也比較少,同時他們的收入也比較低,房價增長不高,資金緊張,社會保障不高,導致房價的上漲在這些城市的財富效應并不顯著。
五、結語
雖然房價上漲對于部分城市來說可以帶來財富效應,但是由于近年來房價上漲過快,已經給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隱患。
首先,房價的瘋漲會加大人們的貧富差距。近年來高漲的房價讓人們都向房地產行業聚集,富人們把自己的資金都投入到房地產行業的開發中,使得行業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加大。
其次,房價會影響消費結構和產業的結構調整,降低居民的生活質量。不斷攀升的房價使得中產階級迫于房價的壓力,減少了消費支出,降低了消費的能力,使得中國外向經濟無法轉變為內外兼收的經濟體系。
最后,過高的房價會刺激投機者的加入,嚴重影響我國的經濟發展的穩定性。由于我國的寬松貨幣政策,增加了市場的貨幣供應量,大量的錢財因為房價的攀升流向了房地產市場。由于地皮供給量的限制,過剩的流動性推動了房價的增長,不斷循環,使得房價高于普通居民的心理預期值。
[1]李淑云.房價的波動對城鎮居民消費的影響分析——基于24個城市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10.
[2] 李成武.中國房地產財富效應地區差異分析[J].財經問題研究,2010(5).
[3] 姚樹潔.戴穎杰.房地產資產財富效應的區域效應與時序差異:基于動態面板模型的估計[J].當代經濟科學,2012(7).
[4] 王春梅.中國房地產財富效應的區域差異分析[J].經濟實證,2015(6).
[5] 張 樂.我國不同區域房地產財富效應差異[J].宜賓學院學報,2014(3).
[6] 朱旭強,張忠壽.資產性收入與非資產性收入的財富效應研究——基于我國各省市城鎮家庭的面板數據分析[J].宏觀經濟研究,2013(11).
[7] 許家軍,葛揚.收入差距對我國房地產財富效應的影響[J].現代經濟探討,2011(7).
[8] 郜 浩,吳翔華.我國商品房價格與CPI關系實證研究[J].價格理論與實踐,2009(6).
[9]常 曄.房地產價格、CPI與居民消費需求增長——基于VEC模型的實證分析[J].宏觀經濟,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