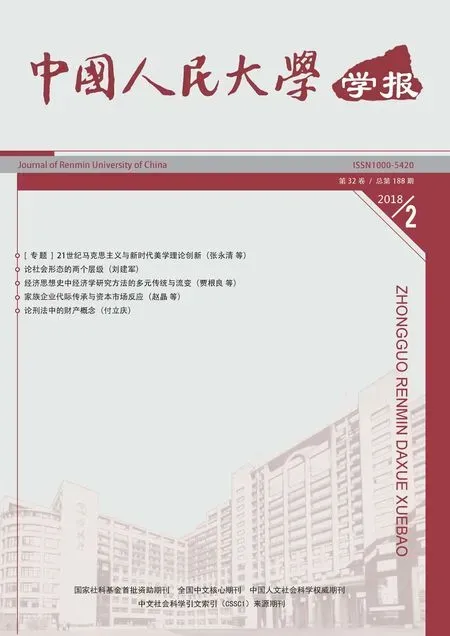先秦儒家憂患意識演變的邏輯
楊秀香 王 斌
本文擬從“合法性”視角探討先秦儒家憂患意識演變的邏輯。“合法性”概念源自現代政治理論,指政府與法律的權威為民眾所認可的程度,包含著民眾對政府權威的承認和服從。民眾為什么要承認和服從政府的權威、政府如何才能使民眾承認和服從其權威,構成了政府的合法性問題,前者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礎,后者是其合法性實現的方法途徑。顯然,只有解決了合法性問題,政府才能具有合法性。政府合法性問題的實質是政府權力是否代表民眾利益、其行政如何才能符合民眾利益的問題。政府能夠代表民眾的利益才能為民眾所擁護,民眾才能自覺服從其權威,其權力才能穩固,才能具有合法性,反之就沒有合法性。合法性內含著政府和民眾的倫理關系,提高政府權力(行政)的倫理性是解決合法性問題應有的基本思路。政府和民眾的關系在傳統社會是統治和被統治的關系,政府權力是統治者的專制統治的權力,因此,合法性在傳統社會指的是統治權力的合法性,合法性問題是統治權力的合法性問題。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先秦時期的憂患意識實質上就是在“憂”統治權力的合法性,擔心統治權力失去合法性的基礎——天佑、“道”、“德”、民心。
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憂患意識是指對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目標不能實現的警戒而謀求支持以克服阻礙實現目標的思維。這樣的目標不外乎國家興盛和百姓安樂兩個方面,司馬光在《進資治通鑒表》中就將“關國家興衰,系民生休戚”作為“機要”之事。具有憂患意識的人會因憂國之不興、民之不豫而奮發努力以圖國泰民安,所以憂患意識是一種積極有為的精神力量。在歷史上,這種精神塑造了一大批在國家危難、民生困厄之際,勇于擔當、力挽狂瀾的仁人志士,并因此成就了中華民族綿延幾千年的發展。在傳統社會,君主專制統治之下的國家“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君主“一個人按照一己的意志與反復無常的性情領導一切”*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國家系于君主一身,其統治權力是否穩固直接影響國家的興衰,憂國直接變為憂君,因此,憂患意識的所憂既在民生又在君主的統治權力。前者在歷史發展中被建構為“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一種民族精神,后者卻有意無意地被回避了。然而,在一種既定的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中,由于統治者往往居于主動地位,決定著天下的治亂、百姓的安樂,所以憂民生苦樂就不能不憂統治權力,因而是不應回避的。從發生學的意義上,毋寧說對統治權力的憂慮比對天下民生的憂慮具有先在性,先秦憂患意識的形成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這樣的觀點,即憂患意識是在對統治者可能失去天佑從而失去統治權力的恐懼中發展起來的。所以,先秦儒家憂患意識的核心就是統治權力的合法性問題,其發展在邏輯上有一個由擔心失天佑、失“道”“德”到失民心的延伸,并進而思考解決合法性問題的方法,即提出德治、仁政的過程,這一過程折射出的是社會轉型的必然性。權力對社會資源的掌控決定了只有擁有權力,才能使濟世安民、解決民生問題具有現實性,因此,在合法性的框架中對先秦儒家的憂患意識進行分析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新的認識角度,這或許有助于我們更加有效地推進社會治理。
一
先秦儒家憂患意識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所憂的對象各有不同。
第一個階段是西周時期,憂患意識的主體是統治者,其所憂在于失天命。
憂患意識人人都有,所憂的對象、憂慮的程度不同而已,但要構成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則必須具有共識性,因而憂患意識只能是關于民族社會發展的思考。這在古代社會集中表現在統治者那里,首先是對于統治權力鞏固與否的關注。當時社會通行的是宗教的思維方式,人們認為天、帝是自然和社會的主宰,自然和社會一切事物的生滅變化都體現著天、帝的意志,統治權力也是如此,其得失、穩固與否都是由天、帝即神決定的,天命就是其合法性的根據。在商代,已經有統治者把上帝作為自己統治的支持力量的記載*牟鐘鑒等:《中國宗教通史》(上),89-90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但總的說來,殷人似乎對自己的統治權力并不擔心,原因在于殷王認為自己受命于天:“皇天眷佑有商”,“先王有服,恪謹天命”(《尚書·盤庚》)。而天命是不變的,會永遠保佑自己:“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尚書·仲虺之誥》)但事實是殷人沒能如愿永遠保有權力,后來天又“降喪于殷”,收回了對殷所授之命,改命周人進行統治:“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尚書·召誥》)殷人因此喪失了統治權力。這一結果導致了周人對統治權力的擔心,由于權力是天所授命,天命就是其權力合法性的依據,失去天命就失去了權力的合法性,所以這種擔心就表現為對失去天命的恐懼。同殷人一樣,周人也認為自己是因天降大命才獲得統治權力的:“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民。”(《尚書·康誥》)文王立周也是天命:“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詩經·大雅·文王》)這是因為“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將先前授予殷的權力改授予周,是天命改變使然。周人因此沒有了殷人的勇氣認為自己能夠“永保天命”,而是承認天命是可變的:“惟命不于常。”(《尚書·康誥》)既然“皇天上帝”能夠 “改厥元子”,收回對殷所授之命,改命周人進行統治,那么,同樣地,周也存在著喪失天命、王朝傾覆的危險,所以周人告誡自己:“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尚書·召誥》)這是周公反思殷亡的教訓后產生的對周王朝命運的憂慮。
這種憂患意識在周文王那里就已經十分明確了,這在周初的《易經》(被認為是文王所作)中多有體現。《易·系辭下傳》指出:“《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這是說《易經》中的卦象是發展變化的,吉兇禍福沒有定數,因此,它讓人明白世事無常,必須有所戒懼,時刻保持警惕,做到趨吉避兇。《易·系辭下》認為:“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也就是說,人必須有危機感(行事小心謹慎),才能平安,否則就會有傾覆之禍。凡事皆如此,這是普遍規律,也是《易》所揭示的根本道理。因此,《易·系辭下》說:“《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經》就是為了防止和解除憂患而創作的。文王之后周的統治者憂天命、憂民意、憂道德,是《易經》中憂患意識的具體化,也是其政治實踐。
第二個階段是春秋時期,憂患的主體是孔子等儒家知識分子,其所憂在于失“道”、失“德”。
在西周時形成的憂患意識表現為統治者擔心政權之不得、恐懼權力之不保而做出的反思和自我警示,到春秋時則演變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知識分子面對天下大亂、禮崩樂壞的社會危機,出于對治亂救世的勉力擔當而對政治權力穩定與否的思慮。
中國奴隸制的發展在西周時達到鼎盛,之后開始衰微,社會進入了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春秋時期。當時周天子權威不再,制禮作樂、征討媾和等國家的重大事項,不再是由天子而是由諸侯們決定,諸侯們為了取代周天子稱霸天下而逐鹿中原,周禮所規定的等級秩序、在禮的基礎上形成的權利和義務的平衡關系被打破,貴族階級、奴隸階級、新興的封建地主階級或是為了維護或是為了爭取各自的利益而形成的沖突和對抗成為社會的常態。亂世之中治亂、救世是人們面臨的現實問題,如何治亂、救世是人們必須做出的選擇,“士”即當時的知識分子成了這一社會選擇的代言者。知識分子們有知識、懂歷史,熟悉政權興衰更替的經驗教訓,有著關于社會發展的理想,變動的社會讓他們看到了實現自己政治抱負的機會,為此他們游走于各諸侯國之間,希望借助于諸侯們的力量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政治主張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學派,即所謂諸子百家,儒家是其中最著名的學派之一。
儒家政治主張的基礎就是他們的憂患意識,但與周初統治者不同。周初的當權者最根本的恐懼是失去權力,其直接表現是害怕失去作為其統治權力支柱的天命,孔子所憂在根本上則是決定人事的“道”和“德”。孔子對天命能夠主宰自然和人事的絕對權能表示懷疑,如《論語》中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論語·八佾》)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論語·述而》)雖然孔子沒有明確否定天命,但認為同侍奉鬼神、祈禱天命相比,盡人事是最重要的:“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所以,孔子對鬼神敬而遠之,將憂慮的重點放到了決定人事的“道”和“德”上。社會的治亂說到底是人的行為的結果,取決于人的行為是否合于道,合于道則治,悖于道則亂。儒家的道有根本原則之意,按照“道”這一根本原則行事,則天下之人就會各行其是、上下有序:“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因此,儒家所憂的首先是“道”的存廢而不是天命:“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統治者依道而行就能夠掌握統治權力、樹立統治權威、具有合法性,相反,如果悖道而行,就會失去合法性、失去統治權威、喪失統治權力。其次,儒家所憂的是統治者道德的有無:“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孔子認為君子即統治者重義有德,小人即被統治者則重利無德(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所以“德之不修”指的應該是統治階級。再次,儒家所憂的是道德教化的缺失,由于百姓無德,所以必須對其進行道德教化使之有德,如果不能用道德禮義引導百姓,百姓在嚴刑峻法之下或許不會犯罪,但卻沒有羞恥心,因此,就沒有服從統治的自覺,統治秩序也就缺少保證。
顯然,天命的絕對權威消減了,“道”“德”的作用突顯出來了,“道”“德”作用的實質是人依道、依德而行,所以歸根結底是人的作用突顯了。這是一種新的關系,即無須以天命為中介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建立起來的直接聯系,從此合法性的依據從天命轉向了人。
第三個階段是戰國時期,憂患的主體依然是知識分子,代表人物是孟子。孟子所憂的是統治者失民心。孟子認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國君努力為百姓謀利益,就能夠讓百姓追隨、擁護,因而就沒有對手能夠戰勝他,就能夠統一天下。但現實是,統治者不關心百姓疾苦,致使百姓沒有財產、生活艱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因此,他們就不可能得到百姓的擁護。如果國君“失其民”、得不到國民的支持,就會被廢棄:“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孟子·盡心下》)不僅如此,如果諸侯的行為不合“為君之道”,老百姓甚至會弒“一夫”,對他進行“征誅”*殺無道之君,進行政權的轉移,這種政權轉移的方式叫“征誅”。。失民心必失天下:“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離婁上》)孟子告誡統治者要以此為鑒:“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同上)因此,民才是統治權力合法性的基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孟子提出了他的光輝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
孟子認為君與民在情感上、行為上具有對等性:“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孟子·梁惠王下》)國君如何對待民,則民就會以相同的方式對待國君。《孟子·梁惠王下》中有這樣的記載:鄒穆公問孟子如何處置在鄒國和魯國的沖突中不肯為本國官吏效命的百姓,孟子回答說這是官吏在災年不僅不關心百姓而且還殘害他們的結果,是百姓對官吏的報復,是不能責怪他們的。他引用曾子的話說“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你怎么對待別人,別人就怎樣對待你,官吏不管百姓的死活,百姓怎么可能為他們效命呢!“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孫丑下》)借助于這種行為上的對等關系,孟子就在邏輯上將作為合法性根據的人具體化為國人、百姓、民。這與孔子不同,孔子將合法性的根據從周人的天命轉變為人,但他所說的人主要是指舊貴族,孟子將民、百姓作為合法性根據,表明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以及對人民力量的重視。
二
因戒懼目標實現不了而憂,所以憂患意識往往會成為人們克服困難、消除障礙實現目標的動力,是一種奮發有為的精神力量。對失去權力的戒懼促使人們去思考化解權力危機的對策。權力危機的實質是其合法性的問題,統治權力要具有合法性,就必須適應當時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現實。中國從原始社會進入文明社會的特殊道路即保留氏族制度、延續氏族統治的結果是形成了宗法等級制的社會,家國同構。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倫理道德是重要的社會調節力量,因此,訴諸道德是得到民眾支持、取得合法性的重要方法。
西周的統治者主張以德配天命,認為用施德于民的手段就能達到永保天命的目的。他們將天命作為權力合法性的基礎,認為只有保有天命才能保有權力,而為了保有天命,統治者的行為必須合于天意。天命、天意是抽象的,它必須具象化才能得到體現,具象化了的天命、天意就是民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泰誓中》)天只能授命給能夠為民做主的人以權力,讓他們治理天下:“天惟時求民主。”(《尚書·多方》)民意由此決定了權力的穩固與否,統治者必須視民之所視、聽民之所聽、從民之所欲以合于天意。然而,“民心無常”(《尚書·蔡仲之命》),這就使統治者不能不對民心的向背心存畏懼。要得民心、合民意,就要了解百姓的意愿,滿足百姓的需要,實現百姓的利益,而生活安逸是百姓最基本、最普遍的需要和利益,這對于統治者而言就是要盡“人事”,即“保民”,也就是周公所說的使百姓康寧安定,“用康保民”(《尚書·康誥》)。一方面,要了解百姓勞作的艱辛、生活的痛苦,要“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尚書·無逸》),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另一方面則要重視民生,“惟惠之懷”(《尚書·蔡仲之命》), “安民則惠”(《尚書·皋陶漠》),尤其是要保護老弱孤幼,“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尚書·盤庚》),這就是要“施實德于民”(《尚書·盤庚》)。合于民意的行為就是“保民”,就是德之所在,因此,統治者必須以德克配天命。如果統治者無德,不計民生,罔顧民意,對百姓采取嚴刑峻法,招致民怨,天就會代民降災行罰。夏桀無道濫刑,施行虐政,殘害百姓,令百姓痛苦不堪,百姓怨聲載道上達天聽,天遂降災罰夏;商紂無德,百姓不滿,所以天“降致罰”——降喪于殷。(《尚書·酒誥》)有德才能配天命:“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詩經·大雅·文王》)夏桀、商紂因為不敬重道、德而早早失去天命,這對周的統治者來說是必鑒之前車:“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尚書·召誥》)他們認識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尚書·蔡仲之命》),因而在統治過程中“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一方面是對德的敬畏,另一方面則是對失德的恐懼。周公告誡統治者必須敬德,要“以德配天”,才能永保天命:“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書·召誥》)由此開啟了中國社會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德治傳統之先河。
孔子主張德治,認為統治者施德于民,教化百姓,就能使其服從統治。在他看來,天下大亂的原因,一方面是百姓“好勇疾貧”,另一方面是統治者“人而不仁,疾之已甚”這樣極端的、對抗性的行為造成的:“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泰伯》)侯外廬先生分析說:“一方面所謂‘小人不知天命’,如‘賜不受命’之類,因了不愿貧賤,爭相為富,以致產生出社會的亂子;他方面‘人’(舊人,指貴族君子)而不仁,恨小人過火,形成了對抗之勢,那也會發生大亂的。因此,統治和被統治的關系都走進了矛盾中,這就是社會的危機。”*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14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孔子認為,要治亂,就要恢復“禮”的權威,要“克己復禮”,用“禮”約束人的行為,避免走向極端:“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仲尼燕居》)他的學生有若將其思想概括為“禮之用,和為貴”。但是,社會動亂恰恰源自人們對禮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的反抗,這是孔子必須正視的,所以他對禮進行了損益,用“仁”補充禮。仁是人的一種愛人的內在道德情感、道德品質。有了仁這一道德情感和品質,人就會自覺依禮而行。而仁的規范作用,首先在于對統治者的作用,即統治者必須有德。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系上,掌握社會資源的統治者處于絕對主導的地位,其道德決定著被統治階級的道德:“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從而決定著整個社會的道德。統治階級之德重要的是統治之德,一方面,要施德與民,給百姓以利益,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只要百姓能安心生活,他們就會按照統治者的意志行事,“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只要統治者以德行政,百姓就能順從統治:“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另一方面,統治者自身必須有“德”,上行下效,人們自然依德而行:“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這樣一來,統治秩序就能夠得到維護。其次,被統治階級要有被統治之德。被統治之德有兩點:一是不“犯上作亂”,不“犯上作亂”就會安于被統治:“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二是要有羞恥之心。百姓有了羞恥心,就會自覺地服從統治階級的統治:“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因此,對統治者而言,要具有合法性,最重要的是要加強對百姓的道德教化,而不是動輒殺罰,否則其統治就是暴虐:“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堯曰》)
孟子則提出了仁政理論,主張統治者施行仁政以爭取民心。他總結了桀紂的教訓,看到權力的得失全在于民心的向背,而要得民心就必須行仁政。如果統治者實行仁政,全天下的人都會翹首以盼,擁立他為王:“茍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孟子·滕文公下》)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仁政出于統治者的不忍人之心,即仁的品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孫丑上》)仁者愛人,仁政就應該是對被統治者有利的統治方式,統治者關心民眾的疾苦,使民眾生活安樂, 就能夠為老百姓所擁護。施行仁政有兩個方面:
第一,對統治暴虐的君主進行討伐,救民于水火。小國宋國要實行仁政,卻遭到了齊楚兩個大國的攻擊,應該如何應對呢?孟子在回答萬章的詢問時說:湯討伐了葛國,是因為葛國的國君殘暴不守禮法,帶領百姓搶奪、殺死給他們送好酒好菜的亳地的百姓,甚至包括一個孩子,湯使天下的人看到他不是為了自己發財,而是為了替亳地的百姓復仇:“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仇也”(《孟子·滕文公下》),所以百姓盼他如“大旱之望雨也”。因為得到百姓的擁護,湯率領的軍隊所到之處戰無不勝。周朝初年,周王東征,救百姓,殺暴君,人們甘愿“臣服于大邑周”,其功績比湯還要光輝。這都是實行王政的結果。統治者討伐暴君,救民于水火,就能夠得到百姓的支持、愛戴,從而無敵于天下,因此,只要宋國實行王政,齊楚再強大也沒有什么可怕的。
第二,給百姓以“恒產”,使民為善順從。仁政的根本是“制民之產”,即給老百姓以“恒產”(固定的產業),使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認為,百姓的特點是有了固定的產業,才會常存善心,遵守道德規范,反之,沒有固定的產業,就不會有善心,不會遵守道德規范:“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孟子·滕文公上》)百姓有恒產并進而有道德,就會依善而行、順從統治:“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孟子·梁惠王上》)統治者實行仁政,就能得到天下人的擁戴,獲得無上的權威:“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同上)
三
不難看出,在先秦憂患意識的演變中,民意始終在場,始終是影響權力合法性的因素,但是,很顯然,在不同時期人們對其影響的重要性的認識是不同的,呈現出日益增強的特點。在西周,民意只是被作為天意的世俗體現,并不構成獨立的影響權力合法性的現實力量。從春秋開始,民意脫離了天意表現出獨立的姿態,但當時民僅僅被看作是可以通過教化接受統治的對象,其對統治權力認可與否、服從與否僅僅以統治階級的意志為轉移,并不構成影響權力合法性的自主力量,其自身也沒有形成影響權力合法性的自覺。到了戰國時期,民意則已經被視為可以左右國君的去留、影響統治權力合法性的決定性力量。民意之于合法性意義的不同在于社會的變化,社會的變革決定了合法性的根據從天命向人、由人向民的轉變。
西周時,社會還保留著從原始社會延續下來的氏族制度,實行氏族統治,土地的所有形式是“國有”,即氏族貴族公有制,沒有形成建立在經濟私有基礎上的“國民階級”(土地貴族、自由民、手工業者),所以那時的“思想意識當然不是國民式的,而是君子(氏族貴族——作者注)式的。具體地講來,意識的生產只有在氏族貴族的范圍內發展”*③④⑤ 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25、144-147、20、38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殷周時期,氏族貴族的思想意識是宗教式的,宗教思維方式表現為人們將天、帝看成是自然和社會的主宰,決定著自然和社會一切事物的生滅變化,也是統治權力合法性的依據。就被統治階級而言,之所以要服從受天命進行統治的王權,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的王權能夠代表自己的利益,即所謂天讓王做民之主,但是,民并沒有因此過上安穩的生活,相反,由于社會戰亂不斷,百姓的生活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人們對天命已失望至極。因此,天的權能及其正義性也就受到了懷疑:“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詩經·小雅·雨無正》) “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詩經·大雅·云漢》)因此,信天意不如信自己,奴隸開始奮起造反,反抗統治,進行大規模的暴動。
到了春秋時期,自由民(國人)開始出現,這些人因為積累了財富而逐漸進入社會的上層。周王室能夠控制的社會體制無法應付社會的這種結構性變化,結果天下大亂,不同階級之間的沖突和對抗成為社會的常態。《莊子·盜跖》中記載了跖領導的奴隸起義:“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左傳·襄公十一年》記載,公元前484年,陳國的貴族轅固為陳國國君的女兒做嫁妝,自己也中飽了一部分,加重了對奴隸的剝削,結果,“國人逐之”,把他趕到國外。志在“救世”者如孔子一類的知識分子,將社會動亂的直接原因歸結為小人好勇、貴族不仁;將其深層原因歸結為人們的利益之爭:“不愿貧賤,爭相為富”;而最根本的原因則在于人的行為、社會的統治缺少道德:被統治者缺少道德才會“犯上作亂”,統治者缺少道德才會實行暴虐統治。所以,孔子實質上是將道德和人看作統治權力合法性的基礎。由于孔子是以“復禮”即維護日漸沒落的奴隸制為己任,要通過“正名”恢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舊秩序,因而被他作為統治權力合法性基礎的道德只能是統治階級的道德,作為道德主體的只能是舊貴族。雖然那時國人已經對國君的權力開始產生影響*《左傳·昭公十三年》記載,楚靈王驕奢淫逸、窮兵黷武招致民怨,他在征討徐國時,楚國內亂,右尹子革建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讓國人決定他的去留。,但被統治階級還不能對統治權力構成實質性的制約。《左傳·襄公十四年》有這樣的記載:“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 、社稷無主,將安用之? 弗去何為?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這是說,人們把自己看成羊群,希望君主像牧人一樣對自己進行統治,使自己不失本性,君主的統治是他們的希望所在。可見,當時的被統治者并沒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因而還沒有表現出決定權力合法性的自覺,這是因為被統治階級即自由民(國人)正在形成、尚不成熟。③
孟子生活在戰國時期,以周禮為表征的奴隸制已經瓦解,封建制在主要的諸侯國已經確立起來,諸侯們窮兵黷武,其目標是要“王天下”即統一天下。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新的社會階級——“國民階級”,在社會中已經“具有支配的地位”④。侯外廬先生指出:“孟子客觀上承認了小生產的‘恒產制’,因此,他把小人的范疇相對地擴大了”,小人即被統治者,包括有“恒產”的國人。地位穩固的“國民階級”在事實上顛覆了奴隸主貴族的專治統治,一方面,因為“國民階級”中的賢者也會被舉薦獲得官職、掌握權力:“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西周宗法的‘宗子維城’到了戰國,發生了變化,國人、自由民也參與政權了。”⑤另一方面,“國民階級”中的一些人在禮崩樂壞、社會權利義務重新分配之際成為“上下交征利”的贏家,積聚了大量的社會財富,成為所謂“巨室”,他們的支持是統治者統治的必要條件,統治者要進行統治就不能得罪他們:“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孟子·離婁上》)不僅如此,最重要的在于他們有著巨大的社會影響力,能夠引導民意:“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孟子·離婁上》)當然,他們的訴求往往也表達著民意,有著動員百姓的社會作用。顯然,人數擴大、地位穩定的“國民階級”,通過不同的方式能夠直接或間接地對一國的政治產生重要影響,其力量大到如此程度,如果國君、諸侯不能得到他們的支持,就存在著被“變置”甚至“征誅”的危險,表明民已經擁有了影響權力合法性的主動權。正因為如此,孟子敦促那些諸侯施行仁政,用仁政爭取百姓的擁護,以使自己的統治具有合法性:“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同上)“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同上)這樣,統治權力合法性的基礎就從舊貴族轉變為新的“國民階級”(“民”)。
可見,從“求民主”到“民貴”,民在合法性中的作用由被動到主動的變化是社會結構的轉型決定的,是必然的。
由對權力得失的戒懼到對天下民生的關注,由關注天下民生而反思權力,是憂患意識形成過程中相向而行的兩條路徑。實際上,對天下民生的關注與對權力的反思戒懼在憂患意識形成過程中是一種共時態關系,二者共同構成人的社會歷史擔當相互支持的兩個方面:“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那些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洞悉具有合法性的權力之于國計民生的重要作用,他們對苛政的批評,批評君王之過,向君主進言諫議,體現了他們對于民生苦樂、社稷安危的高度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