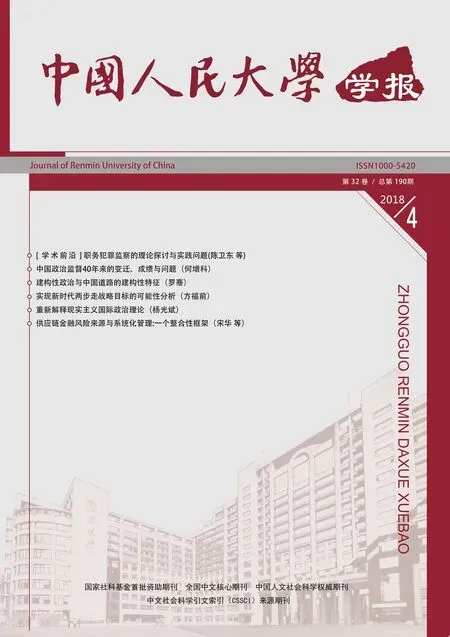“求富”的契機:李鴻章與輪船招商局創辦再研究
朱 滸
李鴻章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創設輪船招商局之舉,向來被視為洋務運動從“求強”轉入兼顧“求富”階段的顯著標志,也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工業化進程中的一個重大事件。但是,為什么是此時開始“求富”,又為什么是由李鴻章來創設該局、并在這個時間開局呢?要探究該局創辦緣起,這本是不容繞過的問題,而學界以往多拘泥于經濟史視角,在揭示這一時期國內外航運業發展狀況、洋務運動興起等背景后,便轉入對開局經營情形的探討。[注]這種敘述口徑最早出現在陳振漢1948年完成的《“官督商辦”制度與輪船招商局的經營(1872—1903)》一文,參見易惠莉、胡政主編:《招商局與近代中國研究》,43-52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新中國成立后,在招商局創辦緣起問題上最典型的表述可見于兩部權威著作(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二卷,402-40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下冊,1359-13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其論述口徑與陳振漢并無二致。實際上,由于對前述問題的忽略,以往論述并沒有完整展現該局的創辦過程,特別是嚴重忽視了其中牽連的諸多重要社會脈絡,以及歷史當事人的主觀能動性。而要準確解釋這類問題,就需要對該局創辦緣起秉持一種開放、綜合的視角,決不能就經濟論經濟。只有全面審視這一事件所依托的實踐進程,發掘其中蘊含的社會脈絡,才能為深入理解洋務建設活動的運作機制提供一個可靠范例。
一、異路:同治十年前的李鴻章與航運業
對于輪船招商局的最終創辦,李鴻章確實發揮了主導作用。然而,這并不等于說在中國輪運業的發軔過程中,李鴻章是創辦輪船招商局的當然人選。事實上,如果把時間回溯到同治十年(1871年)以前(至于為什么要回溯到這個時間之前,容后再加解釋),可以說李鴻章不僅不是招商局創始人的當然人選,甚至都很難說是最有力的競爭人選。這種說法的主要理由是:另外兩位老資格洋務巨擘曾國藩和左宗棠,對于引進輪船和近代航運事務方面的認識和實踐,較李鴻章而言具有十分明顯的優勢。
曾國藩與輪船及近代航運事務之間的淵源,在同時期督撫級別的官員中堪稱最為深厚。甚至可以說,如果同治十年(1871年)前能夠設立輪船招商局或者類似機構,那么曾國藩成為其創辦人的可能性應該是最大的。
首先,曾國藩引進輪船的熱心以及支持試造輪船的活動在洋務大員中都是最早的。最晚到咸豐十年(1860年)間,他就已充分領略了輪船的功效,從而向朝廷明確提出了仿造輪船的建議。[注]李瀚章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二,2025頁,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次年(1861年)七月間,朝廷就購買外洋船炮事宜向他征詢意見,他就購買、仿造輪船的裨益進行了一番詳細的解釋,并斷言:“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注]李瀚章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四,2262-2263頁,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在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初七的日記中,曾國藩也留下了“欲求自強之道……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功夫”[注]曾國藩:《曾國藩日記》,中冊,530頁,九州出版社,2014。的文字。同治四年(1865年)底,曾國藩致信李鴻章稱:“輪船亦不可不趕緊試造。”[注]李瀚章編:《曾國藩全集》,《書札》卷二十五,15232頁,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曾國藩的這些話絕非空言。他從設立安慶內軍械所不久,就奏調以精通西學著稱的徐壽、華蘅芳等人開展試造火輪船工作,并在同治二年(1863年)底造出一只可以航行的小火輪船。曾國藩因此備受鼓舞,一度還有繼續將小火輪船放大、改進的設想。同治六年(1867年),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后,又著力推動江南制造局開辦造船業務,從江海關解部經費中為之奏撥專項經費,添設造船設施。[注]樊百川:《清季的洋務新政》,下冊,1392-1393、1396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其次,在中國內部開始嘗試興辦近代航運的過程中,曾國藩也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隨著外國輪運業滲入中國,到19世紀60年代,華商寄名外國公司之下從事商業性輪運活動已經相當普遍。為了改變這種情況,清政府試圖對華商投資輪運事務進行管理,卻一直議而不決。同治六年(1867年)初,總理衙門兩次就“華商置買洋船”之事咨詢曾國藩,后者明確表示可以放松。正是基于這種放松管制的思路,曾國藩又推動總理衙門核定了《華商買用洋商火輪夾板等項船只章程》,并于是年九月初公開頒行。[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匯編·海防檔》,甲《購買船炮》(三),864-867、876-881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
基于上述情況,曾國藩一度被社會上認為是最有希望推動新式輪運業建設的高級官員。同治六、七年(1867年、1868年)間,華商群體曾出現過連續4次申辦輪船公司的小高潮,其遞交申請的對象都是曾國藩。[注]張后銓主編:《招商局史(近代部分)》,20-22頁,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而此時的曾國藩出于“用輪船則沙船盡革,于官亦未為得計”[注]江世榮編注:《曾國藩未刊信稿》,285頁,北京,中華書局,1959。的持重心理,對于發展輪運的態度變得遲疑起來,最終沒有支持過任何一次動議,使得這個小高潮迅速歸入沉寂。
在曾國藩之外,另一位洋務領袖左宗棠也較早對引進輪船及新式輪運表現出了濃厚興趣。同治二年(1863年)初,他就向總理衙門表示:“將來經費有出,當圖仿制輪船。”[注]楊書霖編:《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六,2861頁,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此后,他的這種態度愈發鮮明。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底,他就浙江善后事宜向朝廷奏稱:“欲治洋盜以固海防,必造炮船以資軍用。”[注]楊書霖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一,451頁,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同治四年(1865年)春,他因發現太平軍得到外國輪船支援之舉,再次向總理衙門強調了仿制輪船的急迫性:“至中國自強之策……必應仿造輪船,以奪彼族之所恃,此項人斷不可不羅致,此項錢斷不可不打算,亦當及時竭力籌維。”[注]④ 楊書霖編:《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七,2901、2950頁,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
在開展造船行動方面,左宗棠甚至比曾國藩表現出了更大的魄力。左宗棠自稱,在克復杭州后不久,他就“覓匠仿造小火輪”,并委托稅務司法國人日意格等,準備進一步展開造船活動。[注]⑤ 楊書霖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一,693、697頁,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間,總理衙門因相繼收到總稅務司赫德、英國公使阿禮國及參贊威妥瑪等人關于中國應“借法自強”的說貼和照會,遂飭令沿江沿海各督撫發表意見。[注]寶鋆等編:《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十,3764-3767頁,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左宗棠趁機先向總理衙門提出“購買輪船又不如自造輪船之最為妥善”的建議④,稍后又向朝廷提出了大辦輪船的計劃,并得到了允準⑤,這就是福州船政局的緣起,此不多贅。而眾所周知,該局起步時的規模就遠遠大于曾國藩在江南制造局內開辦的造船業務。
對于發展輪運事業,左宗棠也持較為積極的態度。前述清政府在討論如何對華商投資輪運事務進行管理的過程中,左宗棠是率先表示可以允許華商購置輪船的高級官員之一,還擬訂了一個管理章程遞交給總理衙門討論,明確提出華商可以向洋商購買輪船。[注]⑨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匯編·海防檔》,甲《購買船炮》(三),821-822、839-840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另外,正如樊百川注意到的那樣,左宗棠在奏請朝廷同意創立福州船政局時,雖然其根本目標是制造兵船,但其闡發造船必要性的第一個理由,卻是基于發展航運業而展開的。[注]樊百川:《清季的洋務新政》,下冊,1401-1402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然而,隨著他在船政局正在建設之際便被調任陜甘總督,此后數年間忙于西北軍務,再也無暇顧及輪運業問題了。
與曾國藩、左宗棠兩人相比,同治十年(1871年)以前,李鴻章與輪船及輪運業事務的關系可謂十分淡薄。首先,這一時期的李鴻章對于造船業務始終態度消極。前述曾國藩于同治四年(1865年)底曾商勸李鴻章仿造輪船之事,而當時正在建設江南制造局的李鴻章卻表示“未敢附和”[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0冊,413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其次,在有關華商從事輪運問題的討論中,李鴻章表達的是收緊的立場。同治四年底,時江海關道應寶時曾擬定了一份章程,意在對華商經營輪運業略施通融。當時擔任上海通商大臣的李鴻章卻批示:“即試行果無流弊……亦不準隨意進泊內地河湖各口,只準在于通商江海口岸往來買賣。”⑨可以說,這個時期的李鴻章,還遠遠算不上發展輪運業的同路人。
二、砥柱:李鴻章與輪船招商政策的定議
李鴻章再次就發展輪運業問題明確表達意見已是大約六年之后,也就是那場著名的、朝廷內部爆發的關于造船業前途的大辯論之時。以往研究表明,正是通過這場從同治十年(1871年)底延續到次年初的大辯論,李鴻章才成為了發展輪運業的主力人物。可是,鑒于前述同治初期李鴻章對輪運業所持的負面態度,以及曾國藩和左宗棠此時仍然位高權重的情況下,李鴻章何以能夠在這場辯論中最終脫穎而出呢?李鴻章這時究竟有著怎樣的非凡表現,才能夠超越曾國藩和左宗棠而最終成為輪船招商局的創辦人了呢?這都是以往很少有人注意的問題。
要充分理解曾國藩、左宗棠以及李鴻章在這場辯論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必須厘清這場辯論的重心之所在。眾所周知,這場辯論的導線是內閣學士宋晉在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的上奏。對此上奏,通常論述大都集中在批駁宋晉關于停辦造船的意見上。其實,宋晉提出停辦船廠后,還有一項建議:“其已經成造船只,似可撥給殷商駕駛,收其船租。”[注]佚名輯:《晚清洋務運動事類匯鈔》,上冊,185-186頁,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9。這里顯然也包含著將官辦船局轉化為招商養船的意思,所以客觀而言,這次上奏對發展輪運業無疑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況且,此前不久,朝廷正因福州船政局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飭令總理衙門與沿海各省督撫籌商養船辦法。[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匯編·海防檔》,乙《福州船廠》(一),311-312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這樣兩個情況相疊加,使得要不要發展航運業及如何發展,成為無法回避的問題。
以往研究指出,對于停辦造船之議,曾、左、李三人都旗幟鮮明地表示了反對,從而使得此議沒有形成太大的波瀾。但以往論述不夠充分的是,在如何發展輪運業的問題上,此三人的看法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認識差異,并由此映射了其后各自不同的行為軌跡。
如果依照建設性意義的高低給此三人排序的話,那么左宗棠的認識水平當屬叨陪末座。至于反映其認識水平的首要文獻,是他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末的一份上奏。在這里,左宗棠的主旨是解釋所謂“糜費太重”以及“局內浮費如何減省”問題。[注]而對于如何養船的問題這里全無涉及。遍查這一時期左宗棠留下的文獻,只發現他在同治十年(1871年)底給胡雪巖的一封信中,曾談及“若以官造輪船運銷官鹽”,則將來或可有所盈余。[注]楊書霖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一、《書牘》卷十一,1605、3064頁,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且不論官鹽銷售向來屬于老大難問題,即以福州船政局而論,該局所造皆為兵船,能否在內河航行、貨運功能又如何,都是沒有經過檢驗的問題。這就可以理解,左宗棠的這一設想此后連他自己都再未提過。
相比之下,曾國藩的認識水平明顯比左宗棠高出不少。曾國藩的看法,主要體現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底給總理衙門的回函之中。與左宗棠著意解釋經費并未糜費的態度不同,曾國藩明確承認造船、養船經費造成了難題。同時,對于利用現有輪船開展租賃的設想,他也非常清楚其中困難。接下來,曾國藩還對發展商運給出了建設性意見:其一是提出兵船和商船的建造要齊頭并舉,其二是建議選拔熟悉商情的官員與商人合作。[注]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匯編·海防檔》,乙《福州船廠》(二),325-326、325-326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
不過,有學者稱曾國藩“準備趁此機會,重新倡導和親自主持創辦中國新式輪運業”[注]張后銓主編:《招商局史(近代部分)》,25頁,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恐怕是一個誤判。首先,連曾國藩自己都承認,已有商船并不具備市場競爭力,而新造商船的計劃更不知何時啟動。其次,他對于能否找到實現官商合作的人選也毫無信心,如其前函中所言:“此等為商賈所深信之員,急當物色之,目前恐難驟得耳”⑦。所以,即便不是因為曾國藩此后不久突然去世,他也很難具有創辦輪運業的決心。更糟糕的是,曾國藩去世之后,南洋官場高層對于創辦新式輪運業更無進取之心。曾國藩盡管對輪船招商信心不足,但為了給總理衙門一個交代,還是委派綜理江南輪船操練事宜的吳大廷和江南制造局總辦馮焌光兩人,遵照總理衙門指示酌議章程。而后,該二人在向署理兩江總督何璟(此時曾國藩已經去世)稟報時,卻都表露出畏難情緒。吳大廷稱“有窒礙難行者五端”[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匯編·海防檔》,甲《購買船炮》(三),903-905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馮焌光稱江南制造局目前擁有的船只“萬難強做貨船,發商承租”[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匯編·海防檔》,丙《機器局》(一),106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根據兩個的稟報,何璟六月間向總理衙門匯報意見時,也消極地建議“招商之說,似可從緩”[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匯編·海防檔》,丙《機器局》(一),95頁;《中國近代史資料匯編·海防檔》,甲《購買船炮》(三),908-909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在曾國藩剛剛去世的二月下旬,李鴻章就在給閩浙總督王凱泰的信中預言,輪船招商之事本“應由上海辦起”,但“南洋無熟悉情形、肯任大事之人,則筑室道謀,顧慮必多”[注]②④⑧ 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0冊,428、413、107-109、477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事實證明,此言果然不虛。
其實,就行動層面而言,李鴻章推進輪船招商的活動更早也更為積極。大約在同治十、十一年(1871年、1872年)之交,李鴻章便委派幕僚林士志“與廣幫眾商雇搭洋船者”籌議租賃輪船事宜,并形成了一份章程。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間,李鴻章將這份章程抄呈曾國藩,并稱“租賃輪船一節,自是經久推廣至計”。與此同時,李鴻章為了促成上海道沈秉成能夠“就巨商反復籌計,或有定局”,還吩咐津海關道陳欽“隨時函商”沈秉成。②可以說,這時的李鴻章已經向輪運業創始人的角色邁進了一大步。
在曾國藩去世之后,且南洋方面整體表現乏力的背景下,李鴻章的作用日益彰顯。這方面的第一個表現,是他全面批駁了前述吳大廷關于輪船租賃“五難”的說法,并把這些意見咨送總理衙門參閱。[注]⑥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匯編·海防檔》,甲《購買船炮》(三),906、907-908、910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另一個表現,則是他于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1872年6月20日)向朝廷上奏了《籌議制造輪船未可裁撤折》,全面闡述了發展輪船及輪運業的必要性。他從“三千余年一大變局”的高度出發,指出閩、滬船局“已成不可棄置之勢”,同時在“各口岸輪船生意已被洋商占盡”的情況下,也必須“華商自立公司”,且“為眾商所深信之員,為之領袖擔當”。④對照前述左宗棠和曾國藩的論述可以看出,李鴻章這時的認識水平明顯高出一籌。
基于上述表現,李鴻章終于贏得了決策層的充分信任。在五月十七日頒布的一道上諭中,朝廷飭令將李鴻章與左宗棠、沈葆楨等人奏折,一并交總理衙門議奏。[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22冊,104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事實上,在這份諭旨頒布之前,總理衙門業已成為李鴻章的堅強后盾。其于五月十二日致李鴻章的公函中,在完全贊同李鴻章對吳大廷批駁意見的同時,復力勸其一面“將章程悉心擬議”,一面“遴諭有心時事之員,妥實籌維”。⑥由此可見,總理衙門已將李鴻章視為辦理輪船招商事務的首要依靠了。
在中樞層大力支持下,李鴻章也加快了行動步伐。據其七月間向總理衙門匯報,他在夏間查訪到了“習知洋船蹊徑”、“熟悉南北各口岸情形”的朱其昂、朱其詔兄弟,并委派其“酌擬輪船招商章程二十條”。按李鴻章的計劃,朱其昂等“即日回滬”后,即與江海關道沈秉成、江南制造局總辦馮焌光等盡快籌議設局問題。⑦其后,沈秉成等人出于“華商輪船暢行……老關稅項大減”的擔心,使朱其昂的活動一度受阻。但李鴻章決心已定,他一面允準朱其昂“照蘇商借領練錢章程撥借二十萬串,以示信于眾商”,一面告誡沈秉成等人“勿膠成見”,從而排除了創辦輪船招商局的最后路障。⑧而當李鴻章十一月間上奏《試辦招商輪船折》時,該局已完全做好開業準備了。
三、機緣:直隸大水與輪船招商局的創辦
通過這場大辯論中表現出來的認識水平和魄力,李鴻章充分展示了自己何以能后來居上、成為輪運業建設主導者的資質。回想他同治初期在輪運問題上的消極立場,真有判若云泥之感。不過,眾所周知,李鴻章從同治六年(1867年)初至同治九年(1870年)秋接任直隸總督之前,一直忙于軍務而未嘗接觸過輪運事務。那么,他就任直督后究竟遇到了怎樣的機緣才會發生認識上的根本轉變,并在不長的時間里便成功創辦輪船招商局、開啟了洋務建設的“求富”階段呢?
很早以前便有學者注意到,在這場輪運業大辯論發生前,直隸遭遇了嚴重的水災,李鴻章也曾有過利用福州船政局兵船運輸賑米的建議。[注]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下冊,136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這的確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發現,但遺憾的是,當時的敘述戛然而止,并未探究如下問題:這場水災與輪運業大辯論的發生是否有所關聯?李鴻章這次運糧建議的起因是什么,其結果又如何?隨著這些問題的浮現,對于輪船招商局籌議過程的考察也需要放在一個更為廣闊、更為復雜的界面上了。
這場水災的確是誘發輪運業大辯論的一條重要導線。這表現在宋晉在同治十年(1871年)底發出那份奏議,就充分利用了這次水災的時機,他聲稱閩、滬船局造成的財政消耗,不啻“以有用之帑金為可緩可無之經費,以視直隸大災賑需及京城部中用款,其緩急實有天淵之別”[注]佚名輯:《晚清洋務運動事類匯鈔》,上冊,185頁,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9。,從而拋出了暫停造船、輪船租賃的建議。不過,宋晉會不會是以賑務為由而夸大其詞呢?對此疑問,看來李鴻章肯定不會贊同。在得知宋晉上奏后不久,李鴻章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間給閩浙總督王凱泰的信中,竟然也出現了以閩、滬船局為“徒添糜費”的言語。在稍后后給曾國藩的信中,李鴻章又稱宋晉所奏“亦采中外眾論而出之也”[注]⑦ 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0冊,413、325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這難免令人費解,反對停止造船的李鴻章,為什么私下里會跟宋晉一個聲調呢?顯然,這里有必要審視一下這次直隸大水及其造成的影響了。
在晚清時期,這次水災不過是一次較重的災荒而已。[注]李文海、周源:《災荒與饑饉,1840—1919》,114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但對李鴻章來說,這是他就任封疆大吏以來首次面對的嚴重災荒。這次水災起因于同治十年夏間連續高強度降水。同治十年(1871年)九月初,根據查勘結果,李鴻章向朝廷奏稱:“本年水災自嘉慶六年后數十年所未有,實較道光三年、同治六年為甚。”[注]⑥⑨ 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4冊,380-381、375、401-402、372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換句話說,直隸地區上次爆發同等強度的水災已將近七十年。而李鴻章這時用來救災的條件卻遠遜于七十年前。除搶修河工至少“需銀三十七萬兩零”⑥外,李鴻章根據一般標準,估算此次救濟災民另需“米五七十萬石、銀百余萬兩”⑦。而朝廷對于搶修河工需費,只允準先“由部庫借撥銀十萬兩”,此外則由李鴻章在直隸省內設法籌措,[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21冊,241-242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至于賑濟費用更是捉襟見肘。由此不難揣測,當李鴻章看到宋晉奏議中關于直隸賑需和造船耗費之間的緩急之論,不可能毫無同感。
當然,以李鴻章這時的見識,并不會贊成停止造船。所以,他對宋晉的更多同感,還是在宋晉關于輪船租賃的建議上,因為這非常符合他迫切發展航運業的需要。而他之所以會產生急欲發展航運業的念頭,同樣與他在這次水災期間的特殊體驗有密切關聯。概而言之,李鴻章在此次大水期間因救災物資運輸問題而碰到的困難,既促使他大大提高了關于輪運業的認識水平,又是引導他積極支持輪船招商事宜的一個重要因素。
那么,這次直隸賑務遇到了怎樣的運輸困難呢?
起初,由于賑需浩繁,而官府財力又嚴重不足,李鴻章很快發起了興勸民間捐賑的活動。不過,李鴻章鑒于直隸“著名瘠苦”,所以勸捐的主要對象是江浙紳商,⑨結果也確實沒有讓他失望,但問題在于,這次捐助活動的很大一部分必須轉化為實物形態。其一是因李鴻章商勸江浙紳商捐辦棉衣,結果南省捐助總數達28萬余件。[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5冊,180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其二是因李鴻章設法購辦賑米,在“派員分赴產米豐收之區設法購辦”外,還囑托南省紳商捐辦米石雜糧。此外,還需運送從其他地區調劑而來的賑糧。因此,從南方及其他地區運送大量棉衣和賑糧到天津,是這次賑災要面對的一項繁重任務。
可是,當時運輸問題上出現的困難遠遠超出了李鴻章等人的想象。這方面的第一個表現是洋商主導下的商輪公司不愿提供運力。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初,盛宣懷從上海致信李鴻章稱,所購賑米因“輪船多不肯裝,搭運殊難”[注]。而這些不愿合作的輪船,便大多屬于洋行。[注]無奈之余,李鴻章等人試圖利用兵輪運輸賑糧,隨之又遭遇了第二個困難,即這種做法費多益少。李鴻章自己曾打算借調滬局兵船裝運賑糧,但隨機得知此舉“誠不合算”,只好放棄了這一計劃。[注]至于利用福州船政局兵船運糧的主意其實出自王凱泰。王凱泰在福建境內代購4萬石賑米之后,即調撥兵船運往天津,結果兵船遇到了“吃水過深,不能徑達紫竹林”的問題,給接收工作造成了很多周折。[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0冊,344-345、428、371-373、428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在了解上述情況后,李鴻章于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1872年6月20日)上奏《籌議制造輪船未可裁撤折》的另一層深意也顯現出來了。如前所述,李鴻章在這里一方面指出閩、滬兩局現有輪船并不適合作為商輪,另一方面又亟亟強調必須設立華商輪運公司。對照之后可以發現,他此前在運輸賑災物資過程中所體會到的切膚之痛,恰恰與這兩個方面形成了直接對應。
李鴻章這時之所以向朝廷正式提出設立華商輪運公司的設想,繼而在不長時間內便得以開辦輪船招商局,同樣與此次賑災期間出現的機緣有關。而這一機緣最關鍵的所在,便是李鴻章對于籌建輪船招商局負責人的最終選擇。從林士志和盛宣懷先后受命擬議招商章程的情況不難看出,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之前,李鴻章很可能是計劃由自己的幕僚來推動籌辦工作的。然而,正如早先研究指出的那樣,無論是林士志還是盛宣懷,都不具備商業背景以及召集資本的能力,直到李鴻章確定朱其昂作為負責人后,輪船招商局的籌建工作才真正步入正軌。那么,李鴻章又是如何相中朱其昂的呢?
在前述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給總理衙門的匯報,以及十一月下旬給朝廷的上奏中,李鴻章都聲稱,他夏間在天津視察漕運時,查訪到承辦浙江海運事宜的朱其昂,才開始商談招商局籌建問題。而后來的研究者根據這個說法,都把李鴻章與朱其昂的最初接觸定于此時。那么,李鴻章選擇朱其昂來承擔一項如此重大的任務,難道是基于一面之緣的輕率決定嗎?實際上,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夏間之前,李鴻章對朱其昂肯定已經不再陌生。至于其間溝通和了解的渠道之一,正是同治十年水災的賑災活動,因為在那些踴躍助賑的江浙紳商中就有朱其昂。由于此次南省官紳助賑成績顯著,李鴻章向朝廷奏請獎勵,其中高度評價了朱其昂的貢獻后,并“擬請交部從優議敘。”[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5冊,182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由于這次賑務到同治十一年春間基本截止,所以朱其昂能夠被李鴻章所知,也就不可能晚于這個時候。而這樣的交集,無疑對兩人夏間的晤談形成了良好的鋪墊。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這次賑務與輪船招商局創辦之間的機緣,還有助于厘清胡光墉(即胡雪巖)與該局的關系。眾所周知,當時的胡光墉是江浙紳商群體的頭號人物,加之早先協助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的經歷,當然有資格和能力成為創建輪船招商局的得力人選。但他長期主要為左宗棠效力,在李鴻章籌建招商局的過程中始終未見發揮過多大作用,開局后也沒有成為該局的經理人。這樣一來未免令人費解,為什么李鴻章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一月下旬向朝廷聲明即將開局的奏折中,會將胡光墉置于該局第二號人物的位置上,而對先期出力甚多的林士志和盛宣懷甚至連名字都不提一下呢?
要解釋胡光墉為何能夠出現在這里,也必須從其因賑務而與李鴻章發生交集談起。就目前所見,胡光墉與李鴻章發生直接交往的記錄,正是此次直隸賑務期間。在李鴻章發起勸賑之舉后,胡光墉不僅是第一批做出積極回應的紳商,也是整個賑務中捐助力度最大的紳商。李鴻章也兩次特地為胡光墉上奏請獎。[注]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4冊,401-402、423-424、453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毫無疑問,這次賑務產生的交集,大大拉近了李鴻章與胡光墉之間的關系。也正是在此之后,李鴻章才起意延攬胡光墉加入籌辦招商局。
在朱其昂受命返回上海后不久,時天津道丁壽昌和津海關道陳欽就根據李鴻章的指示,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月間飭令朱其昂“與胡雪巖觀察合謀商辦”。稍后,李鴻章得知胡光墉表態愿意到上海與朱其昂會面,便立刻批示:“胡道(按:即胡光墉)熟悉商情,素顧大局,既與朱守晤商,當可妥商合夥。”[注]很可能是對朱、胡達成合作抱有極大信心,李鴻章才急于向朝廷奏明設局之舉,并將胡光墉的名字列入奏折。然而,李鴻章上奏后僅過了三天,就不無懊喪地告知丁壽昌,胡光墉以“所慮甚多”為辭,“似決不愿入局搭股”。[注]佚名輯:《晚清洋務運動事類匯鈔》,上冊,231-233、245頁,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9。由此可見,胡光墉的退出頗令李鴻章意外。接下來,招商局雖勉強開局,但朱其昂獨木難支,很快陷入窘境。結果不久之后,李鴻章不得不引進唐廷樞、徐潤來徹底加以改組,這已是以往所熟知的內容,無須贅述了。
本文首先表明,要圓滿解釋輪船招商局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創辦,需要運用政治經濟史、社會經濟史等復合視角,而不能拘泥于“純”經濟史視角。具體而言,李鴻章從一個與新式航運業關系淡薄的官員,轉變為推動朝廷輪船招商決策的中流砥柱式人物;同治十年之前踟躕不前的輪船招商事宜,進入次年后突然駛入了快車道,都不是純經濟因素驅動的結果。其次,要推進對洋務運動的研究,必須更為完整地把握諸多活動的動態實踐進程。就輪船招商局的創辦這個例子來說,以往論述所涉及的史實,更多時候都是為了支持自身定性分析而做出的選擇,往往忽視了很多同樣重要的史實。研究證明,如果不從招商局創辦的具體歷史進程出發,不考察洋務建設活動從“求強”轉向“求富”的發生契機,也就不可能從社會實踐中理解歷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