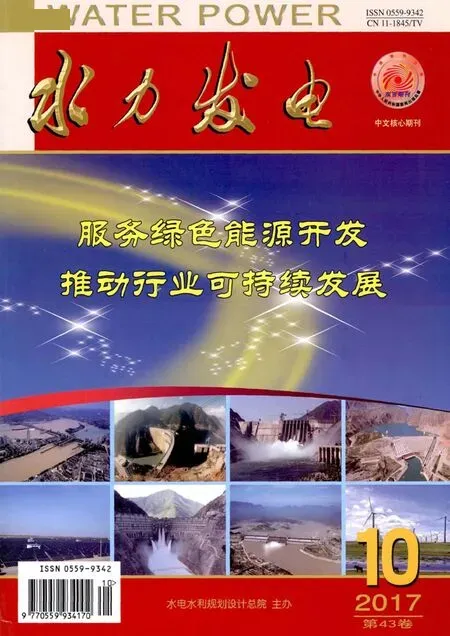基于距離熵優化HHM-ISM的大型水電項目建設期風險評價模型研究
王宏兵,鄭雪筠,李海峰
(華能瀾滄江水電股份有限公司,云南昆明650214)
0 引 言
近年來,我國水電建設的速度持續提高。截至2016年底,水電裝機達3.32億kW,約占全國發電總裝機的20.18%。預計到2020年,我國水電裝機容量將達到3.8億kW,水電開發需求巨大[1]。可以預見,在將來一段時期內,水電項目將是我國能源建設領域的重點。水電工程開發建設周期長、建設參與方眾多、投資金額巨大、風險來源多元化并相互交叉[2],表現出極強的傳遞效應[3],風險事故極易發生[4]。因此,提升水電項目風險管理水平,對保持我國水電行業的穩步發展具有現實意義。
圍繞水電工程項目風險評價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有價值的成果。王冬霞建立了水電工程風險評價指標體系,并構建了多層次灰色綜合評價模型,采用灰色逼近理想解排序法對水電工程多目標風險決策方案進行優選[5];王文飛等對水利水電項目開發與建設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風險因素進行了篩選和識別,并基于項目風險管理理論和我國水利水電工程項目實際情況,將水電項目風險管理流程分為風險識別、風險評估、風險應對及風險監控4個階段[6];李玉欽基于WBS和RBS相結合的方法建立了多準則、多層次水電工程項目風險分析模型[7];李卓玉等對水電行業的55種風險因素進行了識別和篩選,對風險的重要性進行了排序,并基于不同參與方視角對這些風險因素進行了量化分析;鐘登華等建立了風險因素多準則、多層次的ANP結構模型[8];陳志鼎等提出了基于熵權改進AHP模型的中小型水電工程施工風險評估模型[9]。以上研究多數基于風險獨立的假設前提,未考慮風險的交叉影響作用。此外,針對水電項目建設期的風險評價研究尚不多見。
本文以水電項目建設期風險評估作為研究對象,提出了水電項目建設期內的風險評價指標體系。建立了考慮風險間交叉影響的距離熵優化HHM-ISM風險評價模型,實現了風險指標影響程度的定量化評價,以黃登水電工程項目為例,對模型的適用性進行了驗證,為水電建設項目的風險管理提供決策參考。

圖1 風險評價指標體系
1 風險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等級全息建模(Hierarchical Holographic Modeling,HHM)為一種全面的思想和方法論,其作用在于從不同方面、觀點、視角和維度,捕捉并展現復雜系統的內在特征[10]。HHM理論體系中,從單一視角、以單一模型描述復雜系統及其組成部分不盡合理,應基于互相補充、協同配合的原則將其分解成子系統、部件等若干層次,每一層次均為復雜系統的某一特定的視角結構,從而實現對復雜系統形態的全面、準確描述。建設期大型水電項目是一個典型的大規模、結構復雜的系統,基于HHM多視角、多方位的思想,能夠更為準確和全面地識別出系統中存在的風險因素。
本文運用HHM理論,構建了水電工程項目3層風險評價指標體系。①第1層(目標層),即水電工程項目風險,追求項目風險值最小;②第2層(類別層),主要分為自然風險、技術風險、經濟風險、組織管理風險和社會政治風險等5類;③第3層(指標層),針對每類風險提出的對應風險指標。風險評價指標體系見圖1。
2 模型構建
2.1 模型選擇
2.1.1 解析結構模型
解析結構模型(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ISM)由華費爾(J.Warfield)提出[11],其特點是將復雜系統分解成若干的子系統要素,判斷不同要素之間是否有聯系以及如何聯系,并從信息中得到系統的完整結構,最終將系統的結構和要素間的關系用圖像形式表現出來,構成一個多級遞階模型[12]。本文將借鑒基于驅動力和依賴性的ISM算法,將大型水電項目建設期各風險因素依據其驅動力和依賴性進行歸類,從而識別出各個風險因素的內在屬性及相互之間的影響關系。
2.1.2 距離熵
用Euclid距離衡量系統中各元單位間的距離,并通過距離的比值表示系統中各元單位出現的概率,由此計算得到的熵即為距離熵[13]。距離熵的值愈大,則說明各單元在系統中出現的概率愈接近,即表示各單元與最優值之間的差異愈小,愈接近于最佳單元。因此,可以將該方法應用于不確定偏好的客觀賦權。本文引入距離熵,對風險評估過程中的權重估計進行改進,從而得到更加合理、客觀的評價結果。
2.2 構建步驟
(1)判斷各因素之間的影響和聯系。根據對各因素之間的影響和聯系的判斷結果,構建各因素間的結構自影響矩陣(Structural Self-Interaction Matrix, SSIM),即
式中,dij表示結構自影響矩陣中第i行第j列的元素;V、A、X、O表示各因素間的影響和聯系。
(2)建立初始可達矩陣(Initial Reachability Matrix)。以結構自影響矩陣為基礎,按以下轉換原則,描述各因素間兩兩相互影響關系,得到初始可達矩陣AIRM。若dij=V,則aij=1,aji=0;若dij=A,則aij=0,aji=1;若dij=X,則aij=aji=1;若dij=O,則aij=aji=0,式中,aij為初始可達矩陣中第i行第j列的元素;aji為初始可達矩陣中第j行第i列的元素。
(3)建立可達矩陣(Reachability Matrix)。可達矩陣通過矩陣形式描述有向連接圖各節點經過一定長度的通路后可到達的程度。計算方法為:基于初始可達矩陣AIRM,依據布爾矩陣的運算性質(Boolean Algebra),令A=AIRM+I。式中,I為單位矩陣。若有ARM=Ak+1=Ak≠Ak-1≠…≠A,則稱ARM為AIRM的可達矩陣。
(4)層級劃分。根據可達矩陣ARM,對其中的各因素進行整理歸納,最終將所有因素劃分為若干層級。將影響因素Vi的因素集合定義為先行集,以S(Vi)表示;將受因素Vi影響的因素集合定義為可達集,以E(Vi)表示;定義先行集和可達集的交集為共同集,表示為T(Vi)=S(Vi)∩E(Vi)。若某一因素的共同集與其先行集相同,即T(Vi)=S(Vi),則將該因素定義為ISM層級的頂端,并在下一次迭代時將其排除。不斷重復上述迭代計算過程,依次確定各ISM層級所包括的因素,直至所有因素的層級劃分全部完成。
(5)繪制解析結構圖。依據層級劃分結果,輸出包含全部因素的解析結構模型。

上述步驟流程見圖2。

圖2 模型建立流程
3 實證分析
3.1 項目背景
黃登水電站為瀾滄江上游河段的第5個梯級,位于云南省蘭坪縣境內,以發電為主,兼有防洪等綜合效益,裝機容量1 900 MW,屬一等大(Ⅰ)型工程。工程樞紐主要由擋水建筑物和地下引水發電系統組成。大壩為碾壓混凝土重力壩,最大壩高203 m。泄洪表孔、泄洪放空底孔和引水發電系統進水口均布置在壩體內。水庫總庫容15.49×108m3,調節庫容8.28×108m3,具有季調節能力。

表1 各風險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

表2 初始可達矩陣AIRM
3.2 模型求解
(1)各風險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見表1。
(2)建立初始可達矩陣。根據步驟(2),建立初始可達矩陣AIRM,見表2。
(3)建立可達矩陣。根據布爾矩陣的運算性質,計算得到可達矩陣ARM,見表3。
(4)對可達矩陣風險因素進行層次化處理,整理后的風險因素之間的關系集合見表4。
(5)構建水電工程項目風險因素的解析結構圖。通過上述步驟,實現了水電工程項目風險因素的層次化處理,18個風險因素被劃分為6個層級。風險因素解析結構模型見圖3。第1層的風險因素表示該風險因素在所有風險因素里對其他風險因素影響最多,但受其他風險因素的影響最少;第6層表示該風險因素在所有風險因素里對其他風險因素影響最少,但受其他風險因素的影響最多。L1、L2、L5、L6是單因素層級,不存在權重差異。在此,采用模糊綜合評價中常用的九階評分法對L3、L4層內的風險因素影響程度進行評分,標準化后的評分結果見表5、6。

表3 可達矩陣ARM

圖3 風險因素解析結構模型
(6)基于距離熵計算指標客觀賦權值,可得wL3={0.340,0.338,0.323};wL4={0.091,0.0907,0.0899,0.0896,0.0911,0.0953,0.0897,0.0911,0.0913,0.0904,0.0895}。令α和β均取中性值0.5,可計算得到L3和L4層加權評價集如下:GL3=(0.366,0.340,0.294);GL4=(0.092,0.082,0.100,0.102,0.094,0.073,0.091,0.080,0.080,0.094,0.112)。所有層級加權評價結果見圖3。

表4 可達矩陣ARM各風險因素之間的關系集合

表5 L3層風險因素評分結果(標準化后)
4 結果分析
L1層中僅有1個元素,即人員行為與素質S14,說明其對水電項目建設期內的其他風險因素有最為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人員行為及素質風險控制不好,將可能導致工程項目的安全、質量、進度及投資目標失控,給工程建設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對業主單位來說,首先應加強自身項目團隊建設,做到人員充足,專業配置合理,確保成員間的團結與協調,以保持團隊的效率與積極性,并維持團隊的相對穩定;其次應在承包商的選擇上嚴格把關,選擇技術能力強、商業信譽好的承包商,在現今低價中標的大潮流下,尤其要引起足夠的重視。

表6 L4層風險因素評分結果(標準化后)
L2層中僅有1個元素,即勘測不足風險S5,說明其對水電項目建設期內的其他風險因素有著較為廣泛的影響。勘測結果不夠準確,將導致工程建設中的不確定性大量增加,如設計變更數量上升,現場的組織協調工作增加,并進一步引發施工質量風險、施工事故風險和合同變更風險,甚至增大地質災害和其他突發事件風險的概率。因此,在工程建設前期應投入足夠的資源,將勘測工作做細、做實,盡量減少工程建設的不確定性,有效控制勘測不足風險。
L3層中共有3個元素,即電力市場改革風險S10(0.366)、行業政策變化風險S17(0.340)和宏觀經濟調控風險S18(0.294),說明其對水電項目建設期內的其他風險因素影響的廣泛性略低于上層的元素。這3個元素在該層級所占的權重依次降低,但差距不大,都屬于政策層面的風險,對水電項目建設的各個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水電行業眾多參與者中,對上述政策層面風險因素施加直接影響的能力極其有限,唯一能做的就是時刻關注市場和政策的現狀,提前研判其變化趨勢的各種可能情況,精心策劃、提前制定切實可行的應對措施,以盡量降低政策層面風險因素的不利影響。
L4層中共有11個元素,即自然災害風險S1(0.092)、其他突發事件風險S2(0.082)、施工質量風險S3(0.100)、施工事故風險S4(0.102)、設計變更風險S6(0.094)、物價變化風險S9(0.073)、組織協調風險S11(0.091)、合同缺陷與變更S12(0.080)、施工違約與索賠S13(0.080)、環境治理風險S15(0.094)和移民安置風險S16(0.112)。該層元素對水電項目建設期內的其他風險因素影響力居中。從各元素的影響權重來看,可以大致將這11個元素劃分個3個層級。移民安置風險S16所占權重最高,位于第1層級,說明移民問題是該層元素中影響最大的風險因素;施工事故風險S4和施工質量風險S3位于第2層級,權重略低于移民安置風險S16,這2項因素從本質上看都屬于安全方面的風險,前者為施工過程中人員、設備和設施的安全風險,后者為由于施工質量問題而導致的后續施工或運營階段人員、設備和設施的安全隱患,也說明了安全問題一直應是黃登水電站建設過程中的重中之重,不容忽視;其他8個元素的影響權重為第3層級,分別從自然災害、突發事件、設計變更、物價變化、組織協調、合同糾紛和環境治理等方面對水電項目建設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基于上述風險分析結果,建議如下:針對影響程度最大的移民安置風險S16,要超前開展庫區移民規劃設計,加強與各級政府的協調聯系,確保資金及時到位,采用短期、長期扶持安置手段相結合的措施,從而實現有效規避移民安置風險的目標;對于施工事故風險S4,可通過加強參建人員安全教育,完善安全管理規章制度,嚴抓規章制度的執行力度,強化規章制度執行情況的監督,有效管控風險;對于施工質量風險S3,則應從設計、施工、監理、設備制造、原材料采購等方面,全方位、全流程嚴格做好質量管控,確保水電項目施工質量可控、在控;而對于第3層級的各個風險因素,雖然其個體所占的權重相對較低,但其權重的總和占到該層風險因素的6成以上,仍應給予足夠的重視,提前做好風險管控,積極應對。
L5層中僅有1個元素,即投資超概風險S8,說明其對水電項目建設期內的其他風險因素的影響力較小,而受其他風險因素影響較大,若能實現對L1~L4層風險因素的有效管控,則可有效規避投資超概風險S8。
L6層中僅有1個元素,即融資風險S7,說明其對水電項目建設期內的其他風險因素的影響力最小,且受其他風險因素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對其他風險因素的有效管理是有效降低融資風險S7的前提條件。
5 結 語
本文基于HHM思想,提出了大型水電項目建設期風險評價指標體系,構建了基于距離熵優化HHM-SIM的大型水電項目風險評價模型,并以黃登水電工程為例,對模型運用進行了檢驗,檢驗結果與項目的實際狀況吻合度較高,比較真實地反映了項目的真實情況,證明了模型的有效性和實用性。
[1] 李卓玉, 唐文哲, 強茂山, 等. 水電開發風險因素研究[J]. 水力發電學報, 2013, 32(1): 293- 298.
[2] 蔡紹寬, 李玉欽, 宋洋. 基于全壽命周期的水電工程項目風險管理[J]. 天津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08, 10(4): 298- 302.
[3] 江新, 趙靜. 工程項目群的AHP-NET風險評價模型[J]. 中國安全科學學報, 2012, 22(10): 158- 163.
[4] 鄭霞忠, 湛巧玲, 陳述, 等. 基于粗糙集的水電工程施工安全評價方法[J]. 中國安全科學學報, 2011, 21(1): 82- 86.
[5] 王冬霞. 灰色系統理論用于水電項目風險管理的研究[D]. 哈爾濱: 哈爾濱工業大學, 2006.
[6] 王文飛, 黃介生. 水利水電項目風險管理淺析[J]. 中國農村水利水電, 2009(5): 82- 84, 90.
[7] 李玉欽. 基于網絡分析法(ANP)的水電工程風險分析方法研究[D]. 天津: 天津大學, 2007.
[8] 鐘登華, 蔡紹寬, 李玉欽. 基于網絡分析法(ANP)的水電工程風險分析及其應用[J]. 水力發電學報, 2008, 27(1): 11- 17.
[9] 陳志鼎, 張揚, 閆海蘭. 基于熵權和改進AHP的中小型水電工程施工風險評估模型及應用[J]. 水電能源科學, 2016, 34(7): 171- 174.
[10] 海姆斯. 風險建模、 評估和管理[M]. 胡平, 譯.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7.
[11] WARFIELD J N. Social systems: planning, policy and complexity[M].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76.
[12] Bhattacharya S, Momaya K.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of growth enablers in construction companies[J]. Singapore Management Review, 2009, 31(1): 73- 97.
[13] 管清云, 陳雪龍, 王延章. 基于距離熵的應急決策層信息融合方法[J]. 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 2015, 35(1): 216- 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