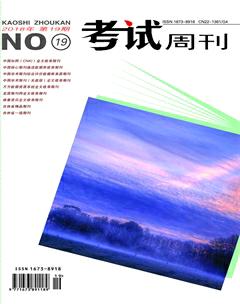《人生》的現代價值取向
陳瑞玲??
摘 要:作為當代文學作品寶庫中具有開拓性的一部力作,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自問世以來一直是文學界研究和關注的焦點,該小說主要呈現了主人公高加林在社會轉型期于城鄉之間兩次“歸來——離去——再歸來”的悲劇人生歷程。在對悲劇的展露中也蘊涵著路遙對人類社會的深刻質詢以及對個人主體的深切關懷,帶給我們一種富含現代性的啟示與價值取向。
關鍵詞:人生;文學作品;悲劇
一、 “歸來—離去—再歸來”—高加林的人生歷程
高加林的人生悲劇,源自于他在社會轉型期的農村與城市之間經歷了兩次“歸來——離去——再歸來”的宿命式人生循環。
(一) 從農民到民辦教師再到農民——第一次人生循環
《人生》的故事是從大隊書記高明樓為安排自己的兒子而下掉高加林的民辦教師職務這一情節開始的,作者顯然采取了橫截面的寫法,將高加林完整人生歷程的第一次“歸來——離去——再歸來”的輪回推到了后景。小說虛寫了這樣一個高加林過去的故事:他高中畢業后沒有考上大學,從縣城“歸來”受到了很大的精神打擊,幸而有機會到縣里的民辦學校教書,他得以從農村生活中“離去”,不用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又有時間繼續對他喜愛的文科進行學習,將來或許還能通過考試轉為正式的國家教師,前途充滿希望。可是大隊書記高明樓為了安插自己剛高中畢業的兒子,強制頂替了高加林的教師職位,高加林只得“再歸來”。他心灰意冷地回到農村,不得不像他父親一樣開始自己的農民生涯,一切雄心壯志和遠大抱負都將埋葬在那貧瘠的土地里。正當他絕望、痛苦、無助時,農村姑娘劉巧珍淳樸美麗的愛情給他帶來了心靈的慰藉,他徜徉在她的溫柔鄉里,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希望,不再以毀滅性的勞動轉移精神上的苦悶,而是逐漸對土地重新喚起了一種深厚的感情。農村的生活使他逐漸相信人的生命與土地間的深刻相連,與一飯一蔬,一衣一衫相連,與生活交織的是物質性的肌理而不是各種抽象的詩情畫意與知識概念,他深深地感受到在生他養他的黃土地中依然能開拓一片新的生活。但是,對城市向往和追求的執念依舊存活在他心中,從來不曾泯滅,每當勞動了一天后的夜晚來臨,他的內心不免重新泛起惆悵與苦悶,農村與城市在他內心深處處于一種矛盾的交織狀態。
(二) 從農民到通訊干事再到農民——第二次人生循環
正當高加林與土地的感情越來越深時,命運再次發生了轉折。高加林的叔叔退伍轉業成為地區的勞動局長,公社文教專干馬占勝為拍他的馬屁,主動走后門為高加林安排工作,高加林如同做夢一般,又從農村“離去”,回到他心心念念的縣城,成了縣委通訊組的通訊干事。這又一次的返城使高加林內心對城市產生了更加強烈的依戀與神往,他決心一定要在城市立足,占據一個位置,實現更遠大的理想和抱負。憑借著天資聰慧和勤奮努力,他很快在工作中嶄露頭角,游刃有余,甚至成為了縣城里的一顆明星。與此同時,他也收獲了城市姑娘黃亞萍的愛情。在劉巧珍與黃亞萍之間的愛情抉擇中,他無法經受得起去大城市發展的前途誘惑,權衡一切后他選擇了黃亞萍,拋棄了劉巧珍。正當一切都向他所希望的方向發展,藥材公司的副經理告發了他靠走后門參加工作的事實,頃刻之間,高加林擁有的一切都化為烏有:體面的工作,光輝的前程,連同浪漫的愛情。高加林又“歸來”到農村,可劉巧珍卻已出嫁,小說最終在德順老漢對他關于黃土地的訓誡中結束。至此,高加林完成了他第二次“歸來——離去——再歸來”的人生循環,終于他又回到了既熱愛又渴望逃離、宿命般地承載著他生命之根的黃土地。
二、 《人生》的現代價值取向
與其說路遙在80年代便在他的寫作中開始了對現代性的反思,不如說他只是在寫作體驗中通過對主人公人生中的困惑、茫然與隱忍地痛楚地書寫,表達對人類社會和個人主體的深刻質詢與反思。《人生》的價值在于它提供給后人一種現時性與永恒性相結合的現代性價值取向,一種新的思考和感受歷史價值與人生價值的方式。
(一) 對人類社會的深刻剖析
《人生》的獨特價值在于它并不以占據道德制高點的辦法來代替和掩蓋真正的歷史和現實的分析。《人生》的價值取向體現在它并不僅僅對社會變革時期的個人行為感興趣,把所有的悲劇都歸結為個人的選擇,而是把目光聚焦在變革時期社會的思想層面上,對造成人物悲劇命運的時代環境因素與民族文化心理進行了深刻剖析,因而《人生》中具有豐富的社會歷史蘊含。當文學與一個有著地域邊界的民族國家的時代發展脈絡聯系起來的時候,一個被賦予了民族精神和文化底蘊的國家形象,便在人們的想象之間清晰起來。只著眼于個人責任而忽視社會、歷史、體制乃至文化的因素,無助于我們對歷史的真正了解。
(二) 對個人主體的深切關懷
《人生》的題旨也深化著個人主體對自我的認識與價值判斷,蘊蓄著一種更具深刻意義的人性關懷與個人省思力量。高加林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耐人尋味,發人深省,“他身上匯集了多重社會矛盾與自我矛盾,蘊涵著豐富的人性內涵,從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認識生活、理解人性的參照物。”通過對高加林人生悲劇的書寫,展現出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知識青年應學會分析左右個人選擇的到底是什么,重視個人與時代之間的隱秘聯系,分析外部世界和我們的內心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為什么會發生這種變化,找尋出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歷史脈絡,從而實現自我更好的發展與完善。高加林自身也在完成著由控訴社會到解構自我的深化,歷經的痛苦成為他清醒的過程。值得注意的是,路遙在對農民知識分子的悲劇和苦難進行反思和批判的同時,還揭示了“對苦難的救贖以及在救贖中人性閃光的一面”。路遙是在農村土生土長的作家,他對農民有著強烈的情感與認同態度。這些普通農民內心的質樸與善良無不閃爍著人性的光芒,在艱難的世道中給人以相互扶持、相互慰藉的力量,也支撐著高加林們從苦難中重新振作起來,重拾生活的信心,為美好的明天而繼續奮斗。
作者簡介:
陳瑞玲,四川省成都市,武警警官學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