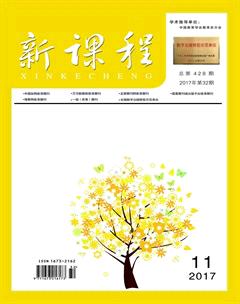淺談李清照的女性意識
太紅晨
摘 要:李清照可以說是中國文學史上唯一一位堪稱大家的女性文學家。她毫無封建女性的卑順之氣,將典雅的東方女性美提高到一個新境界。她追求男女平等,同時又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實現了輔君報國的人生價值。從李清照的個性意識、愛情意識、愛國意識三方面來論李清照的女性意識,并結合其作品,展示她的女性意識,闡述她思想深處“回歸自我”的個性特征。
關鍵詞:李清照;女性意識;個性意識;愛情意識;愛國意識
李清照出生于北宋濟南歷城(今山東濟南)大明湖旁一個書香之家,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李清照一生經歷了從美滿幸福的生活到失去丈夫的悲痛,再到國破家亡、流離失所的悲憤和凄涼,這一切造就了她獨特的人格魅力和與眾不同的女性意識。當所有的女性固守著“三綱五常”的封建禮教時,李清照作為一位封建社會中的女性,她的意識中卻充滿了叛逆性。她對外部世界的剖析和觀照,以及女性自身的內部審視和認同,引起女性“人”的掙扎和抗爭,其意義在于破壞和批判了束縛女性的封建牢獄。在封建社會“女子無才便是德”是必須恪守的信條,特別是在理學日趨盛行、封建禮教桎梏日益加強的宋代,對于一個封建官宦家庭出生的婦女,這個信條束縛得更是厲害。但李清照卻有著桀驁不羈的性格,她敢愛敢恨,大膽沖破封建社會的倫理綱常,充分顯示出一個女性的覺醒意識。
一、追求自由精神和生命氣息——朦朧的女性意識
在傳統社會中,女性缺少人格的獨立和個性的自由,被束縛于封建禮教之中,她們只能“主中饋,唯是酒食衣服之理”“國不可使預政”。但在這男權造就的荒漠上,李清照卻頑強地探索著生命的意義,捍衛著女性的權力。她的覺悟和探索,是與對自然的熱愛分不開的。正如愛默生所說:“對心智起到最早的最重要影響的是自然。”因為自然的愛好者“內在的和外在的感官,仍能真誠地相互適應”。她在自然中感應生命,形成了可貴的自由情感和獨立意識,她的詞作也因此滲透著濃厚的自由精神和生命氣息。
李清照無視傳統束縛,勇敢走出閨閣,走進大自然,她的許多詞作洋溢著如癡如醉的生命“酒”意。如:《如夢令》泛舟出游,沉醉于優美的風景,不知歸路。“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妙趣橫生的描寫,展現出一幅生動詩意的畫面,也讓人感受到那個流連于溪亭日暮的可愛少女對自然的熱愛和向往。作為才華橫溢、豪情滿懷的年輕女詞人,她追求更豐富的精神生活,向往美好開闊的精神境界,喜歡遨游山水,盡情享受大自然的美。女主人公沉醉其中,茫然不知歸路,興盡晚回,短輯輕舟,誤入藕花深處,以至驚起一灘的鷗鷺。在自然中找到真我、真性情,強烈地產生了追求個性解放和獨立的女性意識。李清照出生于書香門第,這對她文學素養的形成有重要影響。傳統儒家文化對女子的約束和她向往與現實生活中異性接觸的微妙而多層次的復雜心理,滲透在“和羞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的細節描寫中,自然靈動,充滿了性格魅力。
二、內心深處對“情”和“欲”的呼喚——走向成熟的女性意識
在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里,女性向來是男性的附屬,而女性本身真實的情感需要卻被忽略和壓抑。她敢于正視“自我”、解放“自我”,敢于以女性的身份真實地抒發女性內心深處的“情”和“欲”。這是一種大膽渴求愛情生活的熱情,這種渴望,是對人生幸福的一種合理的社會要求。如:《減字木蘭花》里,詞人呈現出了一個“妖嬈艷態”的年輕女子形象。在愛情面前,她熱情、主動、大膽。她買得一支鮮花,“云鬢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這個敢于袒露心跡,勇敢追求愛情的女子,不再僅僅站在“被看”的角度,她要成為愛的主體,循著自己的心意而愛;循著自己的心意而動。她的愛已經有了女性“自主”和“自覺”的意味,從中也透露出對自己美麗的自信。試想如果不是對自己的容顏有充分的自信,如果不是對自己的容貌充分珍愛,誰敢“云鬢斜簪”,讓郎“比并看”呢?在李清照充滿自得、自信的語氣里透露出她婚后生活的甜蜜美滿,更體現了她站在女性的立場去肯定自我價值,也以女性細膩的審美視角去欣賞女性自身的美。
三、國破家亡的憂患與責任——升華的女性意識
走向另一極,飽嘗了人生的大喜大悲。她的心靈在反差強烈的刺激中變得敏感而富于悟性。而她對于女性權力的張揚和對男性的挑戰絲毫不遜于男人。她一改傳統無知順從、安于受男權支配的女性形象,敢于獨樹一幟,挑戰大丈夫階層的價值觀。在家國破碎民族危亡之際,她寫下了“南宋衣冠少王導,北狩應悲易水寒”的句子,批判南宋士大夫階層的軟弱無能。在“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夏日絕句》)這首詞中,當權者奴顏婢膝,使人“征鞍不見邯鄲路”,李清照作為封建社會的一個女子,表現出過人的膽識,她敢怒敢言,對當時奴性的社會發出強烈的譴責之聲,表示出對政治的敏銳見解,痛心疾首地呼喚民族精神的覺醒。
綜上所述,李清照有著進步的女性意識:她追求男女平等,剛強灑脫,又不失女性之柔美;她厭惡世俗,心志高潔,卻又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實現著輔君報國的獨特的社會價值;她真誠地對待愛情婚姻,既隱忍大度,極盡為妻之道,又勇毅決絕,斷不與無恥小人茍且為伍。這位曠古才女的女性意識至今仍不乏啟迪意義。
編輯 李博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