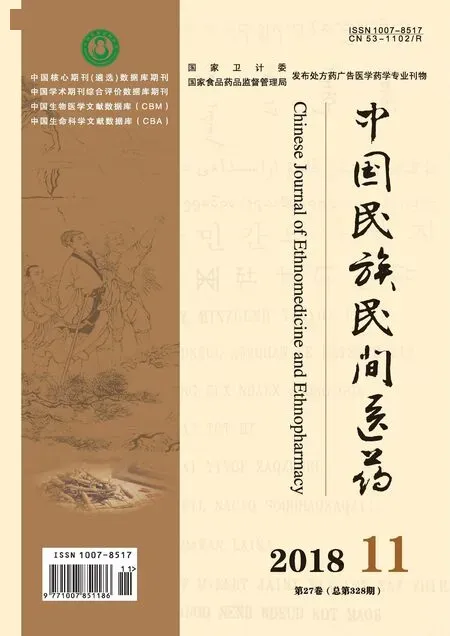中藥周期療法治療經行吐衄臨床體會
1.河南中醫藥大學第二臨床醫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2.河南省中醫院,河南 鄭州 450002
現代醫學認為經行吐衄屬于“子宮內膜異位癥”范疇,指具有生長功能的子宮內膜,在子宮被覆面以外的地方生長繁殖而形成的一種婦科疾病。現代醫學[1]對其機理研究仍存在分歧,認為子宮內膜異位癥的發病因素復雜,其機制呈多因素化,目前比較統一認可的發病理論有種植學說、血源-淋巴性散播學說、醫源性播散、遺傳學說、免疫發病學說等,其主要病理變化為異位內膜的周期性出血及周圍組織的增生、粘連、皺褶并形成瘢痕。本病的臨床表現不一,并因發病部位而異,臨床表現特征與月經周期密切相關,常見癥狀有疼痛、月經失調、不孕、性交痛等。近年來,肺部、手術瘢痕處、腸道、泌尿道、腦部等部位的內異癥的發病率亦有所上升。
1 病因病機
傅金英教授認為子宮內膜異位癥屬于“痛經”、“癥瘕”、“不孕病”、“經行吐衄”等范疇。其中經行吐衄,俗稱“倒經”、“逆經”,是指每逢經行前后或正值經期,出現有規律的吐血或衄血,經后血止[2]。其病名最初記載于《醫宗金鑒·婦科心法要訣》,而《本草綱目·百病主治藥上》記載“有行期只吐血、衄血者,或眼耳出血者,是謂逆行。”《葉氏女科證治》稱之“逆經”、“倒經”:“經不往下行,而從口鼻中出,名曰逆經”。相當于現代醫學的代償性月經[3],為臨床常見疾病之一,尤以青春期或生育期居多。歷代醫書對于經行吐衄的發病認識不一,《醫宗金鑒》云“婦女經血逆行,上為吐血、衄血,及錯行下為崩血者,皆因熱盛也,傷陰絡則下血為崩,傷陽絡則上行為吐衄也。”《沈氏女科輯要箋正·水事異常》亦云:“倒經一證,亦曰逆經,乃有升無降,倒行逆施,多由陰虛于下,陽反上逆,非重劑抑降,無以復其下行為順之常”,血熱而沖氣上逆,迫血妄行,出現吐衄;肝司血海,素性抑郁忿怒傷肝,肝郁化火,沖脈隸屬于陽明而附于肝,經行時沖氣旺盛,沖氣夾肝火上逆,血熱氣逆,灼傷血絡,迫血上溢,發為吐衄;素性陰虛,行經時陰血下溢胞宮,陰血愈虧,虛火上炎,灼傷肺絡,以致吐衄。
2 周期療法,適時治之
西醫治療該病多采用期待療法、激素療法或手術療法等,其療程長、副作用多、易復發等限制了其臨床應用。傅金英教授結合發病時臨床表現及伴隨癥狀采用辨病與辨證相結合,根據“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的原則,靈活運用中藥人工周期療法[4],其是結合月經周期中不同階段的陰陽消長、轉化規律,采用周期性用藥的一種治療方法。經后期是腎陰滋長卵泡發育的重要時期,此期血海空虛,屬于在腎氣作用下逐漸蓄積精血之期,胞宮藏而不瀉,陰長陽消呈重陰狀態,子宮內膜不斷增厚,基礎體溫呈低溫相,治法重在滋腎益陰,益氣養血,傅金英教授常選用如黃芪、黨參、炒白術、茯苓、當歸、川芎、赤芍、山萸肉、菟絲子、桑寄生、酒女貞子、旱蓮草等為基礎隨證加減;經間期陰精極盛,重陰轉陽,氤氳之期,基礎體溫上呈高溫相,沖任氣血活動顯著,治法重在活血化瘀以通暢沖任氣血,并配以溫補激發興奮腎陽,促使排卵,傅金英教授常選用黃芪、黨參、炒白術、茯苓、當歸、川芎、赤芍、桂枝、淫羊藿、巴戟天、酒萸肉等為基礎加減,但用藥需平和,以防損傷陰使陽長不利,故加入活血化瘀藥促進陰陽的轉化,使卵泡順利排出;經前期陰盛陽生漸至重陽,基礎體溫仍處于高溫相,子宮內膜達到一定厚度并處于分泌期中晚期,此時為月經來潮做好充分準備,經血滿而未溢之際,治療上當因勢利導,陰中求陽,溫腎助陽佐以滋腎益陰,亦可加入疏肝理氣藥以適應月經前的生理要求,保證月經期的順利轉化和排出,如淫羊藿、巴戟天、枸杞子、杜仲、菟絲子、續斷、桑寄生、香附、郁金、合歡皮、元胡等;月經期胞宮排出經血,瀉而不藏,是新周期開始的標志,處于“重陽轉陰”的動態變化之中,血海充盈,滿而溢下,沖任氣血變化急驟,重陽則開,子宮內膜脫落月經來潮,基礎體溫驟然下降,此期以活血養血,理氣通經,推動氣血運行,促使子宮排經下瀉,常選血府逐瘀湯加減。由于經行吐衄癥狀常伴隨月經期或月經前后出現,故傅金英教授臨床治療該病尤其注重經前期、行經期、經后期三個時期的治療,同時又兼顧經間期的調治,從不同時期分而治之,起到整體治療的效果。
3 病證結合,用藥靈活
對于子宮內膜異位癥的治療,魏紹斌等[5]采用活血化瘀治法,治療瘀血之本質。臨床上傅金英教授認為經行吐衄本質為血熱氣逆而上,肺絡受損,血溢脈外,血不歸經所致,常見證型為肝火犯肺證、肺腎陰虛證,治療上采用“熱者清之”,“逆者平之”,以清熱降火、引血下行為治則,標本同調。經前或經期初發病,出血量多,多為實熱,可加赤芍、茜草、生地榆、黃芩、黃柏等涼血止血以急則治其標;經后發病,肺腎陰虛,出血量少,多為虛熱,可加北沙參、麥冬、玉竹等滋陰潤燥;脾虛者加黃芪、黨參、白術、茯苓等健脾益氣;肝腎不足者加酒萸肉、菟絲子、桑寄生、續斷、枸杞子、秦艽、羌活、葛根等平補肝腎;帶下色黃有味者加黃柏清在下之熱等,以隨證加減為法。
4 驗案舉例
患者邢某,女,34歲,已婚。2017年9月6日初診。因“行經前流鼻血8月余”來診,患者訴近8個月來無明顯誘因,出現每逢月經來潮前3~7d左右流鼻血,量少,色鮮紅,以致畏懼洗臉,不敢觸碰鼻部,月經來潮后癥狀消失,無頭暈、鼻塞、惡心、嘔吐等癥狀,近日又出現上述癥狀。乏力,自覺面部暗斑明顯增多,腰部酸困,納食一般,眠可,二便調。舌紅,苔薄黃,脈細數。患者12歲初潮,孕1產1,2013年足月順娩一女嬰,現體健。平素月經規律,周期28~30d,經期5~7d,量少,色暗紅,無血塊,有痛經史,白帶量少,色黃,有異味,末次月經2017年8月10日。查體:形體適中,面色萎黃,面頰部有暗斑,余無特殊可載。西醫診斷:肺部內異癥待排。中醫診斷:經行吐衄,中醫辨證為氣陰虧虛證,肺絡損傷,血不循經,病本在肺腎。時值經前期,月經將至,治宜調氣活血止血,滋腎益陰,兼顧行經期以達到引血下行的目的。方藥如下:黃芪50 g,北沙參15 g,麥冬20 g,玉竹12 g,酒女貞子15 g,旱蓮草30 g,當歸15 g,川芎12 g,赤芍12 g,益母草30 g,麻黃6 g,元胡15 g,香附12 g,茯苓15 g,桔梗12 g,牛膝15 g,桂枝10 g。5劑,兩日1劑,水煎服,2次/d,1袋/次。若服藥期間月經來潮可繼服。并建議耳鼻喉科會診排除器質性病變,查血常規及凝血功能以排除血液系統疾病;囑患者調暢情志,清淡飲食。
2017年10月18日二診:專科會診及相關檢查已排除器質性病變及血液系統疾病。訴服上藥1劑后月經來潮(2017年9月7日×6d,量色質如前),末次月經:2017年10月3日×5d,量較前稍增多,色質如前,輕微痛經,帶下已無異常,訴此次月經來潮前仍有流鼻血癥狀,出血量較前明顯減少,偶有腰部及四肢酸困。面部仍有暗斑,納眠,二便調,舌紅,苔薄白,脈沉緩。此時正處經后期,治宜滋腎益陰,益氣養血,兼清虛熱。方藥如下:黃芪60 g,黨參20 g,炒白術15 g,茯苓15 g,茜草12 g,地榆15 g,當歸12 g,川芎12 g,赤芍12 g,山萸肉15 g,黃芩12 g,羌活12 g,秦艽12 g,酒女貞子15 g,旱蓮草30 g,黃柏12 g。7劑,用法同前。
2017年11月15日三診:服藥后未訴特殊不適,末次月經:2017年11月3日×5天,量可,色質如前,訴此次月經來潮前未再出現流鼻血癥狀,痛經、乏力及四肢酸困癥狀明顯減輕,面部暗斑較前減少,帶下正常,偶有腰酸,納眠可,二便調,舌紅,苔薄白,脈緩。此時正值經間期,治宜活血化瘀,溫腎益精,用藥宜平和,方藥如下:前方基處上方加枸杞子15 g,桑寄生15 g,桂枝15 g,淫羊藿30 g,巴戟天15 g。 7劑,用法同前。電話追蹤病情訴2017年12月5日月經來潮,訴經前流鼻血癥狀已痊愈,后隨訪未在復發。
按語:傅金英教授臨床治療經行吐衄,辨病與辨證相結合,陰陽辨證與臟腑辨證相結合,謹記“經前勿濫補,經后勿濫攻”之古訓,從本治之。該患者初診為經前期及月經期將至,故用血府逐瘀湯加減為主,加益氣止血,滋陰降火之黃芪、茯苓、北沙參、麥冬、玉竹,加麻黃、桂枝、元胡、香附以因勢利導,疏肝理氣,引血下行,順應經前期及行經期生理特點,加滋腎止血之二至丸以標本同治;二診乃處經后期,故用加味八珍湯加減,方中黃芪、黨參、炒白術、茯苓、黃芩、黃柏等益氣清熱之品,使補而不滯,不影響脾運,加茜草、地榆涼血止血以治其本,加滋腎益陰之酒萸肉、二至丸,使血海漸長,血歸胞宮,則鼻衄自止,加羌活、秦艽兼以治兼證;三診時正處經間期,故前方基礎之上加桂枝、淫羊藿、巴戟天 、枸杞子、桑寄生增強溫補腎陽之功,使陰陽轉化平衡,氣血調和則血自止。傅金英教授正是抓住了經行吐衄辨證的核心及不同時的發病特點和用藥特點,靈活運用中藥周期療法,出血期急則治其標兼治其本,非出血期緩則治其本兼治標,標本同治,療效明顯。
[1]謝幸.茍文麗.婦產科學[M].8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3:268-269,272-274.
[2]張玉珍.中醫婦科學[M].2版.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2:163.
[3]劉敏如.中醫婦產科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1:364.
[4]劉少麗,朱穎.中藥周期療法治療月經病體會[J].河南中醫,2013,33(12):2169-2170.
[5]魏紹斌.馮婷婷,王宇慧.從源頭治療子宮內膜異位癥的中醫思路[J].新中醫,2012.44(11):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