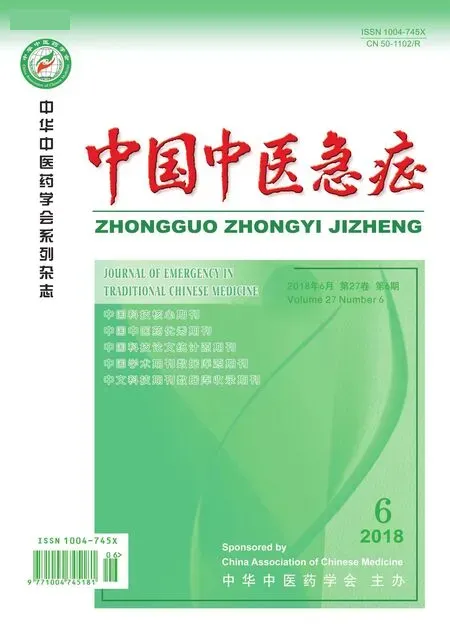膿毒癥發熱的中西醫診療臨床進展
張亞利 錢義明 錢風華 沈夢雯 胡冠宇
(1.岳陽中西醫結合醫院,上海 200437;2.上海中醫藥大學,上海 201203)
膿毒癥(Sepsis)是由感染因素導致的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SIRS)[1],如果早期不及時有效的治療,則發為 嚴 重 膿 毒 癥 (sever sepsis)、 膿 毒 性 休 克 (septic shock)。發熱則是膿毒癥最常見的癥狀[2],是構成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SIRS)的最重要組成部分,是膿毒癥病情轉歸的關鍵。雖然對于膿毒癥發熱的治療已經有了很大的突破性進展,但其膿毒癥病死率未見明顯降低,部分國家發病率仍高達8%~20%[3-4]。所以控制發熱至關重要。西醫對于此的治療確實存在缺陷,因此積極探索中醫藥防治有著廣泛的前景[5]。
1 西醫對膿毒癥發熱的研究
發熱是指機體在致熱源的作用下或各種原因引起體溫調節中樞的功能障礙時,體溫升高超過正常范圍。一方面,發熱有助于繼發人體免疫力對抗感染;另一方面控制發熱可以改善血管張力,降低耗氧量。膿毒癥發熱臨床則表現[6]:高熱(中心體溫>38.3 ℃)或低溫(中心體溫<36.0℃),炎癥反應表現為白細胞增多(白細胞計數>12×109/L),白細胞減少(白細胞計數<4×109/L)白細胞計數正常,但幼稚白細胞>10% ,血漿CRP>正常值±2個標準差,前降鈣素>正常值±2個標準差。一方面經驗性抗感染治療,盡量使用覆蓋所有可能的致病微生物(細菌、病毒、真菌)的一種或多種聯合藥物,保證充分的組織滲透濃度,對應因感染導致的發熱。另一方面,可以通過物理降溫和藥物降溫這兩類方法控制發熱。一類采取體表物理降溫,包括使用冰毯、冰袋或冰帽等,另一類降溫包括影響體溫調節的藥物和非甾體類消炎藥(NSAIDs)等。
然而早期理化依據和患者的臨床表現可能存在不匹配的現象,從而導致藥物應用的不足或過度治療[7]。Schortgen做的隨機對照試驗顯示外部冷卻控制發熱不僅減少升壓藥利用率,而且降低膿毒性休克的早期死亡率[8]。但也有不同的觀點。Chest雜志做過一期關于對膿毒性休克的高熱患者是否常規給予解熱治療社論[9]。反對者認為,膿毒性休克患者的發熱不宜經常治療。在體外和動物實驗研究表明,升高溫度對免疫功能有多種好處。雖然會引起代謝負擔,增加氧耗和心功能障礙,但這些因素對總體結果的相對重要性是難以預料的。藥物退熱的研究也沒顯示任何臨床效益。高葉等從臨床選取63例患者進行目標體溫管理研究提示過度的體溫控制可能對膿毒癥發熱患者有害,其表現在低溫管理組患者其促炎因子水平較低,而淋巴細胞亞群數量較高;高溫管理組,其血液循環改善時間和住院時間短于低溫管理組,并且抗感染治療費用也降低[10]。
2 中醫對膿毒癥發熱的認識
對于中醫來說,“膿毒癥”是一個嶄新的概念,因其有“高熱”的主要特征,將其歸屬于“傷寒”“溫病”“溫毒”“疔瘡走黃”范疇[11-12]。 病因不外乎內因和外因[13]。外因指外感六淫、疫疬、外傷等致病因素侵襲人體。膿毒癥素體雖虛,但正氣尚可與之一爭,因此多有發熱癥候。內因則為久病體虛,飲食勞倦,情志失調損傷氣血陰陽或氣、血、濕、毒等郁結壅遏而致發熱。其病機主要包括正氣不足、毒熱內蘊、瘀血阻滯和腑氣不通[14]。張巍、葉燁等分別從外感、內傷發熱的進行研究和論治,都表明了中醫藥辨證治療膿毒癥發熱的優勢[15-16]。但有關膿毒癥發熱的探討尚為數不多,且治療缺乏理論化與系統化,因此對其中醫診療需進一步研究探索。
2.1 膿毒癥發熱的辨證診療 郭任等通過對傷寒六經病變本質特點的分析,認為局限炎癥反應綜合征、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SIRS)、代償性抗炎反應綜合征(CARS)、彌散性血管內凝血(DIC)、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MODS)的本質一一對應太陽病、陽明病、少陽病、太陰病、少陰病、厥陰病。對于六經不同時期的發熱,分別選用麻黃湯、桂枝湯;白虎湯、三承氣湯;小柴胡湯;麻黃細辛附子湯;通脈四逆湯;方選黃連阿膠湯;麻黃升麻湯等[17]。余德海用小柴胡湯治療65例長期發熱的患者有效率高達92.3%,西醫對照組僅為78.5%[18]。吳冉冉等比較白虎湯、大承氣湯對不同發熱模型大鼠退熱作用顯示清、下兩種治法均能解熱但作用特點有所不同,白虎湯的解熱作用強,退熱迅速且持久[19]。
郭宏敏等認為衛分證相當于膿毒癥早期的局限的炎癥反應階段。氣分證相當于膿毒癥或SIRS期,營、血分證相當于膿毒癥后期或衰竭期。而膿毒癥發熱在其衛氣營血階段不同,辨證選方亦有異。其衛分證主選桑菊飲、銀翹散;氣分證主選白虎湯;營分證主選清營湯;血分證主選犀角地黃湯[20]。何宜榮等在涼膈散、銀翹散對早期膿毒癥炎癥因子干預作用比較研究中顯示銀翹散能抑制早期膿毒癥衛分證促炎因子IL-1β、TNF-α的釋放而減輕炎癥反應,但涼膈散則不能[21]。奚小土等利用清氣涼營湯治療膿毒癥氣營時期發熱與西醫常規治療相比有統計學意義[22]。張愛萍用犀角地黃湯加減方治療膿毒癥(毒熱內盛證)的臨床硏究,其聯合西醫治療能減輕患者的炎癥反應,改善器官灌注,改善凝血功能,縮短抗生素使用時間及住院時間[23]。
張儉等強調以“三焦”統領臟腑經絡,即手太陰肺、手少陰心經、手厥陰心包等上焦臟腑經絡者為上焦溫病;這個階段的患者病情大部分相對較輕,認為Sepsis初期,此期發熱,熱犯肺者以選桑菊飲、銀翹散;熱入心包者以選“涼開三寶”[24]。足陽明胃和足太陰脾等中焦臟腑經絡者為中焦溫病,病邪侵入中焦,多出現急性心力衰竭、缺氧、血壓增高等病情,甚至死亡,為Sepsis中期表現,陽明燥熱者以選大承氣湯、增液承氣湯,太陰濕熱者,方選三仁湯。足少陰腎、足厥陰肝、足太陽膀胱等下焦臟腑經絡者為下焦溫病,若進一步發展則出現逆傳、內陷,多表現為“內閉外脫,氣陰耗竭”。患者多表現為高熱不退、煩躁不安、四肢厥逆,多為急性肝腎功能衰竭、彌漫性血管內凝血等危重病癥,為Sepsis后期表現,此期的發熱為肝腎陰虛,虛風內動者,方選加減復脈湯、三甲復脈湯;熱結膀胱,濕阻大腸者,方選八正散、大承氣湯等。其中王亞用三仁湯治療濕熱型外感發熱 100例總有效率 97%[25]。
王今達教授等在傷寒和溫病學說的基礎上運用中醫理論解釋膿毒癥,提出“三證三法”:毒熱證與清熱解毒法;瘀血證與活血化瘀法;急性虛證與扶正固本法[26]。曹書華等在此基礎上將膿毒癥的辨證思路進一步完善,提出“四證四法”。各證都有不同程度的發熱,對其瘀血癥發熱,可用丹參注射液、血必凈注射液[27]。劉娟研究顯示血必凈對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具有顯著療效。急性虛證發熱可用生脈(參麥)注射液,參附注射液等。腑氣不通證發熱可用大黃制劑,毒熱證發熱可用熱毒清針劑,痰熱清針劑[28]。熊旭東等利用通腑瀉熱活血方治療膿毒癥熱毒熾盛證,并認為其可以抑制膿毒癥早期促炎因子的釋放,減輕炎癥反應[29]。
張淑文通過大量的臨床實踐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建立了膿毒癥、重癥膿毒癥的中醫辨證4個證型。重癥急性熱性病(重癥膿毒癥、感染性多臟器衰竭)的4個主要中醫證型:實熱證、血瘀證、腑氣不通證和厥脫證。其中熱證:實熱證、熱夾濕證、熱盛傷陰證張老擅用復方清熱顆粒加減治療。研究表明復方清熱顆粒聯合西藥治療膿毒癥、急性肺炎患者療效確切,可縮短體溫降至正常的天數,另有其他醫者運用應用針刺、放血及拔灌等治療方法進行降溫處理,也得到了較好的效果[30]。
3 現況與展望
近年來,中醫藥防治Sepsis的研究方興未艾,從清除內毒素、拮抗炎癥反應、提高機體免疫力、保護器官功能等多途徑、多環節進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充分展現了中醫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的優勢,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如在膿毒癥發熱等癥狀上始終沒有較好的控制辦法,原因在于膿毒癥病因病機缺乏準確的認識,尤其是辨證分析需進一步規范化。膿毒癥患者發熱有虛實之別,亦有虛實夾雜,臨床治療中多按照實熱內熾、濕熱蘊結、邪郁少陽、陰虛內熱、氣虛發熱等證型論治。這體現了中醫對膿毒癥發熱治療的辨證求因,審因論治。發熱控制不良寓意著患者的病情惡化,須盡快辨析病因,明確治法,減輕對機體的損害。因此,我們研究者應該進一步加強對Sepsis本質的認識;運用有效的辨證思維,在中醫學理論的指導下,優選組方配伍,開發出切實有效的防治診療,從而降低Sepsis發病率和病死率,提高我國危重病的救治水平。基于此,我課題組自2008年以來致力于中西醫結合治療膿毒癥的研究,積累了較為豐富的臨床診療經驗。研究表明膿毒癥炎癥反應劇烈時期氣分證較明顯,并認為“把好氣分關”是防治溫病的關鍵[31],以升降散加減對癥治療,對控制發熱等癥狀有較好療效。
[1]Singer M,Deutschman CS,Seymour CW,et al.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definitions for sepsis and septic shock(Sep-sis-3)[J].JAMA,2016,315(8):801.
[2]王超,李秦,徐定華,等.410例重癥膿毒癥患者中醫證候的臨床分析[J].中國中醫急癥,2014,23(7):1242-1244.
[3]Dellinger RP,Levy MM,Rhodes A,et al.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for manage-ment of severe sepsis and septic shock: 2012[J].CritCare Med,2013,41(2):580-637.
[4]Konrad Reinhart.Rev Bras Ter Intensiva[J].JAMA,2013,25(1):3-5.
[5]趙國楨,郭玉紅,李博,等.中醫藥防治膿毒癥的研究進展[J].中國中藥雜志,2017,63(8):1423-1429.
[6]中華醫學會重癥醫學分會.中國嚴重膿毒癥/膿毒性休克治療指南 (2014)[J].中華危重病急救醫學,2015,27(6):401-426.
[7]黃偉,萬獻堯.2013版嚴重全身性感染和感染性休克處理指南解讀[J].中國實用內科雜志,2013,33(11):866-868.
[8]Schortgen F,Clabult K,Katsahian S,et al.Fever control using external cooling in septic shock: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12,185(10):1088-1095.
[9]Drewry AM,Hotchkiss RS.Counterpoint:Should antipyretic therapy be given rountinely to febrile patients in septic shock NO[J].Chest,2013,144(4):1098-1098,1101-1103.
[10]高葉.目標性體溫管理在膿毒癥發熱患者臨床應用中的研究[D].蘇州:蘇州大學,2016.
[11]李志軍.“三證三法”及“菌毒炎并治”治療膿毒癥的研究進展[J].中國中西醫結合外科雜志,2012,19(6):553-554.
[12]林孟柯.膿毒癥急性腎損傷的中醫證候特征及危險因素回顧性研究[D].北京:北京中醫藥大學,2016.
[13]羅天扶.膿毒癥肝功能因素與中醫證候分析及臨床預后相關性研究[D].廣州:廣州中醫藥大學,2014.
[14]何煜舟,汪云開,祝晨,等.中醫辨證治療膿毒癥臨床研究[J].中國中醫急癥,2012,21(4):524-525.
[15]張巍,蘇麗萍.中醫辯證治療外感發熱的臨床療效研究[J].成都醫學院學報,2016,11(05):613-615.
[16]葉燁,周仙仕.從內傷發熱論治膿毒癥[J].新中醫,2016,48(8):3-5.
[17]郭任.傷寒六經病變本質探究[J].河南中醫,2009,34(3):221-223.
[18]余德海.小柴胡湯治療長期發熱65例[J].中國中醫藥現代遠程教育,2016,14(7):93-94.
[19]吳冉冉,王欣.白虎湯、大承氣湯對不同發熱模型大鼠退熱作用實驗研究[J].山東中醫雜志,2012,31(7):506-508.
[20]郭宏敏.衛氣營血辨證與老年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客觀指標的相關性研究[A].中華中醫藥學會.第十次中醫藥防治老年病學術交流會論文集[C].中華中醫藥學會:2012:3.
[21]何宜榮,趙國榮,肖碧躍,等.涼膈散、銀翹散對早期膿毒癥炎癥因子干預作用比較研究[J].湖南中醫藥大學學報,2016,36(12):7-10.
[22]奚小土,鐘世杰,黃宏強,等.清氣涼營湯治療膿毒癥30例 APACHEⅢ評分的臨床觀察[J].新中醫,2009,41(8):61-62.
[23]張愛萍.犀角地黃湯加減方治療膿毒癥(毒熱內盛證)的臨床研究[D].南京:南京中醫藥大學,2015.
[24]張儉,龔虹,孔祥照.從三焦辨證探討膿毒癥傳變規律及其治療[J].新中醫,2013,45(8):211-213.
[25]王亞.三仁湯治療濕熱型外感發熱100例[J].中國實用醫藥,2010,5(3):176.
[26]葉勇.“三證三法”的整體觀與運動觀.云南省中醫藥學會、云南省中西醫結合學會、云南省針灸學會、云南省民族民間醫藥學會.首屆蘭茂中醫藥發展學術論壇暨云南省中醫藥界2014′學術年會論文匯編[C].云南省中醫藥學會、云南省中西醫結合學會、云南省針灸學會、云南省民族民間醫藥學會,2014:5.
[27]曹書華,王今達,李銀平.從“菌毒并治”到“四證四法”——關于中西醫結合治療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辨證思路的深入與完善[J].中國危重病急救醫學,2005,17(11):7-9.
[28]劉娟.血必凈治療膿毒癥40例臨床體會[J].深圳中西醫結合雜志,2016,26(18):68-69.
[29]王倩,李淑芳,熊旭東.通腑瀉熱活血方對膿毒癥熱毒熾盛證患者炎性因子的影響[J].中國中醫急癥,2011,20(7):1048-1049,1078.
[30]杜琨,王超.張淑文教授診治膿毒癥、重癥膿毒癥學術思想[J].中國中醫藥現代遠程教育,2015,14(19):30-32.
[31]高斌,李仁柱,朱亮,等.升降散對初期膿毒癥患者中醫癥候的干預研究[J].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2009,11(12):1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