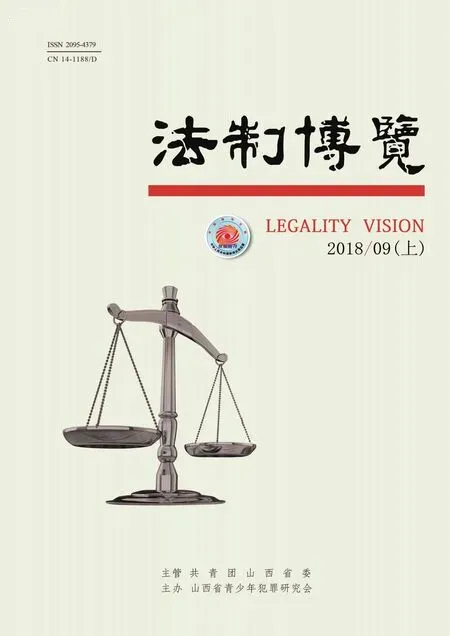論執(zhí)行擔保與民事保證的共同保證認定
章岳龍
杭州經濟技術開發(fā)區(qū)人民法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案例簡介
2011年7月26日,借款人姚某某向翁某某借款400000元,通融公司作為保證人。2012年1月21日,姚某某再次向翁某某借款200000元。2012年4月10日,姚某某再次向翁某某借款500000元,陳某作為保證人。因姚某某未履行還款義務,翁某某于2012年5月3日對姚某某、陳某、通融公司提起訴訟。該案在審理中,各方當事人達成協(xié)議,并由法院出具調解書,姚某某在欠款范圍內承擔還款責任,陳某、通融公司在各自擔保范圍內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嗣后,姚某某、陳某、通融公司均未能按照調解書規(guī)定的時間履行還款義務。隨即,翁某某向法院申請強制執(zhí)行。在執(zhí)行中,2012年5月20日,董某某本人以及作為意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其公司為姚某某所欠債務提供執(zhí)行擔保。后意達公司分別于2012年8月17日、9月4日向翁某某支付800000元和438078元,翁某某出具收條二張。因被告姚某某并未履行還款義務。意達公司于2012年9月24日訴來法院,要求被告姚某某、陳某、通融公司承擔相應的責任。
二、執(zhí)行擔保人在執(zhí)行過程中的清償行為的認定
意達公司認為其基于為翁某某提供執(zhí)行擔保,因翁某某未履行還款義務,意達公司無奈下履行擔保責任,其承擔的系保證責任。而陳某認為意達公司的行為應屬于債務加入。債務加入和保證均是第三人為債權人實現(xiàn)其債權提供另外保障,都屬于人保范疇,尤其表現(xiàn)在債務加入與連帶責任保證的比較上,兩者的外在表征和責任承擔更為相似。史尚寬先生甚至將債務加入行為歸納為隱蔽的保證行為。在司法實踐中,此相似性甚至造成了兩者認定上的困難。最高法民二庭于2006年發(fā)布的《民商事審判若干疑難問題》中指出:“認定一個意思表示屬于債務加入還是屬于保證應根據(jù)實務中案件情況的不同而進行認定。如果第三人在做出意思表示時表現(xiàn)出較為明顯的保證的意思,則可以認定為保證;如果沒有,如果從該意思表示中未能體現(xiàn)出較為明顯的保證的意思表示,則可以從保護債權人的利益的立法目的出發(fā)將其認定為債務加入。”從這個意見中可以看出,司法實踐中,二者的區(qū)分主要在于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債務加入有約定從約定,無約定或約定不明的,結合案件實際情況以及合同目的等情形來推定各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
具體到本案中,保證與債務加入的區(qū)分應屬明顯。理由如下:第一,保證要求當事人有明確的意思表示,不能適用推定,從合同法的角度看,如無明確證據(jù)表明的情形,均無法認定保證;而債務加入有時無需第三人有明確的意思表示,有些情形下可以結合案件當時狀況來加以確定。本案中姚某某因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而被司法拘留,此時董某某及意達公司為了解除其拘留措施、暫緩執(zhí)行而向法院提出愿意為姚某某提供執(zhí)行擔保,在征得申請執(zhí)行人翁某某的同意后,法院提前解除了姚某某的拘留,并告知翁某某暫緩執(zhí)行的期限。為了延緩法院的判決執(zhí)行期,意達公司作為保證人向法院提供擔保,經法院的審查確認,法院作出暫緩執(zhí)行的決定。在整個過程中,意達公司及董某某均無加入到姚某某的在先債務中去、作為主債務人之一為自己的債務向翁某某進行清償?shù)囊馑急硎尽8鶕?jù)上述事實可知,意達公司為案涉?zhèn)鶆仗峁┍WC的意思表示明確。第二,保證責任的承擔必須在主債務履行期屆滿后才會發(fā)生,而債務加入的期限卻不受原債務人的履行期限之約束。本案意達公司承擔的是從債務,依附于翁某某的主債務存在。在法院給予的暫緩執(zhí)行期限屆滿后,在翁某某并未履行還款義務的前提下,意達公司分兩期清償了全部債務。第三,根據(jù)學界的利益之界定標準來看。史尚寬先生認為,“在實際上為保證契約抑為并存的債務加入,應斟酌具體的情事,尤其契約之目的定之。當事人之意思不明時,其偏為原債務人之利益而為承擔行為者,可認為保證。承擔人有直接及實際之利益而為之者,可認為并存的債務加入。”本案中,雖然陳某主張翁某某與意達公司有債權債務關系,但并未提供相應證據(jù)表明翁某某與意達公司、董國明之間存在重大經濟利益關系,并不能推斷出意達公司、董國明具有債務加入的意思表示。因此,本案中一、二審法院判定意達公司清償?shù)男袨閼獙儆谄渎男斜WC責任的行為的論斷正確。
三、執(zhí)行擔保行為與原保證行為能否構成共同保證
通說認為,共同保證是指數(shù)人對同一債務的履行提供的保證。我們根據(jù)各保證人之間有無成立共同保證的意思,可以將之分為意定共同保證和法定共同保證。意定共同保證是指數(shù)個保證人共同簽訂保證合同或者數(shù)個保證人分別簽訂保證合同但自愿構成共同保證;而法定共同保證是指數(shù)各保證人分別簽訂保證合同且無共同成立保證的意思聯(lián)系,而依法確認其共同保證關系。
民事執(zhí)行擔保具有公權與私權行使的雙重屬性,與一般民事?lián)km然在法律性質上有所區(qū)別,但從法律后果上應是一致的。在暫緩執(zhí)行期限屆滿后,若債務人最終未履行還款責任,則執(zhí)行擔保人與其他連帶責任保證人一樣,最終亦是以自己的財產履行其保證責任。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九條的規(guī)定,兩個以上保證人對同一債務同時或者分別提供保證時,各保證人與債權人沒有約定保證份額的,應當認定為連帶共同保證。從上述規(guī)定可以看出,提供保證的時間先后,以及各保證人間是否有意思聯(lián)絡,并不影響共同保證的成立。具體到本案,保證人陳某、通融公司在其各自保證范圍內與執(zhí)行擔保人意達公司、董某某與意達公司之間并未明確約定各自保證份額的,應認定為連帶共同保證。
四、共同保證人之間的責任分擔
共同保證一旦成立,即產生兩方面的法律關系:一是共同保證人之間的內部法律關系;另一是共同保證人與債權人之間的外部法律關系。存在數(shù)個保證人的情形下,如其中某一位保證人履行了保證責任,主債務隨即消滅,并且意味著其他保證法律關系亦隨之消滅,其他保證人的保證責任也被免除。
隨之產生的問題是,承擔了保證責任的保證人的權利如何保護?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后,是否可以要求其他保證人來分擔其履行的保證債務?理論上爭議的焦點也就在于此。反對保證人之間具有內部求償權的學者認為,各個保證人之間并無共同保證的意思表示,承認保證人之間的內部求償關系欠缺法理基礎;各自獨立的保證人的初衷就在于承擔保證責任,彼此之間并無連帶負責及向其他保證人求償?shù)囊馑迹残缘亓畋WC人實際承擔保證責任后再向其他保證人追償,有違意思自治的原則。對此,筆者認為,雖然各保證人之間無共同保證的意思表示,從表面上看,各方確實不存在任何聯(lián)系,但各方均為實現(xiàn)“為同一債務提供保證”的終極目標,實際上已經使得各方之間存在實際聯(lián)系,而且因為有數(shù)人為同一債務提供保證時,能夠分散單個保證人所承擔的保證責任的風險,每一位保證人最終所承擔的保證責任均小于其在提供保證時所需承擔的保證責任,因此在保證人得知還有其他保證人時,承認保證人內部求償關系其實是符合每一位保證人的真實意思表示。
本案中,意達公司在債務人未履行的情況下,分二期向債權人履行了全部債務,從而導致主債務消滅,并且意達公司在履行過程中并無過錯。因此,在意達公司履行保證責任后,享有向主債務人翁某某、保證人陳某、董某某、通融公司求償?shù)臋嗬9室弧⒍彿ㄔ焊鶕?j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0條第2款:“連帶共同保證的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后,向債務人不能追償?shù)牟糠郑筛鬟B帶保證人按其內部約定的比例分擔。沒有約定的,平均分擔”的規(guī)定,判定陳某、通融公司在其保證責任范圍內平均分擔保證責任的論斷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