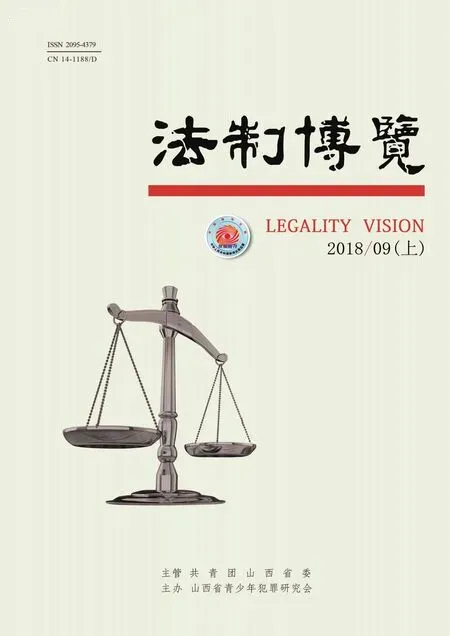論防衛過當之界定
況優優 馬雪萌
西北大學法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7
一、防衛過當的成立條件
我國刑法第20條第2款中對防衛限度的認定是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應負刑事責任的行為,對于明顯超過的認定主要有:
首先,必須是針對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行為進行防衛,侵害行為對權利可能或者已經造成危害時,行為人不得已進行防衛避免或減小損失。其次,不法侵害的性質與防衛所保護的利益不成正比,所采用的防衛手段遠遠超出了侵害所能造成的后果。最后,行為人主觀上是間接故意,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造成重大損失。
二、對于“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理解
首先,對“明顯”一詞的理解。“明顯”不是一個嚴謹的刑法術語,法官在審理案件中對于“明顯”沒有一個明確的參考標準,自由裁量權較大。在實踐中只有能夠被清楚、容易地認定為超過了必要限度時,才屬于防衛過當。具體而言,有以下情形:第一,防衛人為保護微小利益而損害與該利益不成正比的不法侵害人的利益。第二,對于不法侵害行為是否存在、是否結束判斷有誤,針對的是不具有緊迫性的侵害行為。第三,不法侵害行為性質輕微,所保護的利益較小,防衛人用一般手段即可制止卻采用了較強的手段。筆者認為,現實中侵害行為往往是突然發生的,防衛者處于較為被動的、危急的地位,因此很難要求防衛者在抵抗不法侵害時還要考慮到會不會造成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重大損害。必要限度,只是一種價值取向,實踐中難以確定一個具體統一的標準,因此就有可能導致法律適用的不公平。
其次,“對重大損害”的判斷,我國理論界和實務界對重大損失的認定有較大爭議。對防衛者,法律賦予其面對不法侵害時采取一定限度的手段保護自身、他人或國家的利益的權利,但是對于不法侵害者,防衛者造成怎樣的損害是重大損失?筆者認為重大損害不僅包括人身損害,還包括財產方面的損害。此外,“重傷”是“重大損失”的一種表現,相對于死亡而言,“重傷”應當屬于造成“重大損失”的最低標準。因此,在認定防衛行為是否造成重大損害時,應當以防衛行為給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傷”為最低起點。因此,將重大財產損失、重傷和死亡作為重大損害判斷的依據較為合理。
最后,想要弄清防衛過當與必要限度之間的關系,就必須把握明顯超過和重大損害之間的關系,學界主要有四種觀點:
第一種“并列說”,認定正當防衛限度條件時,將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和重大損害二者并列,處于同等地位,缺一不可。
第二種“包容說”,主張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包含重大損害,重大損害是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必然結果。
第三種“交叉說”,認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可能發生重大的損害,也可能只導致一般損害;而重大損害可能是因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引起的,也可能是因為沒有超過必要限度引起的。二者呈現一種交叉關系。①
第四種“因果說”,認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與“造成重大損害”,認為二者缺一不可,前者是后者的原因,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結果。
前三種觀點容易產生行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但沒有產生重大損害的后果,或者產生重大受損害的后果,但是沒有超過必要限度這兩種情況,若秉持這種觀點判斷就不構成防衛過當。“因果說”卻解決了這樣的疑惑,揭示出了二者就是因果系,同時具備并有機統一于防衛過當中,防衛行為只有在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同時又造成重大損害的,才構成防衛過當。因此,筆者贊同因果說的觀點。
三、結語
防衛過當制度是對不法侵害人利益的保護,是對防衛人權利的限制,體現了刑法平等原則和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筆者認為防衛者利益應當大于不法侵害者的利益:首先,防衛者是以正當的理由來排除不法侵害者的違法行為,對防衛過當的界定要最大限度的保障防衛人的利益。其次,在面對緊迫的不法侵害時,不能要求防衛人還能冷靜周全的考慮采用何種手段、達成什么后果,要以一般人的反應為標準,不可在法律上過分苛刻要求防衛人,要避免唯結果論,加重防衛人的責任。最后,應該符合正當防衛制度的立法本意,鼓勵公民進行自力救濟,敢于保護自己的權力、見義勇為。
[ 注 釋 ]
①陳正云.論準確認定和把握防衛過當的標準[J].中國刑事法雜志,1999(3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