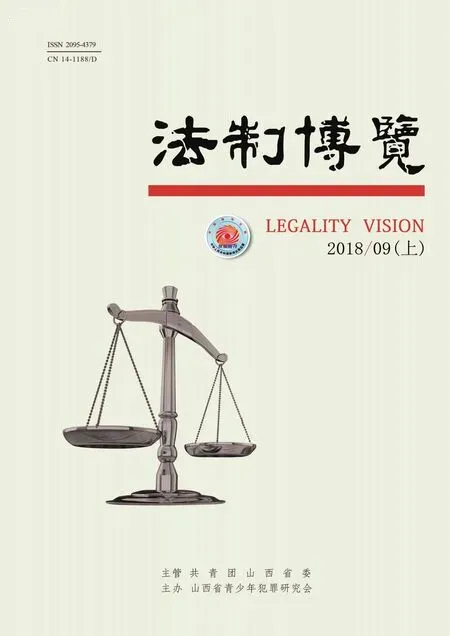再論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適用與完善
李曉瑜
中共鄭州市委黨校,河南 鄭州 450042
2016年時任最高院院長周強提出要用“兩到三年時間破解執行難”,之后全國法院持續開展多種執行專項行動,嚴厲打擊拒執犯罪。2018年作為攻堅最后一年,也是決勝之年,有必要對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適用與完善進行再反思。
一、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立法紕漏
(一)入罪認定標準不夠明確
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是典型的不作為犯罪。被執行人的作為義務源自于已經生效的判決、裁定,執行義務人“有能力執行卻拒不執行,情節嚴重”是構成拒執罪的必備客觀要件,但對于該條款的實質內涵、時間節點的把握,實踐中理解不一。
首先,如何判斷執行義務人是否“有能力執行”。執行義務人的財產狀況并非一成不變,有可能隨時間、經營風險等客觀因素的變動而變動。例如作為執行義務來源的原判決、裁定書生效之后,執行義務人占有或實際控制資產200萬元,應履行債務標的100萬元,但在拒執罪立案前或訴訟過程中,因投資、經營風險、家庭重大變故或增加其他債權人的強制執行申請,被執行人原有資產發生大幅貶值,執行義務人實際占有資產只有5萬元,排除維持家庭生活必需資產外,近乎破產的義務人是否仍屬于“有能力執行”?判斷“有能力”應該以原判決、裁定書生效時間為起點,還是以拒執罪立案時間為起點?
其次,“拒不執行”應以何時為計算起點。是以原判決、裁定書的生效時間為起點,還是以申請執行人提起強制執行申請之日為起點,抑或以法院執行局發出執行通知書之日為起點?1998年最高院司法解釋曾規定,“法院發出執行通知之日”即視為被執行人拒不執行之起點,但此解釋僅明確了被執行人的拒執時間起點,對于協助執行人、擔保人等其他執行義務人拒執的時間起點,卻并無明確規定,當以“法院發出執行通知之日”還是“收到協助執行通知之日”為起算點?同理,“拒不執行”行為的完成,當以送達執行通知書為準,還是以發現執行義務人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時為準,甚或以執行部門采取強制性措施之日為完成標志呢?縱覽目前關于拒執罪的刑事法律法規,均無明示。
再次,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屬于行為犯,且以“情節嚴重”為既遂標準。關于“情節嚴重”,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專門立法解釋中將其明確為五種情形,其中前四種均指向“拒不執行,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但這些列舉性規定仍不免落于太過抽象的窠臼,“情節特別嚴重”與“情節嚴重”的實質區別究竟為何?“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到底是致使原生效判決、裁定永久無法執行,還是致使原生效判決、裁定暫時無法執行?是致使原判決、裁定全部不能執行,還是影響部分判決、裁定內容不能執行?實踐中爭議頗大。
(二)犯罪主體、對象覆蓋不全
依據《刑法》第313條和最高院《關于審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拒執罪犯罪主體指向被執行人、協助執行義務人、擔保人等負有執行義務的自然人和單位,犯罪對象指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執行內容的生效判決、裁定。
但在實踐中,除上述負有執行義務或協助執行義務的主體外,執行義務人的親友、下屬員工(單位犯罪中)等案外人基于私情、義氣等以圍堵或以暴力方式阻撓執行,或積極幫助義務人逃避執行的,其不法行為有可能同時觸犯妨害公務罪、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非法處置扣押凍結財產罪等多罪名,對此想象競合犯,是否一概排除在拒執罪之外?
作為具有執行內容的生效法律文書,除了判決、裁定之外,仲裁裁決、民事調解書、行政調解書、公證債權文書、訴訟保全裁定、先予執行裁定、支付令等都可以作為執行依據。其中民事調解書、行政調解書同樣可以確定執行內容,如離婚調解書中關于財產分割、夫妻債權債務的劃分。當申請執行人以執行生效調解書提起執行程序后,該生效調解書是否可以直接作為認定拒執罪的對象?
二、適用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程序困境
(一)訴訟啟動遭遇尷尬
刑法對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在程序上的最大修改莫過于設置了自訴啟動機制。相較于原來的普通公訴程序,自訴程序更為靈活、簡便,簡易程序的運用明顯增多,申請執行人的適法主動性也得到極大提高。
但在實踐中,自訴人舉證范圍、舉證能力依然受到很大限制。由于社會征信體系的不完善,據以判斷執行義務人執行能力的財產狀況等信息,毋論自訴人很難自行獲得,即使是法院自身依職權調查取證也很難獨立完成。自訴人能提供的多為犯罪線索,與舉證責任中要求的舉證能力、舉證范圍還有很大差距,舉證負擔仍然較重。
公訴程序中,對拒執罪的追訴始于法院發現案情,經由公安機關偵查取證、檢察院審查起訴,最終又回到法院審理裁判。可以說法院在整個公訴程序中既是控告者、啟動者,又是裁判者、證明人,同時還是終結者和執行者,身份多重且相互矛盾。不論是程序正義還是實體正義,法院都很難擺脫有罪推定的責難。
(二)公檢法配合不到位
為切實破解執行難,各地公檢法陸續建立聯席會議制度或三方協作機制,力爭統一辦案標準,形成打擊合力,但該配合協調機制的落實尚不完全令人滿意。突出的表現就是三機關在拒執罪的立案標準上寬嚴不一。公安機關接收到法院移送的案件材料后,通常會考慮檢察院是否提起公訴這一因素,偵查期限長、進度緩慢。對于不符合公安機關立案標準的案件,退卷的同時卻又甚少出具《不予立案通知書》,這在嚴把拒執罪公訴啟動關的同時,卻也客觀上加大了申請執行人啟動自訴程序的難度,使得拒執罪的訴訟進入立案難的怪圈。
三、完善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具體建議
(一)科學界定時間節點,細化犯罪認定標準
對于執行義務人是否具備執行能力、是否如實履行執行義務的判斷,從時間節點上看,建議在詳細區分被執行人和協助執行義務人的基礎上分別確定。對于被執行人,應該以原判決、裁定書的生效時間為起點;對于協助執行義務人或第三人則以接到法院協助執行通知書之日為起點。從拒不執行的實體標準上看,要應當重點結合查控到的財產的可供執行性、經濟性、非人身性等特征綜合考量。
對于非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法定犯罪主體的案外人而言,其妨害強制執行的犯罪行為,應當嚴格依照想象競合犯的處斷原則進行處理,不宜輕易擴大犯罪主體范圍。而關于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犯罪對象,則需要認真辨析。依據罪刑法定原則,調解書本身不是本罪犯罪對象,只有在進入法定執行程序并經法院依程序審查認定為裁定依據后,再行根據該調解書作出的判決、裁定才具備拒執罪犯罪對象的實質。
(二)凝聚各方思想共識,動態銜接追訴機制
加緊完善社會誠信體系,充分發揮失信聯動懲戒機制和拒執罪的懲治、預防作用。充分銜接公檢法三部門在打擊拒執犯罪中的辦案流程、立案標準,強化配合協調和可操作性,合理設定自訴人舉證范圍,積極打造刑事公訴、申請人自訴程序的有效對接機制。強化法院內部審判部門與執行部門在不同啟動程序下對案件受理標準、證據收集舉證、移送接收程序等多環節溝通,嚴格把握公訴、自訴程序證據標準,積極引導自訴程序的良性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