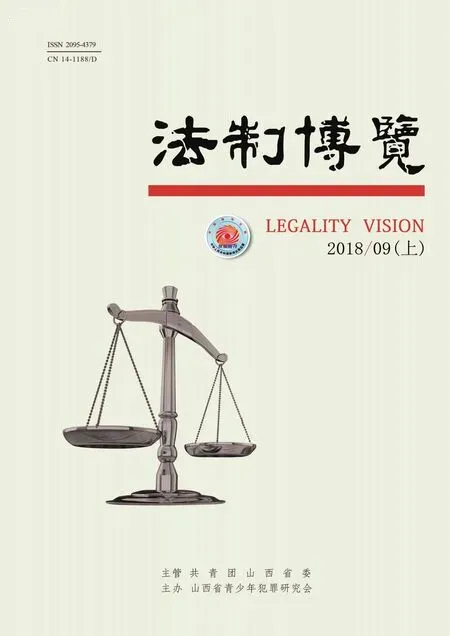論人工智能產出物的知識產權歸屬
李文文
上海政法學院,上海 201701
一、人工智能產出物的知識產權歸屬問題產生背景
2017年7月8日國務院發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正式將人工智能列為國家發展戰略,人工智能在國際競爭、經濟發展、社會建設等方面讓國家迎接挑戰的同時也帶來了無限機遇。
人工智能,英文縮寫為AI,是一種高度精密的數據系統,一方面作為人類探索自然、實踐科學的技術成果,另一方面也利用其內部深奧復雜的算法程序將人類社會的效率價值發揮到極致。
二、探究目的及意義
本文探究人工智能產出物知識產權的歸屬目的在于明確人工智能機器在知識產權法的法律地位。隨著科學領域對人工智能的不斷鉆研開發,人工智能正在向公眾生活滲透并終將與之融為一體,實現信息科技社會向人工智能社會的轉變。遙想2000年摩托羅拉公司生產的名為天拓A6188的手機,它是全球第一部具有觸摸屏的PDA手機,“智能”技術的大門開始向人類敞開。短短幾年,“人工”與“智能”相結合,賦予智能設備人的意識和思維,冰冷的機械人性化,即實現智能化的更高層次,我們無法將人工智能斷言成為智能化的頂級高度,因為對科學世界的預知永遠持于“猜想”階段。由于人工智能本身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可控性,伴隨而來的一切不確定性和風險性也不容忽視。明確這一新新事物的法律地位,無疑有利于維護人類社會的穩定與科技發展。
三、人工智能產出物的知識產權歸屬方向之分析
(一)從權能屬性論人工智能產出物的知識產權歸屬
語音識別、影像識別、機器人客戶服務屢見不鮮,人工智能通過模擬人的思維行為,利用精密的算法可以實現人類目標完成的工作,甚至超越人類的智力水平能達到的高度。人工智能市場在我國正處于半開放的狀態,當科學再跨進一步,人工智能與公眾日常交融便是一發不可收,制定并完善人工智能領域的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于人工智能的產出物能否設定知識產權,這一點尚無爭議,答案是肯定的。但最終其產出物的知識產權之于何處,目前理論界莫衷一是,但本文認為,人工智能是一種智能勞動力,其本身即是人類追求安全、效率等價值的產物,作為工具性的存在,其產出物的知識產權也當屬于現行知識產權法上的權利主體,即歸于人工智能工具的所有權人或其他現實世界的權利主體。
知識產權是“人們基于自己智力活動創造的成果所享有的權利”①,知識產權的客體為無形的智力成果。人工智能的數據資源與算法程序系統均為人為注入,對于其產出物,歸根到底是人類利用人工智能機器的加工物。產出物的知識產權體現為人身屬性與財產屬性相結合,知識產權的權能價值在于保護創造者合法權益的同時鼓勵創新,鼓勵知識的傳播,權利本位的立法指導思想下應以人權保護為中心。法律調整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知識產權作為重要的法律分支領域,更應強調的是人(包括法人)作為權利主體的地位。知識產權常被理解成為“知識財產所有權”,而所有權往往又被冠之以絕對性的權利;從歷史淵源來看,知識產權脫胎于“壟斷權”,其中的著作權更是與所謂的“自然權利”理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②從知識產權具有絕對性色彩來看,若將人工智能機器賦予知識產權主體的地位,顯然是有悖于法理的。
(二)從權利保護論人工智能產出物的知識產權歸屬
從知識產權保護的角度來討論,當產出物的知識產權人身權能或者財產權能或者二者同時被破壞時,遭受侵權損害后果的人也只能是現行知識產權法的權利主體,而不可能是人工智能工具。即使人類已經通過技術手段賦予人工智能機器以人的情感,比如能夠表達喜怒哀樂的機器人,但法律上自然人的自然屬性是其無法取得的,知識產權法上的“人”的概念所具有的主觀能動性與價值判斷的能力是人工智能機器無法具備的。
四、不同觀點展示及本文意見——從人機關系論人工智能產出物的知識產權歸屬
以上從知識產權本身的權能屬性與權利保護兩方面分析,可見人工智能機器的仿真性無論達到何以高度,其終究非真正意義上法律所保護的權利主體。其產出物的權利應當歸屬于設計人工智能機器的人或者人工智能工具所有人所有。
不同觀點認為,人工智能機器已經不是空有智商而無情商的冰冷機器,其舉2017年湛盧文化和微軟合作推出的作品《陽光失了玻璃窗》為例,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完全由人工智能自主創作的作品;AI機器人在2018年Googlel/o大會上不僅可以和人類無障礙溝通,并且可以感受談話對方的情緒變化,能夠應付被打斷的談話進行主動談話,行為已經趨向于一個理性的“人”。本文認為,人工智能產出物具備知識產權客體的獨創性、新穎性等屬性,其產出物作為知識產權的客體或者是客體的載體毋庸置疑,但是,倫理上,從倫理基礎上理解人機技術關系其實是探討人機倫理關系,從智能哲學的角度看這種關系可以追溯到對人類的意義、價值和地位的理解。③不能把產出物與人類利益割裂開來,即不能簡單的把人工智能設備這一主要發揮工具作用的機器認定為知識產權的主體。現階段,我國的人工智能發展技術尚處于“軟人工智能”階段,未達到人工智能完全取代人工的程度。諸多工作,人工智能機器都還未能自主完成,假如認定其可以作為權利主體,絕大多數的人身權能和財產權能也需要由人工智能機器的操作者或者所有者代為行使。由此可見,以一種全面的、發展的視角來看,人工智能機器在本質上與傳統的生產機械別無二致,究其根本產生的起因是服務于人類社會,在人類發展進程中輔助人類創造和提升物質與精神價值。
五、總結
綜上,就目前而論,人工智能產出物的知識產權歸屬主體應為現行知識產權的權利主體,無須將人工智能機器增設為知識產權主體。人工智能技術尚未在本質上對現行法律制度和社會生活造成沖擊,未來存在著一系列不確定性,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人工智能機器的法律地位也存在諸多可能性。但是倘若在面對科技帶來的新生事物時總僅以現有法律教條去解釋,那么有可能會產生以偏概全的效果,它有時候會因為缺乏實證經驗而充滿不確定,有時候會顯得荒謬、不公平或無效率。④本文僅就知識產權角度的冰山一角討論人工智能,法制的有效運行,離不開各部門法的有序配合,只有根據技術的發展與時俱進,適當調整,才能發揮立法與決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 注 釋 ]
①劉劍文,張里安主編.現代中國知識產權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1.
②王春燕.也論只知識產權的屬性[A].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青年學者文集[C].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③齊昆鵬.“2017人工智能:技術、倫理與法律”研討會在京召開[J].科學與社會,2017(2):126-127.
④Samuelson,P.Allocating ownership rights in computer-generated works[J].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w Review,1986,47(4):1192-1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