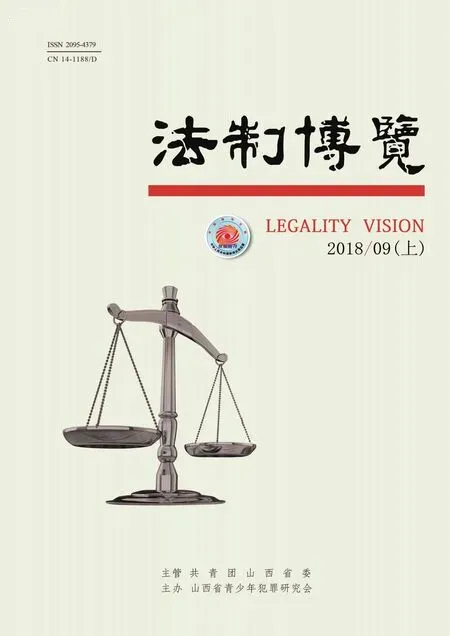論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制度的存廢
廖原菲
廣州大學松田學院,廣東 廣州 511300
優先購買權早在公元前6世紀就已存在,經過上千年的發展,現在已經是一項成熟的制度,并且在國內外都存在。該項制度的存在不但有法理依據,也有社會基礎。在當今社會中,其與其他古老的制度一樣也存在著存廢之爭。
一、我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的立法規定
本文所研究的這一項法律制度目前在我國還無統一的民法典,僅在《合同法》、《民法通則意見》等中被提及。最新的規定則是《關于審理城鎮房屋租賃合同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簡稱解釋),該解釋由最高人民法院頒布,施行于2009年,該解釋對于這一項法律制度對第三人產生效力予以了否定,但卻未規定出租人如何承擔賠償責任,以及該責任的性質如何等。同時,關于這一項權利的行使,第24條更詳細的予以了限制,使承租人權利的絕對化受到阻止,但均沒有明確規定實踐操作和同等條件以及合理期限等,對承租人優先購買權在實踐中所起到的保護作用有限。
二、承租人優先購買權存在理論與實踐中的缺陷
首先,允許承租人以同等條件強制出租人與自己進行買賣契約訂立的承租人優先購買權是一種附強制締約義務的請求權,該制度不符合物權優先原則,是強制干預出租人行使處分房屋權,使得債權在一定程度上被物權讓位,“使標的物之支配權事實上屬于承租人,而出租人不過有空權而已,所有權變成虛有權。”同時,將房屋所有人選擇買房訂立契約的自由被剝奪了,不符合意思自治原則。
其次,由于過于簡單的立法規定,使得成立要件操作性不夠強,很難在現實中對其進行把握。無法確定承租人行使優先購買權的期限以及“合理期限”的起算點,使得承租人難以行使權利。在判案時,法院存在自由裁量現象,究其原因是無詳細對“同等條件”加以衡量的標準,這使得時常出現同案不同判現象,最終導致本項法律制度難以發揮應用作用。
當前,承租人的弱勢地位已發生改變,如果一味的強制保護這一權利,將導致交易糾紛頻繁發生,且侵害到第三人和出租人的利益。當前,這一群體的利益已通過市場的公平競爭等得到一定保護,因此,應廢棄該項制度。
三、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的替代措施
(一)買賣不破租賃制度
替代的這一制度和應該被廢除的法律制度相比,法律效力確定、使用條件詳細明確、性質清楚,而這一切在于《合同法》給予了明確規定,使得替代制度可以將強有力的保護予以房屋承租人(或者說不動產承租人)。在訂立租賃合同期間里,雙方可以進行磋商,如有糾紛存在于這一階段,可通過締約過失責任(由《合同法》規定)來對雙方各自的權利加以保護。訂立合同之后,若諸如抵押權等他物權產生于合同生效后,則依替代的這一制度,承租人可與在先抵押權對抗;若他物權產生于合同生效之前,雖承租人無法與之對抗,卻可以向出租人請求賠償,主張違約責任。出租人在存續合同期間,若想將房屋出售,則向另一方,可發出請求對租賃物進行購買的要約,并將其的所有權基于締約合同來達成,且在對另一方的利益不造成侵害的同時,另一方還受先通知義務的保護,實現徹底保護另一方權利。而在租賃期限到了時,如果承租人想亟需租賃房屋,則可以和出租人磋商,并且前者無權干涉后者的處分房屋的行為。
(二)對承租人余益的保護
承租人在租賃到房屋后,可能會裝飾、裝修租賃而來的房屋,對此種情況下的雙方當事人利益的保護,施行于2009年的《房屋租賃糾紛解釋》明確做出了規定。對出租人,《合同法》規定有費用償還義務。即對于承租人為維護租賃物處于基本使用狀態而支出的費用,以及經過出租人同意的有意費用,可以獲得補償。
(三)完善房屋租賃立法
對房屋租賃立法予以完善,通過法律,對出租人房屋出賣的通知義務予以強行規定,當這一義務被違反時,也就是,出租人未將出賣房屋的信息通知給承租人,則后者可以請求前者承擔違約責任,以此來保護自身的利益。
四、結語
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有著存在的基礎,也曾取得過一定的成效,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其開始暴露出一系列問題,為此,在法理分析中,應秉持“兩弊相衡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也就是,既然在實際中,該項法律制度已無法真正對承租人的權利加以保護,且存在的弊端無法克服;通過出租人的強制通知義務、余益保護制度以及買賣不破租賃制度都可以真正保護承租人的權利,那么將承租人優先購買權制度廢棄已成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