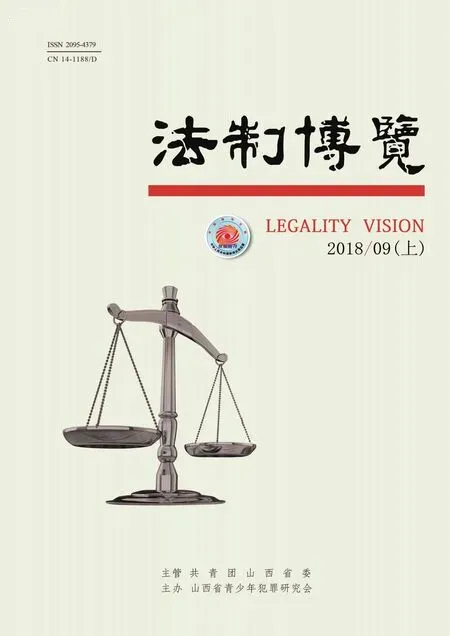13-15世紀英國婚姻訴訟的程序
仝路辰
河南大學法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一、聽證會
通常情況下,訴訟的初始階段,雙方都要親自出庭,以便法官從當事人口中聽到第一手陳述,有些簡單的問題在這個階段就能得到解決。聽證會后,大多數(shù)當事人可以不出庭,由代理人代行訴訟行為。1439年Rochester法院Alice Sagon和Robert Ederich離婚案中,Alice僅作了一份簡短的聲明,聲稱“只要能得到一份令我滿意的嫁妝,就可以離婚”,法院即判決他們離婚。類似案例還有很多,這些案例說明了一個共同的問題:無論是教會法庭還是當事人,都將解決實際問題視為婚姻訴訟的最終目的。當事人如果能在聽證會上達成一致意見,后面的程序可以不用完成。
聽證會是強制出席的,缺席一方將喪失與證人當面對質(zhì)的機會,如果對方提出要求,缺席方還將受到教會的制裁。這種做法保證了當事人積極參與法庭活動,以便迅速解決糾紛。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那就是法庭允許被告提出幾個相互矛盾的辯護理由,法庭不會證實其真實性,只要有一個能反駁原告訴求既可。這種情況極少出現(xiàn),但是這顯示了教會法院的基本態(tài)度,那就是不訴不理。只要原告訴求得以解決,與訴求無關(guān)的事實真相不予調(diào)查。
二、質(zhì)證
如果說聽證會明確了爭議的問題,那么質(zhì)證環(huán)節(jié)就是由雙方拿出證據(jù)來證明自己的主張。在英國的法庭實踐中,婚姻案件的實際證據(jù)幾乎都是證人。聽證會后,被告和證人通常會有一天時間當面對質(zhì),如有必要,被告也可以提供證人反駁原告,這時,原告也可以對被告方的證人進行質(zhì)詢,只有極少數(shù)證人同時為雙方作證。
教會法學家堅持認為法官應當限制大量證人的使用,但當事人總是想方設(shè)法請更多的證人來證明自己的訴訟請求。證人有權(quán)利拒絕出庭作證,但當事人通常會支付證人一筆費用,證人難以拒絕金錢的誘惑便會選擇出庭。如果證人依然不愿出庭,當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請制裁,以強制證人出庭作證。事實證明,這種情況是經(jīng)常發(fā)生的,并且總是奏效。1493-1495年,坎特伯雷法院審理的18樁到達聽證階段的婚姻案件中,一共產(chǎn)生了49個證人,其中有4人一開始拒絕出庭,經(jīng)過強制傳喚程序后,他們最終都出庭了。
對證人的詢問單獨進行,每位證人分別接受詢問,對方當事人無權(quán)對證人發(fā)表質(zhì)詢。這種詢問方式有利有弊。利處在于,證人能夠得到較好的保護,免受被恐嚇的危險;弊端在于,對方當事人無法審查證人所說是否屬實,更沒有澄清的機會。更糟糕的是,法官無法直接與證人對話,全憑證人的詢問記錄進行審理,法官對案件真相是否真正了解十分堪憂。為了保護證人而忽視裁判者對證據(jù)的直接接觸,顯然是有些矯枉過正的。對此,教會法庭也有折中方案。第一,證人都是在法庭上公開宣誓后接受詢問的,法官至少可以據(jù)此判斷證人的可靠性。第二,如果法官對證詞不滿意,可以重新召回證人進行審查,也可自行調(diào)查以印證證人證言。第三,詢問者有時會寫上詢問過程中自己的看法。但這畢竟不是必經(jīng)程序,一切全憑法官的責任心,即使有了這些保障措施,依然不能還原案件真相。
除了證人證言的采集,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影響法官的判斷,比如孩子的撫養(yǎng)權(quán)、社會階層和貧富差距等。教會法沒有把這些因素排除在外,有時還會是參考條件,女方是原告未必就能捍衛(wèi)自己應有的權(quán)利,畢竟在那樣一個父權(quán)制社會,教會法對女性的保護始終建立在對男權(quán)的維護之下。但總的來說,在聽證會階段,法官是致力于還原案件真相、做出公正判決的。
三、宣判
最后一個步驟是宣判,在一方缺席出庭的情況下,也可以做出判決。原則上,法庭不接受調(diào)解,大部分案件都有明確的判決或命令,但在實踐中,很多案件當事人選擇妥協(xié),達成調(diào)解協(xié)議或撤訴。在現(xiàn)存文書中經(jīng)常發(fā)現(xiàn)這樣的記錄:“原告不希望訴訟繼續(xù)進行,被告請求對方撤訴,原告撤訴”。Lichfield1474年的一起案件中,雙方當事人同時出庭并宣布達成和解,案件即宣告終結(jié)。另一起案件中,雙方當事人在德高望重的牧師的見證下達成了和解,法院的書記官也簡單記錄下了這一事件。可以發(fā)現(xiàn),教會法關(guān)于能否達成和解的規(guī)范并未出現(xiàn)在實際操作中,人們更注重問題的解決,達成和解是最令人滿意的解決糾紛的方式,教會法對此也持寬容態(tài)度,沒有多加干預。
總體而言,13-15世紀的婚姻訴訟中,一切都圍繞“效率”運轉(zhuǎn),教會法院為婚姻糾紛的解決提供了高效的場所和寬容的態(tài)度,這種高效的運轉(zhuǎn)機制也贏得了人們對教會法院的信任和接受,無形中加強了教會對社會生活的控制,而教會對日耳曼傳統(tǒng)習慣的接受和妥協(xié),也加速了二者的磨合,為英國法律的發(fā)展留下了寶貴的經(jīng)驗法則。